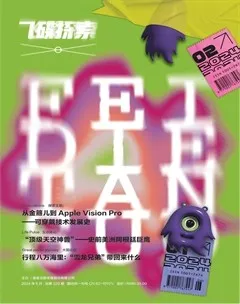意念的能量有多大




1
對“8 0后”“9 0后”的男生來說,機甲象征了一種熱血夢想,在動漫和電影的渲染下,哪個男孩沒有在童年時期做過駕駛機甲拯救人類的白日夢?
綜觀科幻電影,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點:大眾對機器人一直充滿警惕,擔憂機器人會產生自我意識,然后反客為主將人類奴役;可是對于機甲,大眾的態度則是完全歡迎,從未有過半點不信任。原因在于機器人是AI,自帶程序,可以自行工作,可機甲是一種外置裝備,沒有人類的操控,根本無法自行啟動,這種天然屬性仿佛為人類帶來了安全感。
在電影《環太平洋》中,人類為了掌控機甲,將大腦的神經系統與人工智能通過傳感器進行連接,從而達到身體與機甲能同步接收大腦指令。機甲不再是簡單的巨型盔甲,而成了駕駛者的外延器官。換句話說,操控機甲靠的不是操縱臺,而是人機合體的默契,腦袋里的一個閃念,就成為機甲四肢的動作,這具龐大機器的運轉,是在人類意念掌控下進行的。
意念是什么?古人不懂解剖學,以為所有的想法來源于“心”。隨著醫學進步,科學家認為大腦才是意識的發生場所。但我們站到數字化時代的浪潮之上,用計算機思維來看待意念,就會發現,意念的核心是信息的傳遞。如果我們能夠做到不受約束地傳遞信息,就能夠控制一切,修仙小說中的隔空取物并不是幻想,只要我們能建立起高效正確的信息傳遞網絡便可實現。
1 9 9 9年,國際BCI(腦機接口)會議將BCI 定義為“一種不依賴于正常的外周神經和肌肉組成的輸出通路的通信設備”。 腦機接口看起來很神秘,其實原理并沒有想象中復雜。大家普遍以為,動作是一個瞬間,當你看到門的瞬間,手就會自動伸向門把手。其實,從你腦海中跳出來“進門”這個指令,到你的手臂產生實質性的動作,中間存在一系列的過程。在你的身體做出反應之前,大腦運動控制區域的皮層,已經發出“進門”事件的同步電位活動,當這個信號被傳遞到控制四肢的神經,才有了手臂推門的動作。腦機接口就是模擬了人類大腦傳遞信號的過程,越過外周神經和肌肉,直接讓大腦連接計算機,利用算法模仿出龐大而復雜的神經傳遞網絡。
在所有疾病中,癱瘓無疑是最讓人受折磨的,眼睜睜看著自己喪失身體的控制權,明明大腦有著無限想法和情感,卻必須受制于肉體,每一天都如同身處牢籠。現在,腦機接口用科技的力量打開了這座“牢籠”的門。2 0 1 2年,布朗大學針對中風癱瘓的病人發明了一種芯片,名叫“大腦之門”。這種芯片可以將大腦的神經信號傳遞到計算機,然后由計算機將信號傳給機器手臂。病人在頭頂安裝芯片之后,通過腦機接口的方式,用意念來控制機械手臂,成功完成了運動、拿東西等動作,讓病人以人機結合的方式恢復了生活自理能力。
腦機接口的研究應用,不僅能夠給癱瘓病人和殘疾人的生活帶來質的提升,也為普通人的生活帶來了無限希望。比如,意念打字的出現。2 0 2 2年,馬斯克創辦的腦機接口公司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發布會。活動中,馬斯克展示了一只被植入腦機接口設備的猴子用意念打字。他高調地向大眾宣布,意念打字已經正式進入人類的生活。
事實上,意念打字是腦機接口研究最多的應用,早在1 9 8 8年,奧地利科學家就設計出一種有3 6個選項的打字系統,能夠每分鐘用意念打七八個字符。意念打字并不是什么新鮮事,馬斯克的展示之所以給我們帶來沖擊,是因為他以視頻的方式,公開呈現了大腦思維具象化的過程,讓人恍然發現,現實生活離科幻小說的距離,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如果,思維不再是稍縱即逝的閃現,而是能夠被抓捕,被記錄,無形的精神力量能夠被轉化成有形的形式,人類的操控能力就能夠無限延伸。如果,我們的意念能夠轉化為屏幕上的語言,那么,我們是不是也能用意念操縱游戲手柄?用意念控制家里的智能開關?假以時日,是不是也可以用意念操控機械外骨骼?是不是人人都能夠變成鋼鐵俠?這樣的發散聯想,很難讓人不激動。
2
在人的大腦里,存在著1 0 0多億個神經細胞和1 0 0萬億個突觸物質,神經元之間傳遞信息依靠微弱的腦電信號,只要大腦整體電場的強度達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被外置設備采集到。而大腦發出的指令并不是只在單個神經元中傳遞,而是在一大片神經網絡中流淌,這些采集到的信號并不純凈,而是充滿噪聲。而且,一個腦電信號,可能包含多種含義,不同腦電信號之間的差別并不大,想要準確識別出大腦的指令,需要經過反復實驗收集對比信號,分辨信號想表達的意圖,然后將信號與具體動作匹配。
在意念打字的項目中,關鍵點在于信息的采集。常見的采集模式可以分為兩種:侵入性采集方式和非侵入性采集方式。
侵入性采集方式,顧名思義,就是將電極植入實驗者的大腦。傳統的方式是在患者面前放置一個帶有鍵盤的顯示屏,患者通過大腦中的電極控制光標,用光標選擇鍵盤上的數字鍵,實現意念打字;新型意念打字的遞歸神經網絡原理,是讓實驗者在腦海中把字母“寫”出來,通過完成“寫”這個動作,電極觀測到大腦運動皮層中的信號,對“寫出”的字母進行識別,然后將腦海中的字母復制生成在屏幕上,使人的意念變成現實中的文字。
非侵入性采集方式,主要是靠外界刺激,采集原理是穩態視覺誘發電位(SSVEP)。實驗者在頭上戴一個布滿傳感器的裝置,眼前放置一個帶有模擬鍵盤的顯示屏。鍵盤上的字符會隨機生成亮度序列,實驗者眼睛注視著鍵盤的亮度變化。當實驗者心中所想的字符亮起時,大腦的視覺皮層會產生一個強烈的信號。隨著鍵盤亮度的提醒,系統通過對相應信號的編碼分析,確定實驗者想要打出的字符,以此實現意念打字。
兩種采集方式中,侵入性采集方式能夠直接采集大腦皮層的信號,采集數據更為準確,但植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大腦是人身體中最精密的器官,外科手術很可能會對大腦造成損傷。非侵入性采集方式雖然安全,但在采集數據的準確性上有所降低。兩種方式各有優點,但仍然無法做到百分之百準確,打字的速度也明顯低于常人打字速度。意念打字技術雖然成熟,但目前只在醫學領域應用,主要服務于癱瘓病人,離常態化地融入生活還有一段距離。
面對技術變革,有人惶恐,有人興奮,馬斯克曾經放出豪言,說腦機接口很可能是人類能夠戰勝AI 的武器,意念打字的研究成果無疑加強了這種論調。ChatGPT 自問世以來,學習速度超乎人類的想象,AI 不僅能夠檢索、整合信息,也能翻譯、寫論文,還能生成視頻……不到一年的時間,它已經取代了很多人類的工作,人類似乎已經被逼上了絕路,再不趕快進化就要面臨“淘汰”。
3
心學大師王陽明有一句名言:“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陽明的這段話,和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意思相近,都認為人的意念具有至高無上的主體性。
如果從主體性的角度去看待腦機結合技術,意念控制也許是對大腦功能的進一步開發。科學家認為,人類大腦的開發程度只有1 0%,更多的功能還深藏在意識之海,等待我們去發掘。計算機與人類意念的結合,也許能夠幫助人類深入了解自己,在腦機結合的過程中完成進化,就像原始人利用石器成為草原的主人,挪威人利用海船成為北歐的海上霸主,而現在,人類只不過是換了種更先進的工具。意念控制將人類和計算機結合在一起,使人類真正意義上超越了人的生物屬性,不再受身體的束縛,成為人機一體的“超人”,變得更加自由。
但是從審視的角度來看腦機結合,令人擔憂的地方并不少。《三體》中有一個著名的橋段,在和文明程度遠超過地球的三體人開戰時,人類為了反抗殖民,選出4位“面壁者”。所謂的“面壁計劃”,就是面壁者在腦海里制訂作戰計劃。因為智子能夠監視全球的舉動,卻無法發現人類腦海中的想法。思想是人類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計算機能夠大量采集人類的腦電波,就相當于人人都在裸奔,當你腦海里的銀行卡密碼能夠被精準捕捉時,還有什么是真正安全的?
另一個擔憂,就是信息反噬的可能。《環太平洋》中也展現過這個副作用,因為機甲運作產生的信息量太大,一個人的神經系統根本無法承載,所以機甲需要兩名駕駛員一起操作,不然就會造成神經紊亂,甚至死亡。同樣,如果在腦機接口的傳輸過程中,計算機因技術故障將高強度數據傳輸到人類的大腦皮層,那會怎樣?人類會不會成為古希臘神話里戴著翅膀飛向太陽的伊卡洛斯,在可媲美神明的驕傲中迎來沉重的墜落?
那么,對于意念控制,你是什么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