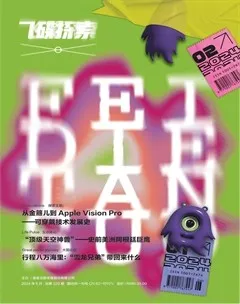新型壓縮空氣儲能電站


儲能,就是把多余的電先存起來,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相當于給電網安裝一臺大“充電寶”,使“靠天吃飯”的太陽能、風能發電都能穩定、流暢地接入電網,存儲備用。
壓縮空氣儲能則是以空氣為介質充放電的“空氣充電寶”。它性能優異,規模大、壽命長、成本低,發展勢頭迅猛。
與鋰電池、抽水蓄能等其他儲能技術相比,壓縮空氣儲能非常“年輕”,在中國僅有1 0多年的開發史,卻發展迅猛,成為后起之秀,令許多業內人士坦言“沒想到”。
一張表
壓縮空氣儲能的概念起源較早,第一個專利于1 9 4 9年在美國問世。德國和美國分別于1 9 7 8年和1 9 9 1年建成壓縮空氣儲能電站,并運行至今。雖然世界各國對壓縮空氣儲能都有布局,但并不熱門,真正將它發揚光大的還是中國。
2 0 0 4年,剛剛參加工作的中國科學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工程熱物理所”)副研究員陳海生開始思考未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給自己定下3條選定標準:朝陽產業、創新性領域、同工程熱物理專業相關。但是,滿足這3條標準的技術是什么?
經過3個多月的調研分析,陳海生相中了儲能技術。這在當時是極其冷門的方向。
那時,我國再生能源裝機占比不足1%,是能源領域里的“小兄弟”,更不存在并網難題。那時的人們很難想象,有朝一日,太陽能和風能會撼動火力發電的主體地位,儲能也將由“冷”轉“熱”。
陳海生畫了一張表,縱坐標是各種儲能技術,橫坐標是創新性、技術成熟度、專業相關度等指標,結果壓縮空氣儲能以5顆星領跑其他技術。但在當時,壓縮空氣儲能在中國僅有理論研究,沒有技術攻關,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空白。
如今回頭看,過去1 0年,我國風電和光伏裝機增長了8倍。2 0 2 3年,風電和光伏裝機更是歷史性地超過火電,占比達5 0.4%。儲能不僅登上了能源發展的歷史舞臺,而且將扮演重要角色。
一場創新
2 0 0 5年,陳海生被公派去英國利茲大學訪學,這是一次技術探索的好機會。
在英國,他和導師共同提出了液態空氣儲能的概念,很快得到6 0 0萬英鎊的經費支持。為了完成這個項目,原本為期1年的訪學變成了4年的正式工作。最終,他們在2 0 0 9年建成國際首套兆瓦級液態空氣儲能裝置。由于液態空氣的密度遠大于氣態空氣,該系統解決了依賴大型儲氣洞穴的問題,比傳統技術更為先進。
有了這次試水,2 0 0 9年回國后,陳海生立志發展比液態空氣更先進的壓縮空氣儲能技術。
當時,傳統壓縮空氣儲能技術存在效率不高的缺點。德、美兩國儲能電站的效率分別僅為42%、54%。也就是說,存進去1度電,只能放出來大約0.5度,另外0.5度在存、放的過程中被消耗了。而且,傳統壓縮空氣儲能裝置必須依賴天然氣提供熱源。
要從根本上突破這兩大技術瓶頸,在中國走通壓縮空氣儲能這條路,顯然不能僅依靠模仿、改進,必須來一場徹底的技術創新。而創新的底氣,源自我國科學家在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領域的多年積累。
傳統的壓縮空氣儲能系統基于燃氣輪機技術,在用電低谷時,利用富余的電能將空氣壓縮并儲存在儲氣室中;在用電高峰時,釋放高壓空氣進入燃燒室,同燃料一起燃燒,驅動透平膨脹機發電。這相當于讓燃氣輪機分時工作,儲能、釋能過程相互獨立,最終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該系統的關鍵在于葉輪機械的高效運轉。工程熱物理所自1 9 5 6年建所以來,在葉輪機械方面研究基礎深厚,創始人吳仲華先生是國際公認的“葉輪機械先鋒”。
基于自身的“金剛鉆”,2 0 0 9年,工程熱物理所提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壓縮空氣儲能技術:在用電低谷時,用壓縮機取代燃氣輪機壓縮空氣,同時回收壓縮熱;在用電高峰時,釋放儲存的熱量加熱高壓空氣,驅動膨脹機,帶動發電機發電。
這一改進不僅不使用額外的燃料,實現了零排放,還將原先浪費的壓縮熱能利用起來,儲能效率大幅提高,理論上可達70% 以上。因地制宜,本土化的條件就此建立起來。但這一改,也意味著從基礎研究到關鍵技術,再到工程開發,都沒有成熟經驗可供借鑒。
一堵“墻”
自壓縮空氣儲能概念提出后,世界各國一直沿用燃氣輪機發電的技術路線,直到中國科學家提出換掉核心部件,業界才看到一條新路。但是,我國在這項技術上并無技術儲備,更談不上產業基礎。陳海生形容當時面臨的困難就像一堵墻。
2 0 1 0年,陳海生帶領一支新成立的小團隊,確定了一個“釘釘子”時間表:用3年時間完成1.5兆瓦示范項目,用4年建成1 0兆瓦示范項目,用5年建成1 0 0兆瓦示范項目。
項目需要攻克的除了核心部件壓縮機、膨脹機的內部流動與傳熱機理相關的難題,蓄熱蓄冷技術也是決定技術成敗的一大關鍵點。
傳統壓縮空氣儲能技術需要補燃,消耗大量天然氣,工程熱物理所儲能團隊經過努力,用先進的蓄熱蓄冷技術彌補了這一不足。并且,他們用的蓄熱蓄冷介質是成本最低的水。“這是一個全世界都沒有出現過的方案。”工程熱物理所研究員王亮說。
要“啃下”這樣的硬科技,必須具備足夠的硬實力。從1.5兆瓦到1 0兆瓦再到1 0 0兆瓦,每一次規模放大,都不是簡單的技術疊加,而是從原理到關鍵部件的重新研發設計。就這樣,隨著一個“釘子”接著一個“釘子”被楔入,在堵路的“墻面”連點成線、連線成面,“厚墻”終于被突破了。
2 0 2 1年,國際首套百兆瓦先進壓縮空氣儲能國家示范項目在河北省張家口順利并網,發電效率達到7 0.4%,每年可發電1.3 2億度以上,節約標準煤4.2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 0.9萬噸。
通過進一步技術創新,山東肥城3 0 0兆瓦示范電站設計效率達到7 2.1%,與儲能技術的“老大哥”——抽水蓄能相當。該電站年發電量約6億度,在用電高峰可為2 0萬~3 0萬戶居民提供電力保障,每年可節約標準煤約1 8.9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4 9萬噸。未來,這將是更適合我國發電行業的主流技術路線。
“成本必須降下來,要大規模推廣,無論如何都得降。”陳海生說,從投入研發的第一天起,他們的目標就是讓這一技術真正在中國落地,造福于民。
一個“螃蟹”
第一個試驗臺、第一個示范項目、第一個并網發電……一路走來,工程熱物理所都在做中國壓縮空氣儲能“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王亮至今記得,搭建第一個1 5千瓦試驗臺時,由于沒有合適的場地,他們在兩棟樓之間的夾道里搭了個頂棚、裝了扇門就成了實驗室。因為里面有一棵很粗的樹,安裝試驗臺時大家繞來轉去,很不方便。
做技術攻關,試驗臺是必需品,但對一支剛起步的團隊來說,這是“奢侈品”。由于投入巨大,2 0 1 2年建設1.5兆瓦中試平臺時,經費非常緊張,必須集中所有可以用到的資源。
除了經費緊張,沒有經驗可循也是這些年輕人面對的一道坎。
“當時幾名剛畢業的博士帶著幾名在讀博士,經常在現場一待就是一個月”,那是大家第一次努力把科學思想變成設計圖紙,再把設計圖紙變成儀器設備。由于國內外都沒有可參考的先例,每走一步都要靠自己摸索。
按照“研發一代、示范一代、應用一代”的發展策略,工程熱物理所的壓縮空氣儲能技術持續發展,在上一代技術示范應用的過程中,下一代技術已經馬不停蹄地開始研發。這些年來,大家跟著項目跑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2 0 2 3年團隊開年終總結會時發現,半數以上職工出差天數超過1 0 0天,有的甚至超過3 0 0天。
張家口百兆瓦先進壓縮空氣儲能國家示范項目首次采用人工硐室,也就是人工開發的地下儲氣洞穴。由于這是首創的技術路線,施工過程中遇到許多前所未有的難題,大家笑稱“總是‘吃螃蟹’也有點受不了”。
2 0 2 1年1 2月3 1日,項目成功并網的那一刻,在場的團隊成員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大家激動地合影留念,一致推舉現場唯一的女性——測試工程師付文秀站在“C 位”。她說:“壓力雖然很大,但成功后獲得的幸福感是別人不能體會的。”
一次成功
對于壓縮空氣儲能的今天,很多人表示“沒有想到”。
一些老先生曾善意地提醒陳海生:“進去4度電,出來3度電,你好好考慮,這個研究方向對不對。”
一位國內同行感慨道:“以前我們都不看好,因為技術上太難了,沒想到真干成了。”
而在已經擔任工程熱物理所所長的陳海生看來,先進壓縮空氣儲能技術在中國科學院誕生、發展,絕非偶然。他說:“第一,中國科學院鼓勵創新,支持科學家開展前瞻性、需要長期探索的技術研究。第二,中國科學院有鼓勵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傳統,能夠支持一項技術從研發走到示范應用。第三,中國科學院能夠形成大團隊,開展大兵團作戰。”陳海生介紹,壓縮空氣儲能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系統工程,需要搭建大平臺,提供長時間、高強度的穩定支持。
儲能研發中心現有職工和學生2 0 0余人。隨著國家“雙碳”目標的提出,儲能產業迎來發展機遇,儲能人才成為就業市場的“香餑餑”。但團隊成立至今,核心成員一個都沒離開。
王亮表示,在團隊里干活踏實,可以專心做一件事,未來充滿希望。“有這么一個平臺能讓我堅持深入干一件事,實現自己的理想,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