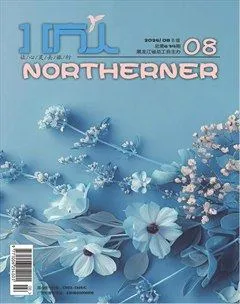比利時:當生命的終點可以選擇
2002年,經過激烈爭辯,比利時通過了3部法律,一部使安樂死合法化,一部承認所有公民有權享有安寧療護,還有一部規定病患有權知曉病情。安樂死合法化,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生命終點的看法。但20多年后的今天,申請安樂死的病患卻沒有預想中那樣多。
2022年,讓–弗朗索瓦便翹首盼著10月22日的那個周六。他每天都會在日歷上做記號,就像囚犯盤算著距離出獄還有多少天。
“得知安樂死的申請通過后,他對我說:‘太好了,成了!’”讓–弗朗索瓦的父親馬塞爾·康拉德回憶道,“知道苦難就要結束了,他如釋重負,甚至開心得能張口說話了!25年的折磨終于要畫上句號。”年過七旬的康拉德給我們看了一張他兒子的照片,拍攝于實施安樂死的前3天。他躺在床上,比了個勝利的手勢。
1998年,20歲的讓–弗朗索瓦突發腦溢血。“他當時正在和我聊假期都干了些什么,然后突然就倒下了,一點預兆也沒有。”康拉德說。這名年輕的建筑系男孩從此喪失了語言能力、高位截癱、反復住院,經歷了多次手術。康拉德說:“一開始他用盡全力,想要回到正常生活。但他后來意識到,這輩子都要在病床上度過了,生活無法自理。”幾年前,讓–弗朗索瓦第一次有了安樂死的想法。“他媽媽極力反對,讓–弗朗索瓦不想讓她難過,就選擇了與病魔繼續抗爭。為了她,為了我,為了所有人。”康拉德說。
2021年,母親去世,讓–弗朗索瓦又一次想到了安樂死。“他左手食指抵著太陽穴,對我做了個‘嘭’的口型。我能說什么呢?這個選擇應該讓受折磨的人來做。”這位父親說。2022年10月22日,在列日市附近的臨終護理院,讓–弗朗索瓦如愿離開了人世。“他不希望注射的時候我們在病房里。護士出來后笑著對我說,讓–弗朗索瓦剛才還給她講了個笑話。醫生也告訴我,我兒子在注射之前,對他說了3次‘謝謝’。”
嚴苛的申請條件
安樂死的申請條件極為嚴苛。申請者需證實自己身患不治之癥、長期忍受無法緩解的生理或心理折磨,還需獲得兩三名參與會診的醫生的同意,最后再手寫申請,簽名并注明日期。
然而,比利時對安樂死受眾群體的定義相對寬泛。自2014年起,未成年人也被允許申請安樂死。除了需征得父母同意外,其他申請條件與成年人相同。此舉引發了激烈論戰,超過170名兒科醫生反對未成年人安樂死。此外,若條件符合,精神障礙患者也可以申請安樂死。
在比利時,安樂死病例雖然有所增加,但仍是少數。2022年,該國安樂死人數(2966例)僅為全國死亡人口的2.5%,而前幾年更是只有1%。“比例提升是因為人口老齡化,而不是因為安樂死越來越普遍。”安寧療護醫生科琳娜·范奧斯特說。
達馬斯醫生認為,“這也是因為民眾對安樂死的相關政策更加了解了。一開始,申請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占比較多,因為他們知道的信息最多”。
20年來,有3萬名比利時人行使了安樂死的權利,其中包括2014年以來的4名未成年人。安樂死反對者擔憂的情況完全沒有發生。他們曾高聲疾呼,認為安樂死將演變為一股不良風氣,席卷老年人群體。
傾聽訴求
安樂死的合法化甚至創造了新的儀式,比如“安樂死之節”。“在安樂死的前一天,讓–弗朗索瓦被特許離開病房,和好朋友外出狂歡。他們玩到凌晨兩點才回來。”康拉德說。大部分臨終患者的家人會選擇陪伴在患者身邊,度過最后的親密時光。德梅斯特一家便是如此。“我的丈夫患有心臟淀粉樣變性。”伊麗莎白·德梅斯特說,“這是一種不治之癥,最終會引發大腦疾病。他自己就是醫生,見過許多生活毫無質量可言的臨終患者。他不想變成那樣。”
老太太深情地回憶起丈夫離去的那一天:“早上他還給我買了花,說是要向我‘賠罪’,因為不能和我共度61周年結婚紀念日了。孫子幫他洗了個澡。然后他給我們最親密的好友打了電話,與他們作最后告別。那天晚上,我們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后來醫生來了,他和我們說了再見,便和醫生進入臥室。醫生為他注射麻醉劑后,我也走了進去。接著,醫生給他打了致命的一針。那一刻,我的心都要碎了。”
家屬時常會邀請前來實施安樂死的醫生喝杯咖啡或香檳。“有一次,我為一名95歲的老太太實施安樂死。”達馬斯說,“注射之前,她的3個女兒和她一起哼唱起了普雷維爾的詩歌——《參加葬禮的蝸牛之歌》。她的主治醫生也跟著唱了起來。”
當然,不是每一次安樂死都如此順利。即使病患自愿赴死,親友或許也仍舊無法接受。“我的兩個孩子就不能理解他們爸爸的做法,他們都希望他能活下去。”德梅斯特說。而醫生在這個過程中也會受到傷害。“我盡量一個月內只實施一次安樂死。”布魯塞爾的全科醫生伊夫·德洛赫特說,“最好是早上,這樣我還能有時間開車去海邊透透氣。”范奧斯特說:“隨著時間流逝,我實施安樂死時的恐懼漸漸減少了。但我一直知道,我才是最大的輸家。作為醫生,我沒能讓病患相信生命還有價值。不過,更大的罪惡在于沒有傾聽病患的訴求。”
在安樂死病例中,精神障礙患者仍是少數,只有不到1%。不過醫護人員相信,這一群體的需求會逐漸增加。2022年5月,居住在弗拉芒大區的一名23歲女子,因無法忍受精神痛苦而選擇了安樂死。6年前,她親歷了布魯塞爾機場恐怖襲擊事件。雖然身體沒有受傷,但從此患上重度精神障礙,深受折磨。6年間,她曾多次入院,但情況未有好轉。那么,法律是否應該賦予她選擇死亡的權利?安特衛普檢察院認為,這名女子接受安樂死的流程并不違法。“安樂死的法律最初考慮的是癌癥患者。”范奧斯特解釋道,“但精神障礙患者也應有權要求安樂死。”不過,這個案例依然在比利時引發了軒然大波,許多民眾都感到難以接受,其中不乏醫療界人士。“雖然患者或許難以忍受痛苦,而且也沒有什么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不希望看到類似情況發生,尤其是年輕患者。”德洛赫特說。
和許多人一樣,退休社工約希亞娜從前也對精神障礙患者接受安樂死這件事驚恐不已。“我的女兒賽弗琳娜忍受了30年的折磨,去年提出要安樂死。她17歲就患上了精神病,被診斷為抑郁癥及精神分裂癥。什么療法都試過了,但效果都不好。她自殺過好幾次。2022年春天,精神醫生給她試了一種新藥,但副作用很大。她和我說想申請安樂死,我震驚得緩不過神,覺得自己又被籠罩在了自殺的陰影下。”約希亞娜說。她承認,自己用了一些時間才接受了女兒的決定。“當我發現她在申請安樂死后輕松了許多后,我似乎也漸漸能夠理解了。我陪伴她走完了最后一程。她那天穿的衣服還是我和她一起去挑的。2022年7月4日,她在自己家里離開了。”約希亞娜說。
在比利時,安樂死的受眾范圍或許還將進一步擴大,涵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這一群體也有安樂死的需求。“但目前而言還無法實現,因為法律要求安樂死申請人必須意識清醒,能夠表達自身意愿。”尊嚴死法案協會比利時分會主席雅克利娜·埃克曼說,“對于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來講,只有陷入了不可逆性的昏迷狀態,安樂死申請才會被通過。”“但這不是眾多患者想要的。他們希望能提前申請安樂死,然后在特定時間實施,比如在認不出子女的時候;或是只要還未完全喪失認知能力,就可以隨時修改實施時間。”達馬斯說。然而目前,比利時政府似乎并未對這一話題作進一步探討。
(摘自2024年第4期《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