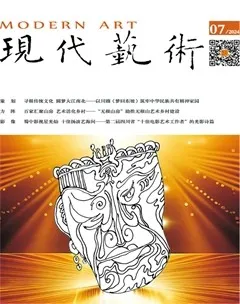結構新穎 形神兼備
戲劇是藝術形式也是文化形式,其創作常以歷史人物為原型。蘇軾作為帶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也作為巴蜀之地的杰出人物,無疑是一個可挖掘的文化藝術瑰寶。近期上演的大型新編歷史川劇《夢回東坡》便以其為對象。《夢回東坡》既巧妙融合了傳統川劇的多種藝術元素與表現手法,在敘事結構、形象塑造與舞美設計等方面也進行了合乎情理的創新轉化。可以說,該戲以景觀生產的方式生動形象地活化出了蘇軾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程與豁達寬廣的內心世界。
形散神聚:敘事結構創意新穎
蘇軾一生宦海沉浮,從政四十年,輾轉多地,主政八州,人生故事繁雜多維。要在有限時間內的舞臺上講好其故事,塑造好其形象,無疑是一大挑戰。以川劇表演藝術家陳智林為領銜主演的川劇編創團隊,反復研究、揣摩,終以頗為成功的結構形式克此難關。他們回歸歷史本來,守正創新,巧妙突破“三一律”的平面敘事結構,以夢中追憶過往的倒敘邏輯架構,采用川劇折子戲的表現形式,輔以散文化的手法,有機整合并精彩呈現了蘇軾一生的主要事件與心靈軌跡。
《夢回東坡》一戲分為八場,重點展現蘇軾知黃州、惠州、儋州的經歷:黃州悟道、修建雪堂、惠州修橋等重要場景畫龍點睛地將人物性格、復雜世事及人性真美活見于舞臺。主要故事基于倒敘框架線性展開(事件內容及因果關系因之清晰明了,易于觀眾進入劇情并沉潛其中),又隨意識流動而弱化各場戲彼此間的因果鏈條——這種形散神聚、不無創新意味的敘事結構,不僅使全戲在時空轉換上流暢自然,也給觀眾帶來了一種沉浸式的觀賞體驗。這在某種意義上契合了羅伯特·瓦爾肖所說的道理:“首創性只有在這樣的程度上,亦即當它只是加強了所期待的體驗而不是根本改變它時才是受歡迎的。”
愛情與死亡作為文學藝術的永恒主題,在《夢回東坡》中得到了毫不造作的演繹和自然而然的流露。戲中借書匣由空到滿這一細膩而巧妙的敘事線索以及對《赤壁賦》的反復吟詠,深情勾勒出蘇軾與其妻王閏之之間的那份質樸而又濃烈的愛情。在“修建雪堂”一場中,接書匣的情節尤為傳神——夫妻二人欲拒還迎的微妙拉扯,彼此間的小心試探、揣摩,都被精準、具象地呈現出來。在“夜游赤壁”一場中,王閏之隨口所作的口語詩既充分運用川劇的通俗易懂特點,達到令人忍俊不禁的觀賞效果,也形塑出一個樸實無華但又內蘊人生智慧的鄉村婦女形象。當然,這亦為后續劇情埋下伏筆。實際上,盡管王閏之不識字,但其卻懂得詩文之于蘇軾的重要性;她也因此于焚詩之后又不辭辛勞地四處收集詩稿,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最終得以將書匣“完璧歸趙”,并能在蘇軾等人面前誦出“口語版”《赤壁賦》——這實是王閏之對蘇軾真摯愛意的表達。在王閏之離世時,蘇軾悲痛欲絕,他含淚復述妻子的“口語版”詞句——這亦是蘇軾對王閏之愛之深切的直觀展示。很明顯,這一頗具匠心的情節編排,不僅達成了劇情回環結構的起承轉合、前后呼應,也將觀眾的情感推向高潮。自然,由此引發的強烈情感沖擊力直擊人心,讓人深刻體會了愛情與死亡所帶來的震撼與動容。
神韻卓然:形象塑造立體鮮活
《夢回東坡》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并沒有陷入一味說好、過度拔高的虛夸模式,而是獨出機杼地借多重性格組合來立體、豐滿地呈現。它通過機巧的情節細節設置,情真意切、哀而不傷的唱腔,具象生動的風格化言行,形神兼備地刻畫了蘇軾及其周圍人物的典型形象,使觀眾既能更為深入地理解其性格、情感和行為,又能深入其內心,借內外世界的生命景觀識出其乃“熟悉的陌生人”,即“他一方面像這范疇里的許多人,同時又只像他自己,任什么別人也不像的”。
當然,《夢回東坡》中的蘇軾并非完美無缺的形而上存在,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活靈活現的“人”的真實存在:他有喜怒哀樂,也有人性不完善的一面,既不像其父想象中在直面構陷時傲骨嶙嶙,也不似其母期望中在被嚴刑拷打時鐵骨錚錚——他事實上選擇了屈就威權與不實認罪的委曲求全。其實,這種審美層面上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并沒消減人物的崇高感,反而讓觀眾能更加真實地感受到人物的人格魅力、人性張力,感其所感,與其共情。當然,戲中其他角色的傳神塑造也豐富了劇情和主角形象:他們與蘇軾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彼此的互動與影響在凸顯自我性格的同時,也使劇情更有層次與色彩。知黃州時,頗為落拓的蘇軾曾為當地修橋而與姐夫程之才發生過令人捧腹的斗智斗勇故事:該場戲借兩人之間的川味俗語對白、唱段、土話等,為表演注入濃厚的幽默元素與地域色彩;兩人的言語交鋒顯示了蘇軾的通達睿智、一心為民與程之才的小人得志、一時糊涂;你來我往之后,程之才幡然醒悟,由想要報復蘇軾的小人形象轉變為關愛百姓的負責官員形象,人物也因此栩栩如生(盡管“轉變”稍顯突兀,但慮及本戲結構與“夢回”設定,其亦在情理之中)。
綜合觀之,通過多維立體的表現方式,《夢回東坡》成功地塑造出真實飽滿、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躍然于舞臺,便會讓人更為全面深入地了解蘇軾,睹其作為杰出人才的真實面貌與復雜性格——其神韻卓然的詩書畫藝、治世方略、品德操守與人生哲思,使該戲在整體層面上達至思想性、藝術性與觀賞性的有機統一。
內蘊豐富:舞美設計虛實相生
總的說來,《夢回東坡》的舞臺風格是簡約唯美的,卻蘊含豐厚的內涵與悠長的意味。戲中置景、道具多寄寓象征與隱喻,也使舞臺現出一種抒情寫意的氛圍。全戲舞臺背景以月為主導。作為重要的布景裝置與傳情達意的元素,精心設計的月亮自然流溢出以物傳神、以虛襯實的美學效果,輔以燈光、色彩的妙用,背景中的月亮時缺時圓。不無寫意風格與浪漫主義色彩的月之圓缺象喻了人的悲歡離合,亦折射出蘇軾一生上下沉浮、輾轉奔波但又達觀向善、富有詩意的生命旅程。作為傳統戲曲舞臺的常見布局,左懸“出將”、右掛“入相”的舞臺置景既揭示了中國傳統戲曲文化的深厚底蘊,也暗合蘇軾在遵循政治體制、君臣綱常、倫理法制(演員則依循左上右下的戲劇程式)的同時,又安貧樂道、因地制宜、出奇創新(表演則吸納現代、融入世俗、貼近現實)的入世又出世的人格情懷。
基于舞臺背景的整體構思,《夢回東坡》的舞臺道具追求寫意,以少勝多,以簡馭繁。除用一些門框代表好友為蘇軾修建雪堂送來的實物、用兩個車旗象征蘇軾想象中的攜妻回鄉之車等較為簡單的道具展陳外,戲中隨處可見無實物的表演。由此營造的帶有寫意性、曖昧性的舞臺空間給予觀眾更多想象空間,使人不僅能較為自由地理解劇情,準確地把握角色心理,也能在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田野上放飛想象的翅膀,“精騖八極,心游萬仞”,達至情感的至真至純與心靈的凈化升華。
誠然,作為川劇,也因是川劇,《夢回東坡》大量運用川劇的唱、念、做、打程式及源自世俗生活的方言俚語,為人鋪陳出既嚴肅又詼諧的戲曲生活展演:幽默通俗的川劇念白、變化多樣的川劇唱腔、可圈可點的水袖技藝與設計精巧的武戲打斗等作為特殊的敘事景觀,在讓觀者更為深入地領略戲中人物的情感變化與戲曲演員的深厚功力的同時,也作為讓集體反思的虛擬性載體(作為夢又似于夢),不斷暗示出關乎個體人生、關乎人類生存的基本道德倫理底線。
結語
思及開去,《夢回東坡》不僅是一場關于蘇軾的戲曲盛宴,更是一場匠心獨運的文化景觀。它別出心裁的夢境設置、蘇軾重要人生節點的有機串聯、具象鮮活的世俗世界與人物性格、虛實相生富有寓意的舞臺設計等,集中形塑了蘇軾波瀾起伏又詩情畫意的一生。他的大愛至純、詩意理想、豁達風骨、韌性掙扎等都成了見于舞臺的敘事景觀,不論是其“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的與友月夜泛舟的舒暢之情、“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刻骨愛意,還是“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豁達從容,都自然溢出別樣的意味。或者說,作為“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我們可以得到某種對‘終極實在’之感受的形式。……藝術家靈感產生時的感情,是人們通過純形式對它所揭示的現實本身的感情”,川劇《夢回東坡》已經超出戲曲的顯在本文與潛在本文,進入更廣泛的語境(不啻于人物安身立命的時代)了,啟人深思,耐人尋味。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看戲如觀人生,況味各異。通過對川劇《夢回東坡》的鑒賞體察,接受主體既能夠對蘇軾這位歷史實存的“名人”有更為深刻、全面的理解和認知,也能借川劇的藝術表演、獨特韻味來感知這位堪稱“全才”(詩、詞、書法、繪畫、建筑、醫藥、廚藝等皆通)的北宋文學藝術大師的文采風貌與別樣情志。在觀賞過程中,創作主體(也作為審美客體)與接受主體(也作為施動對象)之間的眉目交流與傳神際會,亦能讓他們一同經歷戲中歷史人物所經歷過喜怒哀懼、悲歡離合與生死況味。這是戲劇的魅力、文化的魅力,更是生命的魅力、生存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