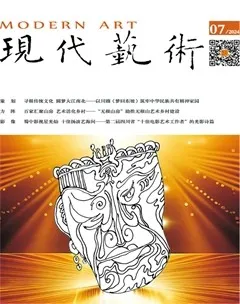以詩入夢 詩戲凝構
第五屆四川文華獎劇目大獎作品、大型新編歷史川劇《夢回東坡》于近期完成了二十多場全國巡演。該劇憑借深刻的思想內涵、精湛的舞臺表演及別具一格的藝術手法,贏得了觀眾的一致好評。它不僅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川劇獨特的舞臺韻味,更為人帶來一場深入心靈的精神共鳴與藝術審美的雙重享受。其中,詩詞的巧妙融貫可謂本劇目的一大亮點。蘇軾的詩詞在著名川劇表演藝術家陳智林先生的生動演繹下,具象呈現了詩詞背后,作者的人生軌跡和心路歷程。角色飾演者渾厚激昂的唱腔、扣人心弦的詞曲,恍若將觀眾拉入歷史情境,進而完成一場跨時空的藝術表達,使其精神煥發,余韻悠長。
川劇本就與詩詞密不可分,不少作品或以詩詞為劇作藍本,或將詩詞轉化為唱詞戲歌,進而形成詩戲渾然一體的美學范式。《夢回東坡》的詩詞嵌入不僅是文體之間的相互滲透,更深層次地體現了中國式精神情思和詩性審美。它通過將蘇軾經典詩詞中的圖景與情思巧妙融入戲劇,精心刻繪了一幅生動立體的舞臺畫卷,同時構建出蘇軾意蘊深遠的精神世界。這種融合以川劇為載體,以詩歌為路徑,托物言志,直抒胸臆,既還原了真實立體的蘇軾形象,豐富了戲曲藝術的表現形式,也給予了觀眾更深刻的藝術享受和思考空間。
一、敘事塑形:詩與戲的交融
顯而易見,詩詞的選擇、嵌入不能脫離故事、情感的發展,需要符合作者對理想的追求及故事情境的規定性,也需要符合人物當時的心境。詩詞在戲曲中能推動情節發展、深化主題、塑造人物、抒發情感,同時還能提升其韻律美與文學性。在《夢回東坡》中,詩詞在念白、唱詞中的融合,并非根據敘事需求和時空背景直接嵌入,也非一味追求詩詞的完整性呈現,而是考慮到人物表演及角色情緒的需要而融入,多起到畫龍點睛的妙用。《夢回東坡》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展開一場對蘇軾“一生”的尋跡之旅,時空的壓縮重構成為必然,而多借高度的概括、提煉來完成敘事、表意的詩詞,作為超脫現實世界與空間束縛的藝術形式,也恰好與戲曲在敘事時空上存有充分的一致性,互滲、互嵌自然而然。
(一)“夢回”的多維空間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夢”是蘇軾詩詞中常見的表現對象和敘事空間,有了“夢”這一設置,劇目表達的情景內容得以拓展,現實時間、敘事時間和文學時間得以流轉交融。從客觀層面出發,劇目從一場蘇軾與父母對話的“夢境”開始,夢境的植入類似于電影的蒙太奇手法,構建了多元的敘事空間邏輯,此時的戲劇時空以“夢回”為載體,詩詞與念白、實景與夢境交替出現,時空在詩詞帶來的“虛”的世界與演員帶來的“實”的現場表演中自如流轉,舒緩、從容地完成詩意空間的建構,創造了更為豐富的觀看體驗。
夢境帶來的“實”與“虛”也體現在對蘇軾精神層面的表達上。其實,蘇軾的“夢”更像一場其追逐精神世界的愿景。將蘇軾置于當代觀眾的視野下,以“夢回”的形式進行連接,將其本人的詩詞貫穿其中,通過演員的演繹完成情境再現,從而帶領觀眾體悟一場跨越千年的精神世界。詩酒帶來的夢中情境與失意歲月的生活情景交替出現,互相交織,不僅見出蘇軾本人的人生觀,也讓人于浪漫與現實的交疊中體悟了獨特的“蘇式”哲學。
(二)詩以道志
《莊子·天下》曾提到“《詩》以道志”。縱觀蘇軾一生,坎坷的人生經歷與樂觀自強的生活態度都與詩詞密不可分,以詩詞抒發心中感悟,又以詩詞為精神寄托。戲中演繹了其妻王閏之為其保存詩稿盒子的橋段,令人印象深刻。蘇軾對詩匣的珍視,也是詩于蘇軾而言尤為重要的具象展示——蘇軾以詩寄情,詩是其精神世界的載體。
將詩詞融入川劇唱詞與念白,無疑能凸顯作品的情緒體驗,也能直接外化人物心境。詩詞本身寄寓的情緒感染力,加以張力十足的舞臺表演,便極易使觀眾產生心理植入效果,繼而強化自身藝術感知力。在“黃州悟道”一場中,蘇軾的遷居場景被詩詞賦予了深刻的藝術感染力,生活拮據但依舊灑脫的蘇軾即景生情:“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該詩句出自蘇軾的《遷居臨皋亭》,巧用于此,不僅揭示了蘇軾此時內心的困惑、掙扎、無奈,也讓人一睹其自嘲、灑脫、無畏的情緒。實際上,這種種身不由己的無奈實是前一場戲“烏臺詩案”的失意延續,但蘇軾所流露出的自洽精神,也與當代人所追求的現代生活哲學觀相扣合——臺下的觀眾此刻與臺上的蘇軾在精神層面上產生了強烈的跨越古今的共鳴,讓人深刻體悟到詩與精神的永恒魅力。
在全戲結尾處,蘇軾以一曲《定風波》傾訴自己一生的回望與感慨,他大聲吟唱:“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這不僅僅是對自然風雨的泰然處之,更是對人生波折、坎坷的豁達與坦然。戲劇舞臺上演員的出色表演與詩詞原文達到了形神合一的佳境,觀眾此時既能夠感受到蘇軾那種無奈中的自嘲、灑脫中的堅定,也能體察到他對生活與命運的深刻感悟。
詩詞通古今,得雋之句,與今人相接。之所以雋永動人,既在于其精神與人類情感相通,也在于其體現出的獨特的中國式審美意趣。《夢回東坡》成功地將詩詞與戲劇相融合,使得不無現代性的“蘇式”精神世界與哲學意味得以于千年后生動綻放。
二、審美范式:視聽與情思的雙關
詩詞作為獨特的語言文本,在本體上具有節奏美、音樂美與人文美。《夢回東坡》將詩詞融入創作,詩詞文體結構與川劇曲式結構互文,詩詞的文學性與川劇的藝術性也有機結合,美美與共,繼而完成了一次中華傳統詩詞、古代傳統文人的具象化藝術表達,不僅有較高的文化價值,也為川劇創新以及有效傳播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載體。
借意蘊悠遠的詩詞與川劇通俗獨特的唱詞交替,《夢回東坡》生動具象地塑造了蘇軾既是文人,也是草根的人物形象。詩歌與戲劇共構的虛實相生的空間中流溢出獨特的中國式象征審美,有機實現了詩歌與戲劇的藝術統一,當然,也完成了當代藝術家對蘇軾精神世界的理解與表達。
詩詞的嵌入所帶來的節奏韻律能充分體現創作者的匠心。摒棄大段詩詞的生硬嵌入,而是巧妙地將其分開融入戲詞中,交替出現,彼此呼應,便能在聽覺和心理上都掀起情感波瀾。詩歌本身的韻律與節奏融入川劇獨有的輕松、幽默的對白或調侃,便會持續不斷地撥動觀眾的心弦,引領其進入情感世界。當戲中蘇軾吟誦《念奴嬌·赤壁懷古》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詩詞吟詠與唱詞——“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交替出現,對話、吟誦、吟唱多種表演方式融為一體,不僅完成了蘇軾與古人的跨時空對話,也完成了今人與古人的跨時空對話,而此時舞臺上電閃雷鳴的舞美效果則將藝術效果推至高潮。
角色扮演者以超凡脫俗的表演技藝,將詩詞的文本之美轉化為劇場空間內自由揮灑的生動場景,使觀眾仿佛置身充滿藝術氣息的時空中,深刻體悟川劇藝術所帶來的恒久且深刻的審美體驗。在演繹蘇軾與妻子王閏之訣別時的詩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時,演員不僅較為精準地還原了詩詞的意境,更通過自然流暢的表演,將情感的真實性與氛圍的藝術性有機融合,并發揮到極致。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演繹不僅僅是“還原”,更是深入到了角色的靈魂深處,讓觀眾在真摯的審美愉悅中,體察詩詞背后的雋永蘊涵。
三、“血脈覺醒”:縱橫多維的藝術對話
戲中令觀眾印象深刻的經典詩詞演繹與再現的片段,不斷地在社交媒體中被提及,可謂是“自帶流量”。正是這些詩句喚起了獨屬于中國人的“血脈覺醒”,也喚起了國人的文化自信。《夢回東坡》中再現的詩詞,多是觀眾耳熟能詳的經典之作。似2024春節檔火爆的動畫電影《長安兩萬里》的詩詞嵌入,影片同樣賦予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內涵。值得一提的是,該片因其對傳統文化的巧妙運用,已被多所學校納入數字化教材。同樣,《夢回東坡》也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詩歌文本的戲劇化演繹也激活了傳統詩詞的可視化表達。這些承載國人記憶的經典詩詞,作為文化瑰寶,古往今來,總能激發不同時期國人的文化自信;作為深深烙印在國人心中的集體記憶與瑰麗想象,也承載著中華民族厚重的情感期許與審美認知。當《夢回東坡》中蘇軾深情詠嘆“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江城子·密州出獵》)之時,觀眾無論耄耋或孩童,都會不自禁地沉浸于這激昂的詩意中,空間的界限于此時仿佛被打破,情感的共鳴也悄然升起,臺上臺下共同營造了一場震撼心靈的視聽盛宴。
思及新時代的藝術創作,美學境界與抒情精神并存,守正與創新并行。《夢回東坡》詩詞的嵌入對于新時代川劇藝術的創新和傳播,無疑具有深遠意義。可以說,正是因為有詩詞的烘托,《夢回東坡》才有了突出的文化性——詩詞賦予其更深厚的文化基因,激發觀眾濃烈的文化自信。毋庸置疑,川劇作品聚焦本土歷史文化,通過“還原”人物解讀歷史,而且匯通古今,借川話音韻、川人精神將巴蜀人文的性格特質與文化地域特征盡情展露,從而更好地推行了文化傳播,并散發出卓然的文化活力。
很顯然,詩詞在川劇作品中的嵌入在提升自身藝術表現力和視聽體驗感上有著重要意義,但這種嵌入式的藝術構思不僅要在藝術創作上具備美學意義,更要在文化傳播上體現出一種精神責任。《夢回東坡》的詩意演出所帶來的永恒,觸發了當代人的反思,喚起了觀眾的人文感知力,重塑了中華美學精神的表達。換言之,這種可謂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的藝術創作,既是對傳統戲曲藝術表達形式的一次成功革新,也是對川劇跨文本傳播路徑的深度思考與有益探索,在彰顯傳統藝術魅力的同時,也為川劇這一傳統劇目在新時代的傳承與發展開辟了嶄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