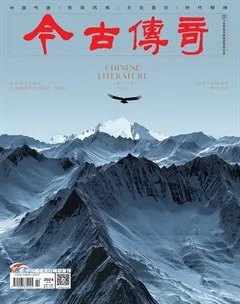“在草尖的低矮處開出白花”
“刺點”也即“痛點”,拉丁語原為“Punctum”,是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在他一生最后的著作《明室》(La Chamber Claire, 1980)中談論攝影時所用的術語之一。巴爾特指出,人會死亡,當時之物也會逝去。但通過攝影,我們卻能通過瞬間進入平靜,從而進入永恒的死亡之中。巴爾特所說的能讓我們從瞬間進入平靜的應該就是被攝影師抓住的“當時之物”,是能夠喚起一個人記憶或情感聯結物的“刺點”。可以說,“刺點”是一種“偶然之物”,“不僅刺疼了我,也傷害了我,使我痛苦”。作為畫面之外的一種東西,“刺點”“簡短、活躍,動作敏捷得像猛獸”,足以從文本細節和局部將畫面“引向一個身心交織在一起的人的絕對優美”。換言之,“刺點”以其偶然性、無名性和未編碼性,不僅“將照片轉喻式地打開到一個與記憶和主觀鄰接的領域”,更是喚起畫面之外的精神向度。
詩歌,也當如是。詩不僅是記憶的虛構之物,也是存在的詞語性創建,詩的本質應該是“傾聽、回應、建構存在”。詩人呂煊的新作《鄉村新物語》中就充斥了大量巴爾特意義上的“刺點”。正是通過這些刺點,詩人呂煊不但重構了他的記憶,也由記憶建構了他的精神空間。盡管這些精神空間被現代性浪潮侵襲和消磨得明顯有些逼仄和荒蕪,甚至成為記憶之上的“廢墟”,但這“廢墟”卻某種意義上成了詩人的神性空間。借由這些空間,呂煊也從詩的虛構與審美意義上找到了回家的路,與曾經的、業已消失的、正在消失的,但事實上正在漸行漸遠的鄉村的田園、美好以及懷舊建立了一種存在論意義上的聯系。正如陳思和所說,“作家在創作的背后有一個完整的理想境界,這是他對自己的創作應達到的境界的期待。這種期待有時候是作為無意識存在于作家的創作心理中的,可能連作家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但它恰恰是藝術最真實的體現”。呂煊通過詩歌寫作期待達到的理想境界,就是找到人與世界聯系的方式。這個世界不僅僅是鄉村的、記憶的而是人的自我的、靈魂的世界,是人與宇宙、人與萬物的應和,類似荷爾德林意義上的“回家”(Heimkunft)。那么,貫穿《鄉村新物語》的核心關切是什么?為何呂煊詩歌文本中的細節也即“刺點”如此重要?詩人到底怎樣通過詩歌建立了與精神空間的聯系從而有了“回家”的聯系?
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還要從《鄉村新物語》中各種各樣的“白”這一情感對應物入手。白花、白雪、白火焰(悖論)、白冰棍、白月光、西湖暮晚霧色里的白,等等,這充斥詩歌中的“長長的白”,讀來就如詩人自己的發現一樣,“有點清凈”。不僅清凈,更是有些憂傷。這些白的緣由究竟是什么?什么是這些白的源頭?這清凈的一簇簇的關于白的物象,對呂煊詩歌意境和抒情風格的形成到底有何作用?這些關于“白”的種種意象或物象等“刺點”也成了我們進一步閱讀《鄉村新物語》的“線索”。白,之所以清凈,是因為詩人經歷過、看過、見識過,看過了、經歷了、見識了便也通透了。讀《鄉村新物語》之前,我們并不知道詩人呂煊的成長和教育背景,不過筆者也無意要知道他的背景,至于他的家庭、教育背景乃至創作的現狀和思路都是陌生的。我們相信,文本自己會說話。閱讀文本,最直接最感性的層次就是你直面文本時的那種感覺。按照巴爾特的觀點,一旦文本形成之后,作者已經“死了”,不是作者而是文本道出了一切。至于呂煊有沒有鄉村生活的經歷、經驗或者鄉村體驗,這些記憶究竟是美好的、傷感的、憂傷的、喜樂的,都不重要,因為詩人通過一長串躍然紙上的關于白的或和白有關的意象,早已形構了他的詩歌“故事”,那就是清凈的、憂傷的,帶有一種悲憫的鄉村的新的“物語”。
“物語”實則是“故事”,是營造的“虛構”的“故事”。創作于11世紀的《源氏物語》(1001—1008)是日本平安時代女作家紫式部的一部長篇小說,描寫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經歷和愛情故事,全書在貫徹寫實的“真實”美學思想的同時,也創造了日本式浪漫的“物哀”思想。呂煊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想必在他命名這部詩歌作品時就已經有意識建構自己的“故事”了。呂煊的“鄉村物語”是都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之后的“故事”,是鄉村在現代性的侵蝕之后逐漸從“地方”到“無地方”的“故事”,是人類逐漸被后人類改變,試圖在新的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竭力和諧共處的掙扎中保持“地方”和獨特主體性的“故事”,是后人類主義時代鄉村的“新故事”。如果從這些要素出發來考量呂煊的詩歌,不難理解為何詩人筆下要呈現出那一長串“長長的白、有點清凈”的“物語”。可以說,這是他竭力從“低矮的草叢中”,用美的、抒情的、詩的語言,為后人類主義時代的鄉村綻放出的一簇簇“白花”:純凈、懷舊、憂傷、無奈。
值得注意的是,呂煊詩的底色是勿忘我的淡淡的藍色,哀而不傷。這些低矮的草叢中開出的白花,是一種早已經飄落在故鄉的鄉愁。詩人很明白自己當下的感受。所以,他用《鄉愁在故鄉飄落》命名詩集《鄉村新物語》的第一輯。這一輯在筆者看來是全詩集中寫得最好的部分,抒情、純凈。“清明的雨”“細雨”“梅花”“荷花”“燕子”“喜鵲”“小滿”“杜鵑”“白鷺”“白雪”,等等,關乎鄉村的“物”語。清明和小滿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時令或季候,其情感聯系的是傳統的農業社會,這無疑是呂煊記憶中有一些懷舊色彩的鄉村。這些時令聯系的是專屬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記憶,留有農耕時代的印記,如清明踏青、祭祖,小滿收麥、插秧等。燕子和喜鵲都是農村或郊外尤其是鄉村常見的鳥兒,伴隨著一年的春天來臨時的歡欣和喜訊到來的悠長記憶。梅花、荷花、杜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常見的花兒,凝結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審美情緒,但又因其傳統也成了古典詩詞中常常吟詠的對象,關聯著傳統的農耕社會,順理成章地作為抒情物隱藏在詩人的文化無意識深處。
上述情感之物中最為獨特的還屬白鷺。白鷺經常出現在江南的田間阡陌,在呂煊的詩歌中,他如此描述白鷺,“一只白鷺從我們的頭頂緩慢飛過,振翅收腿,讓我目睹了它飛翔的嫻熟和安詳”。可以說,白鷺正是詩人在經歷了許多人生坎坷和磨礪后的一種寫照:嫻熟、安詳。“我隨著白鷺穿過悶熱的岳園”,是詩歌《隨著白鷺穿過悶熱的岳園》的題目,也是他這首詩的最后一句,詩行至此,戛然而止。“當時之物”映入眼簾,詩人迅疾寫下,寫下便是刻下,從瞬間進入平靜。嫻熟的安詳是詩人向往的一種感覺,是詩人期待讀者感受到的一種感覺,而這種感覺給予讀者的也是一種心靈的“觸動”,一種“情感的觸動”。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認為,我們要回到實事(物、意象)本身,就意味著回到先于認識而認識又總是要談論的世界。他反對自然主義或唯科學主義的立場,批評它們把科學的觀念看成實在的鏡子,設定自在世界,認為真實的意識可以用因果關系的形式與之發生聯系。梅洛·龐蒂指出,不存在內部的人,因為人總是在世界之中,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認識自己。有鑒于此,白鷺既是呂煊的向往,也是他的自喻,是他心里曾經有的但卻在現代性的進程中逐漸遺失的一種東西、一種情感之物。此時的白鷺,既是作者靈魂的投射,也是威武、靜穆的岳園的投射,是詩人與外界之物互相對應并經過情感沉淀之后的另一重“投影”。
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在1817年4月寫給朋友J. H.雷諾茲(J. H. Reynolds)的信中這樣說道,“我認為詩的驚人之處在于一種美妙的充溢,而不在于稀奇少有——讀者被打動是由于他自己最崇高的思想被一語道破,恍如回憶似曾相識——”或許有讀者或評論家認為,呂煊此處將白鷺與岳園并置而非將白鷺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更遼闊的空間,相比經典古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等,詩人的格局有些局限,不夠寬廣。此言不差。但是,呂煊畢竟希望的是從鄉村的物象中找到心靈的投射,而白鷺此時從岳園的悶熱穿過,帶給詩人和讀詩人心靈的沖擊是一種遇到知音的“美妙的充溢”,是詩歌之外業經語言編碼后而帶來的另一種清涼和寧靜。筆者生活的家鄉河網密布、阡陌縱橫,伊水之濱,白鷺點點。從呂煊的詩中,筆者看到的不僅僅是帶給詩人的一個個“刺點”,也是帶給筆者的一個個“刺點”,白鷺就是其中之一,“恍如回憶似曾相識”。白鷺、呂煊、鄉村、岳園,人與物、人與非人、人與自然、人與世界,互為“分形”,互為映射,不僅構成了詩歌文本結構深處的一種對話,也為詩歌文本建構了多重的彼此映射的空間。
這個多重的彼此映射的空間,便是呂煊的精神空間,也是他的精神家園。如果說鄉村以及對鄉村生活的“刺點”的表征和摹寫構成了呂煊詩歌的精神空間,那么,這些精神空間也在呂煊一次次的描摹、表征和吟唱中,成了他的神性空間。“孤獨”是一種扎根于現代性的群體性心理境遇,或可用本雅明意義上的“碎片”來形容。“碎片”隱喻的是人與人關系的割裂,也是現代性語境下社會專業分工和流水線生產和生活導致的對事物的體驗的破碎,更是人與世界母體之間血脈紐帶被斬斷后的異化狀態。詩人是孤獨的流浪者,呂煊也不例外。詩人的高敏感性使得他對現代人的孤獨、流浪和碎片化的體驗更甚。身處都市化和全球化壓迫的逼仄的都市空間之中,詩人“歸家”不得,只能一次次地通過詩的語言,不停地呼喚他的精神家園,呼喚家園的出場。吊詭的是,每當家園出場的時候,這些曾經的家園卻也成了被現代性解構了的陌生物,再次成為“刺點”。正如呂煊在《白雪返回大地的瞬間》這首詩中寫到,“火焰的白,猶如白雪返回大海的瞬間/凝固的冷,是一場雪相遇另一場雪后的白”。詩人此時喚起的依然是詩人和讀者心中傷痛的“刺點”的“白”。“白”不僅僅是一種顏色,儼然成了一種虛無、一種虛空,是狀態,是境遇,是心境,這種“白”可以是火焰的白,也是熱情的白,是飛蛾撲火似的熱情之后的白的虛無,是皎潔的白雪與深邃的大海的相遇,是大自然中的一場雪相遇另一場雪后疊加的白,是一個靈魂的純潔與另一個靈魂的純潔相遇之后的白的生成。“白”此時有了程度的疊加、迭代,乃至一種意義上的生成和升華,是年少熱情之后中年的淡然,是心靈柔軟與柔軟相撞之后的超越,不僅是寬厚,也是博愛,大有風浪過后或者經歷了歲月的風霜刀劍之后,一切釋然之后看淡了的“白”。這是一種“有”之后的“無”,看過豐富的另一極端,便是簡潔。事實上,對類似這種經歷的情感的抒寫在呂煊詩集《鄉村新物語》的其他分輯里,也有呈現。此處為了不多分叉,暫不贅述。
說到精神空間,一定要說到呂煊詩歌中借由一個個刺點呈現出的“神性空間”。他用詩的語言賦予具體的人和物以一種所謂的“神性”。在呂煊的詩中,鄉村永遠在場,但這些鄉村也遠非舊時和記憶中的鄉村,鄉村不再是呂煊筆下士大夫的鄉村,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田園牧歌似的鄉村。鄉村不僅在場,但卻往往隱匿,鄉村與呂煊之間,既呈關聯的關系但又若即若離。呂煊的詩中,這些有關白色的各種物和意象所呈現出的鄉村世界,早已明日黃花、物是人非。那里,他的親人漸行漸遠,父母也已遠去,停留在詩人筆下的除了記憶還是記憶。這些記憶不僅一次次縈繞而又一次次徘徊,熟悉而又陌生,在又不在,使得呂煊的詩歌文本在懷舊和傷感的美學氛圍之余還縈繞著一種“暗恐”(uncanny)的美學效應。這種暗恐的美學效應無疑成就了呂煊鄉村美學的另一特點,那就是“廢墟”。
作為一種心理學術語和審美范疇,詹池(Ernst Jentsch)、蘭柯(Otto Rank)、奧托(Rudolf Otto)、雷克(Theodor Reik)等精神分析學者都討論過暗恐的豐富所指,最終將這一概念系統化的當屬弗洛伊德。弗氏不再拘泥于自笛卡爾以來西方哲學將熟悉與奇異二分的觀點,認為暗恐是一種長久被人熟悉的“在家”感突然在無任何預兆的條件下出現而帶來的恐懼感。換言之,暗恐是“壓抑的復現”的另一種表述,不熟悉的其實是熟悉的,非家幻覺總有家的影子在徘徊或暗中作用。弗洛伊德認為,內心重復的沖動最令人震驚的結果之一就是復影的出現,這種自我擾亂不僅能喚起暗恐感,還伴有閹割、失落和死亡恐懼。暗恐是一種“奇特的熟悉與陌生的混雜”,具有典型的雙重性和混沌性,畢竟暗恐本身的熟悉的不熟悉、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意識中的無意識,使其有了一定的悖論性、不確定性和含混性等重要的負面美學效應等。就呂煊的詩歌來說,鄉村的在場和不在場以及鄉村物象等“刺點”的重復出現,實際上喚起的不是一種欣喜,而是一種壓抑物的回歸,是一種徘徊在我們所有生活在當下的人的內心無意識深處的“缺席的在場”。
鄉村是一個徘徊在我們當下每個人生活深處的“幽靈”。換言之,鄉村是現代性驅逐而又驅逐不去的“幽靈”。只有正視這種充滿暗恐感的“幽靈”,用詩歌將其拉入主體的關系場中,詩人尋找并希望回歸的“家園”才不至隱匿。回到本文伊始時我們提到的巴爾特的觀點,巴爾特認為,只有將“刺點”用攝影的方式記錄下來,我們才可能“由瞬間進入了平靜,進入了永恒的死亡之中”。事實上,通過對鄉村這一廢墟之上各種“長長的白”的“刺點”的書寫,詩人也讓他的鄉村“物語”有了出場的機會,更是得以讓他的精神家園進入了一種文學意義上的永恒。莎士比亞曾借他的十四行詩第十八首早就說過,只有將美寫進永恒的詩句之中,美才不至于如英倫三島的夏季一樣轉瞬即逝。呂旭不僅借由詩歌為他的“鄉村”建構了新的“物語”,并由此去擁抱他的記憶,擁抱他與父母和家鄉親人的聯結,擁抱他的精神和靈魂;同時,他也借由詩歌這個虛構之物與上述事物一同歸入永恒的平靜之中。這是一種福祉,是詩歌帶給他的福祉,也是一種潔凈,是詩歌帶他“回家”的潔凈。
詩歌本身就是文化的刺點。詩歌拒絕定義,也拒絕學理。唯有在沉思中敏悟,而又在敏悟中突破。詩歌不需要詩人刻意制造“陌生化”,反倒需要寓深意于平淡的方式來制造“刺點”。呂煊并沒有在他的筆下構建宏闊而又虛無的廟堂之說,而是用樸素、平實的語言,記下了一個個普通但并不凡俗的“刺點”,為他本人,也為與他一樣的曾經的一代人,照亮了“回家”的路。在這個神圣而又純凈的“廢墟”之中,一簇簇白花正在痛苦中生長、綻放,它們當如中秋的一輪皓月,照亮呂煊,也照亮讀詩的我們。
張小平 任職于揚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責任編輯 王仙芳 349572849@qq.com)
- 今古傳奇·當代文學的其它文章
- 影響力人物——彭四平
- 少年的祈禱
- 雪落又新年
- 讓每一朵花都守住芬芳
- 天路故人
- 傳奇書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