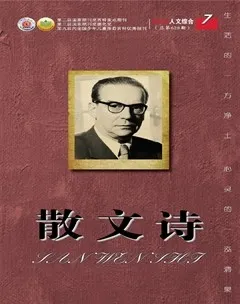娃娃音(外一篇)
高一沒分文理科時,聽見有個班里傳來一種小孩子的聲調,不是突然一時興起的發音,而是一位老師,持續用這種小女孩的聲音在講課。當時,我只是無意路過,不巧,接下來就是學生大段地齊讀,于是,新鮮、陌生的聲音就那樣不翼而飛了。
之后,又聽見過幾次同樣的聲音,才知道這位老師教語文,又細又高的女聲,每個字卻發得很重,像結實的蠶絲,被不竭地吐出。老師本人也長得小巧玲瓏,不知道臺下的學生們聽著這樣賣力地講授,會不會格外專心。那道蘊含能量的溪流,反正是吸引了我好奇的聽覺,并中斷所有思索,探秘一般將其吸收。
終于有一次,那位老師要在我們班講課評優。
她姓江。
近距離聆聽這一波接一波的細嗓音大肆涌入耳中,像空山鳥啼,似春江水唱。或許那是一種獨特的生理構造,讓一個成年女性保留了孩提時的音調,卻絲毫不減職業的負荷,這聲音,不是矯揉造作,也不是嘩眾取寵,反而有著一種天然的可愛。細細的聲線,在講課時行云流水一般,但一到了重要的知識點,就輕柔而變高亢——這種對知識擲地有聲地傳達,是真正的言傳身教,讓人無法不專注,無法不感動。
我們那時還不知道娃娃音,至少我是沒聽說過的。畢業很多年后,看到某些女明星的嗲音火遍媒體時,我才猛然想起,那位江老師,不就是這種天生的娃娃音嗎!
某次聚會,一位女同學回憶說,江老師教文科班《林黛玉進賈府》那一段,在晚自習時,寫了滿滿一黑板的金陵十二釵判詞及詩文。她在下面正抄到《葬花吟》,結果,老師又拿板擦,將它們擦去了,干干凈凈,一字不留。這是專供她自我陶醉練字玩嗎?
——就是花謝花飛花滿天?
——這你都要抄,怪不得你那么矯情!
——哪里啊,我以為是要背誦默寫的。
——她就是矯情,上學時對人愛答不理的,說是呀要學黛玉一樣清高……
我記得這位老師的粉筆字:行楷,筆筆帶鋒。如果那時候就有智能手機,不就可以直接記錄下那整整一黑板的經典古意了嗎?可又一想,若是有了手機,那些詩句不是更方便快捷地直接搜到,也就沒人在意老師的手寫板書了嗎?十二道精致書寫復又被匆匆擦去的判詞,十二個有血有肉的薄命女子,經由這位弱柳扶風的女教師之手,瞬間發出了怎樣聲嘶力竭的不甘呢!
你們老師平常也那樣說話啊?
剛剛還在打鬧的同窗們停了下來。
是的,那聲音不是裝出來的。那位朋友對我的疑惑心領神會。她有小半年聲帶囊腫手術期,于是,換了另一個年輕的代課老師。
老同學難以置信的話語,聽著淡淡的,我們卻都惻然沉默了好一會兒,好像是要讓那如娃娃音的講課聲再次縈回各自耳畔,輕輕亮出一道赤子般淳樸的底色。平凡如她,注定敵不過大明星的影響力,卻將一種春風化雨般的恩情給予了我們,將一種天然不雕飾的精神永遠鞭策著我們——
今后的道路上,也一樣。
夜 曲
下雪了。
雪籽兒,星星般一顆一顆降落,打在玻璃上。“啪啪”的聲響,那是一泓湖水蕩漾耳蝸的形狀。
城里的新式大廈上下雪了,鄉村的老舊屋瓦也在白頭。我知道。于是,我起身,去找一張白天偶遇的照片,來自一位古典詩詞愛好者的雪天集錦。
照片,取材于一排集裝箱廠房后的建筑小樓。很多年前,我住處附近的一棟藍玻璃建筑通過它,再次映入眼簾。
四層的整體大樓,據說是某家國企的行政辦公場所。每層面朝國道的走廊,均由嵌著亮閃閃的藍玻璃鋁合金窗戶封閉,在周圍松杉、綠樹與壟壟莊稼地旁窄小私房的簇擁下,透出極具規整格調的現代化氣息。
窗戶梭到左還是右,光線打在玻璃上是藍還是綠,這些簡單的細節,曾經是我每個早晨與傍晚都會路過的板正與活力。
還是那個方向,我回到了以前這座大樓所在的地方。它像在舊照片里一樣,被我經年凝望:四方齊整依然,高大到能俯視周圍所有廠房純白的屋頂。只是在拓寬不少的道路一側,仍如倒伏的枯草般,泯然眾人矣。
每一層鋁灰的窗框尚在,大半窗戶已經缺失,仿佛洞開無遺,不復威嚴的老人大嘴:走廊斑駁的白墻,撕去一半的春聯,歪歪扭扭的晾衣繩,無人問津的衣裳……潦草的世俗涂鴉,訴說著世事變幻。
樓房外圍,一如從天而落的大雪,鐵質豎條醒目的銹跡……把重重的時光倒影沿貼著瓷磚的墻壁,連同五花八門的小廣告、小印章,一道道烙上紛繁的記憶里。新裝的空調,以及天線小鍋,有高有低,挨挨擠擠。仿佛那些年齡不一的歸來者,分散著,站立原址上,有的目光,在回望往昔的歲月;有的眼神,閃爍遠方的深邃和奇妙。
——萬物皆有情啊!
雜草叢里,一條瘦狗,鉆進一樓那間被人斜著撬開的卷閘門內,尾巴向外面沖著。
“汪汪”的叫聲中,一股暖意流遍全身。
我重新躺下,像一個孩子鉆進一場雪夜的安眠。
我相信,今夜的夢境,一定是皎潔的。就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