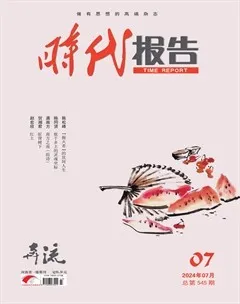人情味兒
我是一個愛聽故事的人,但因記憶力差,嘴舌笨拙,自己卻很少講故事。下面這個故事,是在去年我到湘西張家界旅行途中,聽當地導游阿浩講述的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
阿浩是地道的苗族人,出生在湖南張家界桑植縣大山深處。大學一畢業,就干起了導游職業。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導游業績,全是靠嘴。阿浩個子不高,聰明伶俐,嘴巴微翹,能說會道。用同行阿哥的話說就是:
阿浩就像沱江的艄公,很會見風使陀,“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剛上班不久,阿浩在旅行社就混得“風生水起”,“銷售明星榜”上時常看到他的名字。那是疫情前的一天,阿浩帶了一個“散客”拼團。聽口音來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奔張家界名氣而來。
觀奇峰怪石,乘索道天梯,聽民間故事,賞苗族風俗,旅行團成員個個興高采烈,興致盎然。唯獨一位50多歲的山西阿姐顯得有點兒“另類”。她一直緊鎖眉頭,悶悶不樂,與景與人與情格格不入。
阿姐形干瘦,面憔悴,色如“干絲瓜”發灰發暗,她不像其他人一樣:或三或兩結伴而行,而是一個人特立獨行。她不是被遠遠地拉在后面,就是一個人坐在高處望著奇峰異石長時間發呆。
阿浩心里一直在打鼓,從一開始就盯上了她。根據阿浩的帶團經驗,外出旅行大多為親朋好友相約,情侶夫妻相伴,扶老攜幼結伴而行,而阿姐卻一人報團,獨自旅游。
一個外出旅行,都是有故事的。阿浩不敢問,也不想問。他的任務就是把這個團安安全全帶下來,途中說服大家多買點特產,多沖點業績就完成任務了。
可他又一想:絕佳風景處,也是想不開的人的理想歸途路。一旦自己帶的團中出現意外,不要說沒了業績,恐怕連自己的飯碗都難保住。
想起這些,阿浩不禁渾身一哆嗦。他打起十二分精神,追上阿姐,跑前顧后,唯馬首是瞻,當起了貼心導游。
為逗阿姐開心,阿浩使出渾身解數,一路講起湘西趕尸、深山剿匪、婚喪嫁娶等,還不時亮起嗓子唱一段當地的《山歌好比春江水》等民歌。
眾游客邊欣賞奇異的美景,邊聽阿浩精彩地講解,不時拍手叫好!
阿姐看阿浩如此賣力,臉上的愁云也似被清涼的山風漸漸吹散,眼角也慢慢泛起一絲笑意,她心疼地說:“阿浩!您辛苦了。現在像你這樣敬業的導游真不多了!”
“謝謝阿姐!我們苗族人熱情好客,都是這樣的!”阿浩口是心非地說,私下卻暗想,“要不是為了碎銀幾兩,龜兒子愿意這樣。還不是為了下一步的‘重頭戲’購物環節做鋪墊唄!”
直到率眾游客下了山,阿浩終于長長地松了一口氣!
阿浩又馬不停蹄地帶團趕赴購物環節。
“阿浩!你看我買的什么東西?”
剛邁出當地特產超市大門,阿浩被山西阿姐攔腰截住。
“壞事!”
阿浩心里一驚!
阿姐手捧一盒當地特產朱砂,伸到阿浩鼻子下說:
“你聞一聞是什么味道?”
阿浩低下頭裝模作樣地深深嗅了一口,邊嗅邊想:
只要買了不退貨!莫說讓我聞聞,哪怕讓我吃了,我也認了!
阿浩抬起頭滿臉堆笑地答到:
“香味!”
“不對!”
“阿姐”輕輕搖搖頭說:
“阿姐年紀大了,也不抹香水哪來的香味?”
阿浩一聽,心里陡然發慌。阿姐看似柔弱,實則狠人,不好對付也!
“你再聞聞!”
阿姐接著說。
阿浩這次不敢糊弄了!他望望面帶微笑的阿姐,又仔細打量打量眼前紅燦燦“朱砂”,用食指和拇指捏起一撮放到鼻翼下,閉上眼睛,悠悠吸了兩口,足足有十多秒鐘。阿浩隨著呼氣吐出一句話:
“阿姐的汗味!”
“哈哈哈……”
阿姐大笑起來!
她邊笑邊指著身旁兩個鼓囊囊的大購物袋說:
“阿姐雖然快60歲了,但買這點兒東西,還不至于累得大汗淋漓!”
她慈愛地端詳著阿浩的臉說:
“我們都知道朱砂無色無味。但是,它有“人情味兒!”
阿姐喘口氣接著說:
“你們導游也需要養家糊口,也不容易!有時推銷一些地方的特產拿點提成沖沖業績可以理解,但不要太過了!而我們游客,外出旅行一般都要給親友買點兒當地的特產。同時也是對您一路服務的認可和支持。所以要相互理解,適可而止。這就是我說的人情味兒!”
阿浩聽了渾身一顫,心頭一熱,兩汪淚水充盈眼眶。
旅行結束后,阿浩與山西阿姐成了微信好友。每年春節前夕,阿浩都不忘給遠在山西大同的阿姐寄些臘肉等湖南特產,阿姐也給阿浩發來紅包當壓歲錢。
到了2019年,猝不及防的“疫情”給旅游業帶來重創,張家界景區游人日益稀少。阿浩處于半失業狀態!
無所事事的阿浩愈加牽掛遠在千里之外的阿姐,微信聯系的次數明顯增多。可是,不是阿姐長時間不接,就是匆匆說了幾句話就被掛掉。從阿姐日漸微弱的語氣里,阿浩感覺到了一絲不祥的氣息。
阿浩最后一次聯系阿姐時,從手機聽筒里突然聽到旁邊隱約有人說:
“你媽真可憐!你們當兒女的也盡力了。”
聰明的阿浩立刻意識到不妙,阿姐在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他決定立馬趕往山西,去見阿姐最后一面。
可當時受疫情管控,千里迢迢,如何從湖南張家界趕往阿姐的家——山西大同啊!
阿浩租了鄰居一輛出租車,連夜出發。按照所寄快遞的地址,阿浩好容易找到阿姐的家。他敲開房門,一位臂戴黑紗的小伙子望著他,詫異地問:
“您是……”
阿浩顧不上回答,踉蹌幾步奔到客廳。墻上的阿姐正慈祥地端望著她,仿佛在問他:
“阿浩,你咋來了?!”
煙霧繚繞,天旋地轉。阿浩幾乎暈倒,好容易緩過神來,他嘶啞著嗓子,慢慢唱起苗族山歌《哭亡》。
阿浩給我們講完這些,嘴唇顫抖,嘴中呢喃,似乎還沒有從夢中醒來。
此時,我看到他那雙大眼睛里,有兩汪淚水在打轉兒,在陽光照射下,晶瑩剔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