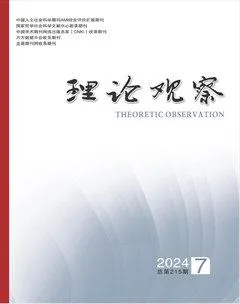再融入鄉土:回流農民工參與農村社區治理意愿研究
摘 要:本文聚焦回流農民工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意愿,利用西藏日喀則521戶農戶的調查數據,運用Probit模型,分析回流農民工參與社區治理意愿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農戶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較高,但參與行為較低;農戶主觀規范意識越高,參與意愿越強;農戶社區歸屬感越強,參與治理意愿越高;農戶回流時間越久,其參與社區治理意愿越弱。
關鍵詞:社區治理;回流農民工;參與意愿
中圖分類號:C915;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4)07 — 0095 — 09
一、引言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城鄉差距的逐步縮小,農民工的回流現象日益成為影響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田夢君等,2023),尋求更多的經濟機會(陶瑋等,2022)。長期以來,農民工作為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的主要勞動力(王大哲等,2022),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馬草原等,2023)。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杜劍等,2023),以及農村地區政策的改革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選擇返回農村(蔡弘等,2023)。
從社會經濟背景看,農民工回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王鎵利,2022)、工作機會的減少(熊穎哲,2022)及農村地區生活質量的提高(李昭楠,2022)。此外,國家在農村地區的投資增加(劉延華,2018),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改善和農業政策的支持,為農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農民工回流可以被視為勞動力市場的自我調整機制(張歡、吳方衛,2023),城市就業機會的不穩定性和農村地區新興就業機會的增加,是推動農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同時,家庭和社會文化因素,如:家庭的責任感以及對鄉土的依戀,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傳統上,農村社區依靠緊密的社會網絡和共同的價值觀來自我管理和發展(柳澤凡,2020)。隨著農民工回流到農村地區,使原有的社會網絡和治理模式受到了沖擊,給農村社區治理帶來了新的動態和復雜性(何強,2020)。這一回流不僅影響了農村社區的人口結構(雷煥貴等,2021),也對社區經濟、文化(王山河,2008)和治理模式(劉玉俠、張劍宇,2023)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經濟層面上:回流的農民工帶回了他們在城市獲得的技能和經驗(閆琳琳、李雙雙,2022),為農村地區帶來了創業和創新的潛力(劉玉俠、張劍宇,2023)。同時,回流農民工通常能夠帶回一定的儲蓄(周春霞,2022),這些儲蓄被用于改善居住條件、投資于農業等,從而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多元化發展;在社會結構上:由于勞動力流失嚴重,使得農村勞動力老齡化、性別比重(失調)日趨嚴重。農民工回流使農村勞動力得以重新分配(張喆,2013),對農村地區生產模式和家庭結構都產生了影響(賀小丹、董敏凱,2021),同時家庭內部的性別角色和代際關系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劉達培,2024);在文化層面上:城市的生活經歷改變了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何淑婷,2023)。農民工的回流對農村社區治理的參與意愿產生了影響(史璇,2016),他們更希望用所學的治理知識應用于農村社區的管理中,推動社區治理的現代化。
盡管學界對回流農民工從不同視角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首先,目前學者研究的數據來源多是中國農民工檢測報告、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等全國性宏觀數據;其次,在研究內容上,對農民工回流后產生的影響分析多從人力資源、技術、就業等經濟角度展開,較少關注回流農民工群體對當地社區治理參與意愿和行為;第三,目前學者更多關注的是東部、中部農村地區,對西部地區關注較少,尤其是西藏回流農民工如何參與并影響農村社區治理方面還未進行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從社區歸屬感、主觀規范視角出發,探索西藏日喀則市回流農民工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意愿進行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以期為少數民族地區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和農村社區治理提供政策參考。
二、回流農民工的概念界定與群體特征
準確把握回流農民工的概念及特征,是本研究的邏輯起點。對于“回流農民工”學術界并未形成一個統一的界定,但其定義基本包含外出時間、回流時間、回流空間的認識等(劉玉俠、張劍宇,2023)。對于外出時間,國家統計局《農民工檢測調查報告》將時間界定為6個月以上;部分學者為了突出回流農民工的外出務工特質,認為時間應在1年以上(楊忍等,2018);對于回流時間的界定,部分學者參照人口普查的定義,認定在“6個月以上”(陳世海,2014)。同時,大部分學者認為6個月難以完全排除城鄉兩棲人口和因處理事務或特殊原因滯留在家的農民工,故回流時間在1年以上才算合理(胡楓、史宇鵬,2013);在回流空間上,一部分學者認為不應區分回流地,只要回流到戶籍所在地(包括農村、鄉鎮、縣城)即符合界定條件(王煒、許幸蓮,2011)。另一部分學者則限定為回流到戶籍所在鄉村,包括本村和縣域范圍內的其他村(胡楓、史宇鵬,2013)。西藏由于受其傳統文化、政府政策、家庭束縛等影響,除極少數農民工屬于長期外出務工外,大部分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屬于季節性轉移。據調查數據顯示:轉移時間上6個月以內的占1.15%;6-12個月的占0.96%;13-24個月的占36.47%;25-36個月占35.12%;36個月以上26.30%。在本研究中將回流農民工外出時間以國家統計局《農民工檢測調查報告》界定為準,界定為6個月以上;回流空間上以回流到戶籍所在地為準。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主觀規范與回流農民工參與社區治理
主觀規范是指個體在行動之前感受到的來自外部的社會壓力,這種壓力往往由社會結構中的社會關系主體對社會中個體施加所產生,如家人、朋友、同事等對某一行為的看法對個體所產生的壓力(鐘驊,2012)。多數學者在主觀規范對個體意愿的影響上進行了相關研究,研究表明主觀規范對個體意愿有顯著性影響。賈鼎(2018)的研究發現環境決策參與的公眾主觀規范會顯著地正向影響公眾參與決策的意愿;張紅等(2015)認為主觀規范除直接正向影響公眾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還會正向影響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態度;對農戶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意愿具有顯著性影響(胡晨成,2023),對參與農業面源污染調控的意愿具有正向影響(李守越,2023)。
農村是一個傳統的熟人社會,社區是由鄰里組成的,大家共同認可社區發展與個人發展的關系,因此,在共同目標的作用下,鄰里是除了家庭成員外對自身行為影響最為明顯的主體,鄰里提供的示范作用,能潛移默化地進入到人們決策思考范圍之內(謝巍,2023)。村民主體對治理的態度受家人、朋友、鄰居的影響,當周邊的人都在積極地參與社區治理,并且鄰里之間有相互監督的效果,會提高居民自身社區治理的參與意愿,更利于村民做出有利于社區治理的行為。以居委會為核心代表的社區治理行動主體,既是制度與政策的基層執行者,又是社區內部多方有序治理的實際協調組織者(何威,2023)。作為基層管理者,村委會或者村干部在鄉村社區治理中處于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對鄉村居民和治理的影響非常大。
個體在做出某項行為決定時會受到他人或社會壓力的影響。在個人行為決策過程中,對其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有三個:包括來自家庭成員、親朋好友的支持或反對,周圍鄰居以及威望和權威人士的認可或否定,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規范和引導(岳羽,2023)。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1主觀規范對回流農民工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1A居委會、政府部門倡導對回流農民工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1B 自我認同感對回流農民工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1C 家人、鄰里支持對回流農民工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社區歸屬感與回流農民工參與社區治理
社區歸屬感維度。社區歸屬感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所屬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認為自己屬于這個社區,愿意為社區的發展和進步做出貢獻。卓文昊(2023)研究發現社區歸屬感及政府動員對社區參與治理意愿呈正相關;葛亞楠(2023)通過研究發現社區歸屬感對居民參與社區治理具有影響作用;李欣(2020)基于鄰里環境因素對社區歸屬感與居住意愿的影響中發現,社區歸屬感對于居住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社區歸屬感象征著居民對社區的強社區參與意愿,是渴望實現真正融入社區的鄉愁(劉悅來等,2023)。回流農民工有一定的社區歸屬感(胡艷華,2014),社區歸屬感也是農民工回流的重要方面,作為農村社會中的村民,都有落葉歸根的感情,所以社區歸屬感對農戶意愿以及行為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本文借鑒前人研究,以“鄰里關系”“領里互助”來衡量社區歸屬感。社區歸屬感越強的人通常更傾向于參與社區治理(徐淑新,2020),他會更加關注社區的事務,會積極參與到社區的各種活動和事務中,與其他社區成員一起共同促進社區的發展。同時,他會更加信任和尊重社區的其他成員,更容易建立聯系和合作。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2 社區歸屬感對回流農民工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A 鄰里關系對回流農民工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B 領里互助頻率對回流農民工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回流年限對回流農民工社區治理意愿的影響
農民工回流年限對于被調查對象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維度——外出務工者,他們在經濟發展更好的地區長期生活,受到當地潛移默化的影響發展更為成熟,形成相應的理念和行為習慣,另一方面常年在外往往具有更為開闊的眼界(陳秋霞等,2023)。回流年限越久,對社區治理事務越有更深入的了解,其治理觀念與在外出務工所認識的治理觀念方面可能存在沖突,可能對社區的治理方式不認同,那么就會對其參與社區治理意愿的選擇有一定的影響。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H3:回流年限對回流農民工參與社區治理意愿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
四、數據來源、樣本特征
(一)調查區域選擇
西藏位于中國西南部,是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也是西部地區推進發展建設的重要地區。西部地區地廣人稀、資源稟賦好,為了合理開發西部資源并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國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西部大開發、西氣東輸等。由于政策的影響,西部地區的產業發展帶動了勞動力需求(張華等,2021),產業發展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大批西部農民工回流。然而,西藏外出務工者存在明顯的地區差距,阿里地區外出務工人數明顯偏低,昌都、那曲次之,而日喀則外出務工人數明顯偏高(孫自保等,2016)。日喀則市也相應出臺多項吸引人口回流的政策,為回流人口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以此提高回流農民工的收入。綜上,選擇日喀則地區為調查區域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抽樣調查與說明
本文使用數據來自課題組成員對西藏日喀則回流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為了保證調查的有效性,課題組成員招募了日喀則當地同學進行調查溝通協助,并對調查員進行農村社區治理的概念與范疇、詢問舉例、訪談技巧等方面的普及。正式調查前,小組成員以林芝市周邊居民為調查對象進行了預調研。預調研過程顯示,課題組設計的變量比較合適,但偏專業化,為保證調研效果,課題組將問卷問題進行了口語化修正。并于2023年12月—2024年3月期間對日喀則回流農民工進行正式調查。調查內容主要包括農戶的個人特征、家庭特征、社區治理參與等方面。調查共發放問卷570份,剔除數據前后邏輯不符及缺填、漏填等明顯錯誤的樣本,最終獲得有效樣本521個,有效回收率為91.40%。
(三)樣本特征
在樣本基本特征上(表1),被調查者男性偏多,因男性居民外出務工較多,女性一般在家持家,所以相應的回流農民工中男性占比會較大,符合其事實;年齡結構上,46歲以上的占樣本總數較少。針對調查對象而言,樣本年齡結構較為合理;家庭年收入方面,收入在15萬元以上的樣本量占比較少;樣本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專(中專)及以上占樣本比重為22.84%,高中程度占22.65%,初中教育程度占37.24%,小學及以下占比較少。總體來說,被調查樣本符合西藏日喀則市實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調查對象在社區治理意愿以及行為方面基本情況如表2所示,大多數回流農民工有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然而,將這種意愿轉化為行動的人數卻相對 較少。只有“意愿”沒有“行為”的參與是不完整的,而只有“行為”沒有“意愿”的參與難以持久。要充分發揮回流農民工的主體性作用,就應在激發其參與意愿的前提下,促進其落實到行為(李曉雅,2022)。
五、研究方法與變量設置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被解釋變量為是否愿意參與社區治理。由于被解釋變量為二值選擇變量,所以本研究采用Probit模型進行研究說明。構建Probit模型為:
Prob(Yi=1|Xi)=Prob(α0Ti+βiXi+εi>0|Xi)(1)
式(1)中:Yi表示被解釋變量,Yi=1表示調查對象有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Yi=0表示調查對象沒有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Xi表示解釋變量;α0表示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Ti表示控制變量;βi表示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εi表示隨機誤差項。
(二)變量設置
被解釋變量:調查對象參與農村社區治理意愿,參與意愿分為有意愿和無意愿兩種。“愿意”賦值為1,“不愿意”賦值為0。
解釋變量:參考已有的關于農戶社區治理意愿研究中顯著的影響因素,將個人特征、主觀規范、社區歸屬感作為本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量。主觀規范維度,借鑒張紅、張再生等學者的研究,調查問卷中設置:“參與社區治理我覺得很光榮”“家人、朋友、鄰居及同事支持我參與社區治理”“各級政府部門、社區居委會大力倡導居民參與社區治理”3個變量來測度主觀規范。社區歸屬感維度,借鑒溫理等學者的研究,調查問卷中設置“鄰居關系融洽”“獲得過鄰居幫助”2個變量來測度社區歸屬感。
控制變量具體包括性別(xb)、年齡(nl)、家庭年收入(nsr)、教育程度(jycd)、回流年限幾個方面。回流年限以時間段劃分,以1-5進行賦值,“回流年限6個月以內”=1、“6-12個月”=2、“13-24個月”=3、“25-36個月”=4、“36個月以上”=5。
六、模型結果與分析
(一)回歸前的檢驗
本研究先把問卷中的數據結合變量賦值整理出來,用stata.17軟件對整理后的數據進行了簡單的變量相關性檢驗。通過表4中結果可知,主要變量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相關,此次調查所得數據通過相關性檢驗,可往下繼續分析。
為保證回歸結果的準確性,還要對樣本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從表5中可以看到,條件索引VIF值都小于10,可知,變量之間不存在共線性或者存在較弱的共線性,說明模型選擇的主要解釋變量是正確的,可以進行回歸。
(二)模型實現
本研究利用Probit模型回歸分析,根據表6回歸模型結果可知,不斷對變量進行交叉擬合回歸,顯著性在幾次回歸后結果基本一致。由此,也更能檢驗模型擬合結果的穩定性以及模型擬合度較好。
(三)結果分析
從表6回歸結果的顯著性來看,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主觀規范、社區歸屬感、以及回流年限方面,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性別和年齡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從模型(3)結果來看,受教育程度對治理意愿影響顯著(P<0.05),回歸系數為0.203,在維持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受教育水平高的農戶在一定程度上有更高的認知能力,能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農村社區治理,在社區治理方面有更高的參與的意愿。受教育水平高的農民擁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強,這些都會提升農民對農村社區治理的參與意愿(孫琦,2023)。家庭年收入水平影響效果顯著(P<0.01),回歸系數為-0.271,說明家庭年收入越高,相應的農戶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越低。從受訪對象看,家庭收入高的家庭,家庭成員大都工作較忙,他們更傾向于關注自己的職業發展和經濟利益,對社區治理方面相對投入關注度較少,因此使得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下降。
主觀規范維度影響效果顯著(P<0.01),對回流農民工參與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的正相關影響,H1 假設得到驗證。如果一個人感受到的來自社區成員的支持和期望越高,他可能會更傾向于參與社區治理。且一個人認為自己有能力為社區做出貢獻,并認為社區治理是符合自己價值觀的事情,那么他可能會更傾向于參與社區治理。社區治理會讓自己產生一種成就感、自我效能感(岳羽,2023)。
社區歸屬感層面,回歸分析顯示社區歸屬感對農戶參與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H2假設得到驗證。農戶的社區歸屬感越強,對社區內各個方面的信任度就越高,主人翁的意識就會越強。從而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就會越高(溫理,2018)。
回流年限指標上,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回流年限對農戶參與社區治理意愿有顯著負向影響,H3假設得到驗證。新生代回流農民工與農村、土地、熟人社會的聯系較少,他們回流后會呈現出更多的不適應性,在經濟、社會、心理三個層面的普遍不適應(張世勇,2014)。農民工回流時間越久,對社區治理會有更深的觀念認識,對社區治理事務有更深入了解,其治理觀念與在外出務工所認識的治理觀念方面可能存在認識上的沖突;再一方面可能會對社區治理行為方面越來越不認同,感到越來越失望,進而降低自己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
(四)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考察解釋變量的影響更穩定,我們試著進一步對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分別先后控制住nl、xb、jycd、nsr這4個控制變量后對模型進行回歸(李夢,2017),結果如表7所示。
七、對策建議
農村社區治理是建設和美宜居新農村的重要途徑,本文以西藏日喀則市回流農民工作為調研對象,綜合上文的研究結果,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主觀規范、社區歸屬感、回流年限方面都會顯著影響回流農民工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因此,應當重點從以上幾個方面著手,以提升回流農民工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意愿。
提高受教育程度,全面提升個人素養,加強社區治理認知。大多數農戶群體文化程度低,認知能力有限,這樣會嚴重影響社會組織的發展。發展社區教育將有利于提高受教育程度較低群體的社區治理認知水平,進而促進參與意愿行為水平的改善(尚云,2019)。因此,政府應多開展組織相關的教育宣傳工作,建立多元資源整合的社會化培訓體系,提高社區成員參與社區治理的認知和積極性。
形成多元宣傳主體,提高村民對社區治理認識的重要性。當前,農戶對社區治理的認識水平較低,自治能力較差,認為建設社區、管理社區就是政府的事情,跟自己無關。雖然農村社區都實現了村社共治的局面,但是沒有實現與普通農戶共同治理的局面,治理主體比較單一。社區黨支部和社區居委是社區治理的關鍵核心力量(郝文強,2023),應通過居委會鼓勵引導農戶參與社區治理的積極性。
發揮模范示范作用,引領村民實際參與,增強主觀規范意識。農村是傳統的熟人社會,村干部在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羅博文,2023)。村干部不僅是政策上傳下達的最后接棒人,也是社區治理實施的先行者,有著模范帶頭的作用。因此要加強村干部在社區治理相關方面理論和技能的培訓,并且村干部要主動積極投身到社區治理工作中,帶動農戶更好的提高村居民參與意愿。
構建和諧的居住環境,增強農戶的社區歸屬感。社區治理重在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讓居民成為社區治理最大的受益者是社區治理的目標所在(錢戴玉,2023),提高社區歸屬感可以促進農戶參與到社區治理。通過建設一個和諧的社區環境(張靜,2020),創造更為豐富的社區成員居民交流平臺,培養社區歸屬感,緩解社會壓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滿意度。
〔參 考 文 獻〕
[1]田夢君,熊濤,張鵬靜.勞動力轉移對耕地拋荒的影響研究——基于農業機械化的調節效應分析[J].世界農業,2023(11):103-114.
[2]陶瑋,尹月秀,魯如艷.祖輩與父輩共育幼兒的教育沖突表現及應對策略研究[J].教育觀察,2022,11(03):29-31.
[3]王大哲,朱紅根,錢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緩解農民工相對貧困嗎?[J].中國農村經濟,2022(08):16-34.
[4]馬草原,李宇淼,孫思洋.農民工“跨地區”流動性變化及產出效應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23(09):23-41.
[5]杜劍,徐筱彧,楊楊.高質量就業:理論探索與研究展望——基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作用的研究背景[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23,45(08):58-69.
[6]蔡弘,陳雨蒙,馬芒.縣域城鎮化視角下第一代農民工返鄉差異研究[J].重慶社會科學,2023(08):75-90.
[7]王鎵利.推動實現高質量就業的財政政策探討——以浙江為例[J].地方財政研究,2022(12):66-70.
[8]熊穎哲.反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英國托利社會主義論貧困問題(1842—1847)[J].史林,2022(06):12-17.
[9]李昭楠,劉夢,劉七軍.炊事燃料清潔轉型能否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基于CFPS2018的微觀證據[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22,21(02):239-248.
[10]劉延華.農民工回流原因、回鄉就業現狀與對策研究[J].山東行政學院學報,2018(04):45-51.
[11]張歡,吳方衛.要素價格、產業轉型與農民工回流[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23,25(04):108-122.
[12]柳澤凡.基層治理現代化背景下的村干部職業化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20.
[13]何強.基于交往行為的新型農村社區公共空間評價與優化策略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2020.
[14]雷煥貴,馬慧鑫,趙思宇,等.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民工回流、創業與終結的思考[J].理論觀察,2021(10):87-91.
[15]王山河.農民工“回流”對輸出地區的影響研究——對重慶市黔江區新華鄉和太極鄉利益相關者的深度訪談[J].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05):65-68.
[16]劉玉俠,張劍宇.對回流農民工的多維審視:基于現有研究分析[J].河北學刊,2023,43(05):160-168.
[17]閆琳琳,李雙雙.回流農民工助推鄉村振興的路徑探析[J].黨政干部學刊,2022(12):44-49.
[18]周春霞.雙創背景下農民工返鄉創業榜樣的行為特征分析及啟示[J].安徽農業科學,2022,50(18):223-228.
[19]張喆.淺談勞動力遷徙對勞動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J].勞動保障世界(理論版),2013(05):48.
[20]賀小丹,董敏凱,周亞虹.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民工回流與農村資源配置——基于農民工返鄉后行為的微觀分析[J].財經研究,2021,47(02):19-33.
[21]劉達培.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農民的自我認同危機:形成與紓解[J].北方論叢,2024(02):32-39.
[22]何淑婷.農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及市民化測度研究[D].南昌大學,2023.
[23]史璇.農民工參與農村社區治理的作用研究[J].現代職業教育,2016(12):12-14.
[24]楊忍,徐茜,張琳,等.珠三角外圍地區農村回流勞動力的就業選擇及影響因素[J].地理研究,2018,37(11):2305-2317.
[25]陳世海.農民工回流辨析:基于現有研究的討論[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4,13(03):265-272.
[26]胡楓,史宇鵬.農民工回流的選擇性與非農就業:來自湖北的證據[J].人口學刊,2013,35(02):71-80.
[27]王煒,許幸蓮.基于“推—拉”理論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回流現象分析——以黑龍江省為例[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6):91-95.
[28]鐘驊.上海菜場布局規劃思考與探索[J].上海城市規劃,2012(03):92-97.
[29]賈鼎.基于計劃行為理論的公眾參與環境公共決策意愿分析[J].當代經濟管理,2018,40(01):52-58.
[30]張紅,張再生.基于計劃行為理論的居民參與社區治理行為影響因素分析:以天津市為例[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7(06):523-528.
[31]胡晨成.糧食主產區農戶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意愿心理驅動因素分析[J].西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3,48(08):63-70.
[32]李守越,尚明瑞.農戶農業污染認知、農業污染補貼對耕地投入行為的影響研究[J].科技與經濟,2023,36(04):51-55.
[33]謝巍. 村規民約、鄰里效應對浙江省農村人居環境治理參與影響研究[D].河南財經政法大學,2023.
[34]何威.風險防范與危機抵御:面向“不確定性”的社區治理及其實現[J].河北學刊,2023,43(06):178-186.
[35]岳羽. 新鄉市農村居民參與社區治理意愿與行為研究[D].河南工業大學,2023.
[36]卓文昊.共享視域下社區參與式治理作用機制研究[D].山東大學,2023.
[37]葛亞楠.哈爾濱市“村改居”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共治研究[D].哈爾濱師范大學,2023.
[38]李欣,辛文玥,陳夫靜,等.鄰里環境因素對社區歸屬感與居住意愿的影響——以海口市為例[J].城市建筑,2020,17(28):5-9+14.
[39]劉悅來,謝宛蕓,毛鍵源.城市微更新中治理共同體意識形成機制——以社區花園為例[J].風景園林,2023,30(08):20-26.
[40]胡艷華.農村勞動力回流后的社會適應與社會保障現狀研究[J].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37(05):40-43.
[41]徐淑新.拉薩市社區治理中的居民參與問題研究[D].西藏大學,2020.
[42]陳秋霞,朱嘉豪,許章華,等.“是否值得”對農民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治理意愿的影響——基于福建省農村地區的Ologit模型實證[J].管理現代化,2023,43(05):156-166.
[43]張華,劉哲達,殷小冰.中國跨省流動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間差異及影響因素[J].地理科學進展,2021,40(01):73-84.
[44]孫自保,宋連久,劉天平,等.藏族農牧民外出務工影響因素分析[J].西藏發展論壇,2016 (04):14-20.
[45]李曉雅.農村人居環境治理中村民參與意愿與行為轉化研究[D].河北地質大學,2022.
[46]溫理.農戶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和影響因素研究[D].安徽農業大學,2018.
[47]張世勇.返鄉農民工研究——一個生命歷程的視角[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244-265.
[48]李夢.企業規模、RD支出強度與全要素生產率[D].東北財經大學,2017
[49]尚云.烏魯木齊市社區治理居民參與意愿及影響因素研究[D].新疆農業大學,2019.
[50]郝文強,黃鈺婷.基層治理的復合聯動結構與長效互動機制——基于C市R社區的案例研究[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25(06):210-219.
[51]羅博文,孫琳琳,張珩,等.村干部職務行為對鄉村治理有效性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來自陜隴滇黔四省的經驗證據[J].中國農村觀察,2023(03):162-184.
[52]錢戴玉,孫玲,余棟.“五社聯動”協同治理實踐與優化[J].合作經濟與科技,2023(23):176-178.
[53]張靜.新時代農村社區治理中的居民參與問題研究[D].中國礦業大學,2020.
〔責任編輯:孫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