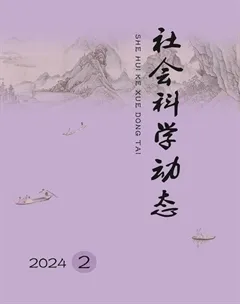中國故事的一種講法
摘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無論是在詩歌還是小說當中,海男一直堅守先鋒的姿態,用純粹的、狂歡化的語言營造了一系列獨特意象,以迷離夢幻的文本敘事給讀者帶來精神上的滿足。海男在《青云街四號》中糅入詩歌、散文、繪畫的元素,尋求文體的突破,探索文體的實驗,為當代作家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一種新的寫作經驗。
關鍵詞:先鋒;《青云街四號》;文體實驗;中國故事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一般資助課題“新世紀以來女性小說流變論”(項目編號:XSP2023WXZ012)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4)02-0092-04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男的小說創作呈現出鮮明的性別色彩和對女性境遇的獨特關注。學界解讀海男的小說時,大多圍繞“女性意識”“女性寫作”“身體寫作”“女性文學”等關鍵詞展開。事實上,這種標簽化的闡釋確實揭示出了海男小說中的性別話語與性別立場,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研究者運用女性主義理論剖析文本的實踐,但也往往容易步入一種預設的誤區和研究的傲慢——為套用已有的理論話語而忽視作家作品本身的豐富內涵,從而對作家作品造成一定程度的遮蔽與誤讀。最初翻閱海男的長篇小說《青云街四號》(202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時,筆者就誤以為小說講述的只不過是又一個關于女性成長與出逃的故事,但隨著閱讀的推進,卻不得不為自己的自以為是而慚愧。事實上,一旦拋開既定的成見,跳出自我束縛的理論窠臼,我們就會重新發現海男寫作的價值與意義。
一
亨利·詹姆斯認為,“小說按最廣義的界說而言,是個人的、直接的生活印象,首先是這種生活印象構成小說的價值,而小說價值的大小,就看生活印象的強烈性如何而定”,并強調“現實氣息”是“小說的最高德性”。(1)提倡冷靜、客觀地觀察現實生活,按照生活的本來樣式精確、細膩、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近些年來備受青睞。尤其是21世紀以來,以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利、農民工的身份認同、鄉村被城市“殖民化”過程中的生存焦慮等為主題的“底層寫作”逐漸興盛,推動了作家與批評家對“中國經驗”“中國故事”的關注與發掘,“重返民間”也一時之間被許多作家奉為寫作圭臬。眾所周知,文學中所表達的經驗是作家對自己或者他人經歷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經驗事實的書寫或敘述,是基于生活真實的藝術虛構。作家寫作時,哪怕是自己的親身經歷,也不會原封不動地照搬,總要運用藝術的法則對這些經歷進行裁剪,融入自己的理解與闡釋,形成獨特的藝術化圖景。從這一層面來講,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也不可能達到完全“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反映生活”的效果。與密切關注現實的“底層寫作”不一樣,海男的《青云街四號》提供了另一種寫作經驗。
《青云街四號》以云南昆明翠湖公園旁青云街四號的私人牙科診所為軸心,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講述了王醫生、“我”、慈蘭阿婆等人的故事。從故事發生的環境場所來看,昆明、翠湖公園、青云街、青云街四號牙科診所、文達畫廊、面臨拆遷的四合院、哀牢山等,都是具體可感的、真實的地理空間,就連青云街到翠湖的那條狹窄的小徑都可按圖索驥地找到。從這個角度來看,《青云街四號》高度遵循了再現生活真實的寫作原則,細膩地勾勒出了小說的敘事環境,給讀者營造了一種高度真實的閱讀效果。但通讀小說,不難發現,海男并沒有完全按照傳統現實主義的手法去編織故事。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基本都是采用第三人稱的敘事手法,而20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受現代主義影響,敘事視角會有所變化或節制,如書信體小說也會采用第一人稱敘事。《青云街四號》采用的是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視角,以出入診所的人物活動為經線,以慈蘭阿婆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人生為緯線,“我”宛若刺繡般穿針引線,在經線與緯線間游刃有余地穿行,為讀者細細繪制了一幅貫穿歷史與當下的人生圖景。
王醫生的青云街四號牙科診所是小說敘事的空間與外部環境,活躍在小說中的人物都以牙科診所為軸心,發生著或緊或松的聯系。如果畫一幅思維導圖的話,牙科診所就是圖的中心點,王醫生、“我”、慈蘭阿婆是思維導圖的一級分支;王醫生與郭濤、設計師小上海、阿南等患者間的關系,“我”與朝木的感情糾葛、“我”與拾荒的桂枝阿姨、尋夢少年飛飛的交往,慈蘭阿婆的逃難史、抗戰史、愛情史構成了思維導圖的二級分支;郭濤承包果園、朝木被騙、阿婆家租住的大學生與女模特、阿婆家保姆小花的成長等構成了思維導圖的三級分支。一級分支之間又由“我”連綴起來,將所有的故事精心引導出來,“我”作為王醫生的好友,時而旁觀審視,時而介入王醫生的生活,陪同她去看望身患癌癥、遠離北京來到云南種植果園的郭濤,一同救下抑郁的女孩并去支教學校探望孩子們,分享大學退休教授桂枝阿姨的助學秘密;“我”同時又是慈蘭阿婆歷史記憶的忠實聽眾,阿婆的逃亡故事借由“我”娓娓道來;“我”還是朝木的歷史情感與現實情感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歷史與現實在“我”這里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得以匯聚,盡顯第一人稱的敘事優勢。
作為小說的敘事人,“我”同時又承擔著小說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即“我”與朝木的情感線是小說中的一條情節主線。“我”的作家身份讓“我”能夠自由出入于現實與虛構之間,小說的敘述時間經常被打亂,敘述順序也相對自由,同一時間不同時空相互交疊,慈蘭阿婆因而也能夠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自由游走,營造出一種開放的敘事效果。“我”在傾聽慈蘭阿婆述說其個人抗戰史時,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視角不時地轉換為第三人稱的全知全能視角。“我”同時又能隨心所欲地從故事中抽離,將慈蘭阿婆的故事分解成一次次持續的講述,甚至不斷地明確暗示讀者,《青云街四號》只是“我”虛構的一個故事而已。小說中的真實作者、隱含作者、敘述者、小說故事中的人物一時之間難舍難分。
從敘事來看,這種寫作手法并不陌生,20世紀80年代先鋒作家馬原筆下就曾多次被實踐,“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的敘事圈套給無數讀者帶來了閱讀上的沖擊與洗禮。以馬原、余華、格非、蘇童、莫言等為代表的先鋒作家從敘事、語言、結構上不斷突破傳統小說,對“怎么寫”進行了不懈的實驗探索,為當代文壇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經驗與實驗文本。先鋒小說盛行時,海男正以極具先鋒性的詩歌而著稱。海男也曾坦言:“我仍然記得我心醉神迷地從八十年代末期進入九十年代的文學活動”,“就是在這一時期我寫下了大量的被評論家譽為先鋒文學的作品。”(2)不難看出,先鋒小說的敘事資源與先鋒詩歌的寫作實踐早就已經構筑了海男小說寫作的話語背景,并為其寫作提供了藝術積累。
二
20世紀90年代以來,海男的長篇小說《蝴蝶是怎樣變成標本的》《私生活》《縣城》《身體祭》《親愛的身體蒙難記》《碧色寨之戀》等大多圍繞女性成長與肉身體驗來講述一個個情節連貫、頗具女性話語的故事。對于任何一個小說家來講,講故事是必須具備的能力。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非常注重故事情節的完整性,講究敘事的因果鏈,在矛盾與沖突中營造敘事效果。從故事構架來看,《青云街四號》的情節較為松散,敘事跳躍性也較大,王醫生的醫患關系、“我”的寫作與現實人生、慈蘭阿婆的人生故事這三條情節主線看似完整,但都留有大量的空白,整篇小說也沒有刻意營造出強烈的敘事沖突。王醫生、“我”與慈蘭阿婆,這三個主人公任何一個人的經歷都可以演繹成另一部女性的成長與出逃史。尤其是當“箱子”“旗袍”“蝴蝶結”“高跟鞋”“碧色寨”等意象的不斷出現,讓讀者誤以為海男在重復《蝴蝶是怎樣變成標本的》《碧色寨之戀》的故事。但出人意料的是,小說打破了作家此前采用的一系列傳統故事套路:如王醫生的家庭、情感經歷都被置于幕后,王醫生與患者郭濤、小上海的關系并沒有按照慣常的寫作思維演繹成男女戀情,王醫生的出逃與私奔并未拘囿于狹隘的兩性關系,而是在疲倦的現實生活之余追求個人精神自由的突圍;“我”與朝木的中年重逢,留下的也只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慈蘭阿婆遠征抗日的歷史只開了一個情愛的頭,就因戀人李繼軍的戰死而偃旗息鼓,戰火紛飛時代的家仇國恨、戀人間的生離死別、親人間的分崩離析等足夠渲染歷史與情節的橋段都被毅然舍棄。不難看出,海男有意識地放棄了此前小說關注兩性關系的女性主義寫作思路,刻意回避了身體與兩性情感,取而代之的是閱盡世事后的睿智與豁達。
海男刪繁就簡,以幾個主要人物的活動為載體,表達自己對當下社會現象的憂慮與反思。小說多次強調手機的導航功能、搜索功能便捷地實現個人空間的位移。連90多歲的慈蘭阿婆都能夠熟練地運用現代通訊手段,在微信中與兒孫輩互通有無。王醫生微信朋友圈的動態也不時成為“我”解讀她內心的入口。但在這些便利背后,“我”流露出的擔憂無處不在。科技的高速發展在解放人的同時,卻又成功地束縛了人。當人們過度依賴手機的時候,人類與自然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遠,手機也就成功地異化了人類,甚至成為部分人實施詐騙的作惡工具。小說中三個大學生雇傭的人體模特、朝木現女友的消失,從一個側面呈現了人與人之間信任關系的脆弱與喪失。
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正悄無聲息地改造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蠶食著人們的生活空間,吞噬了自然的野趣與詩意,回歸純樸的原生態生活成為越來越多的人逃離城市的不二選擇:“小上海”每隔一段時間就從上海飛到昆明來“續命”;癌癥患者郭濤放棄個人財產,從北京撤退到哀牢山種植果樹,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簡單生活;鄉村女孩小花由一個偏僻山村來到昆明當保姆,因祖輩傳下來的精湛的刺繡手藝而被發掘出來;小花懷揣美麗的城市夢奔赴北京,不久后驀然驚醒,再度回到昆明和慈蘭阿婆創辦“一個人的歷史博物館”;小花的父親癌癥確診后從省城回到家鄉后卻胃口大開,毅然決定放棄住院治療。地球終將消失,我們每個人只不過是匆匆過客,生老病死,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不變法則。海男運用了一系列隱喻化的敘事來表達重返自然的呼聲。當然,重返自然并不代表抗拒現代化,也不代表守成甚至后退,而是呼吁放慢腳步、用心傾聽大自然、尋找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放慢腳步才能對歷史駐足回望。慈蘭阿婆的一生跨越了兩個世紀,在炮火紛飛的抗日戰爭中,她跟隨家人由上海輾轉逃難至昆明,并買下一座四合院安了家。慈蘭與哥哥慈歌踴躍報名參加了中國遠征軍,用青春與熱血譜寫了不朽的人生篇章。小說有意略去了戰爭結束后慈蘭的日常生活,而用大量筆墨渲染慈蘭阿婆留下來的歷史見證物:六個相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箱子、母親的旗袍碎片、戀人李繼軍的遺物、兄長慈歌的舊物等。這些陪伴慈蘭阿婆一路走來的物品,成了“一個人的歷史博物館”中的珍貴館藏,熠熠生輝地編織出一種樸素的、個人化的、民間的、充滿情懷與溫度的歷史記憶。
這座歷史博物館,同時也是身處云南邊陲的海男一個人的紙上博物館,寄予著海男書寫“時間與社會背景的歷史相遇”的不懈努力。在現代化的開發浪潮中,慈蘭阿婆那座刻滿了歷史滄桑印跡的四合院正面臨著被拆遷的命運。海男從個人史的角度提供了另一種記錄歷史的方法,這無疑將激發更多的人去搜集散落在民間的各種文化遺存,去豐富和補充被宏大歷史所遮蔽與遺漏的歷史記憶,進一步還原歷史的真相。
三
張愛玲在《赤地之戀·自序》中寫道:“我有時候告訴別人一個故事的輪廓,人家聽不出好處來,我總是辯護似的加上一句:‘這是真事。’仿佛就立刻使它身價十倍。其實一個故事的真假當然與它的好壞毫無關系。”(3)現實主義的真實歷來都不是衡量一部小說作品成功與否的必備要素。對于先鋒小說而言,真實與否更不是問題。與現實主義追求的生活真實相比,先鋒小說更注重在語言與形式層面形成突破,最終抵達心理的真實、敘事的真實。
小說家兼詩人的雙重身份,造就了海男寫作的詩性話語,其小說呈現出明顯的詩化色彩。“詩化小說是現代主義小說的一種形式,也即用詩歌的方式組織敘事。為了最大程度地逼近詩,削弱散文小說敘述結構的統一感和邏輯性,作者需要利用詩歌的特色手段來替換或轉化散文性敘事的形式技巧——諸如強調關鍵詞語、有意重復某個意象、富有暗示意義的細節、節奏等。”(4)《青云街四號》中不斷出現“箱子”“私奔”“蝴蝶結”“旗袍”“高跟鞋”“空中花園”等意象,且在“我”的敘述中不斷被強化。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這些意象,都被賦予了特定的隱喻功能:“箱子”既意味著在路上的漂泊和靈魂的突圍,也表征著“歷史中間物”的塵埃落定;“蝴蝶結”“旗袍”“高跟鞋”隱喻女性的活力與性別氣質;“私奔”僅僅隱喻一場沒有結局與未來的逃離過程;“空中花園”也可看作是對小說人物的隱喻性表現。在“空中花園”,每個人都可以短暫地從現實生活的各種煩惱中抽離,在藍天白云之下感受片刻的心靈自由。如王醫生每次從一樓診室上來休憩,都會褪去白大褂,露出白大褂底下精心搭配的服飾,煮上一壺普洱茶細細品味,掙脫現實的羈絆與困囿。意象是詩歌構成的基本要素,也是詩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海男酷似一個在筆尖跳舞的精靈,將詩歌的元素與符號引入到小說中,用詩意的語言去搭建敘事的迷宮,用碎片似的敘事話語連綴起歷史、現實與未來。
海男曾坦言,這部作品兼于長篇小說或散文之間,當然還有詩歌的符號。從小說文本來看,海男在《青云街四號》的寫作中尋求的是一種近似于西方小說中的傳奇式的自由,以玄妙的語言來達到詩意的境界,以進入更高的現實和更深的心理之中。小說不僅彌漫著一種濃得化不開的詩意,同時還呈現出一種油畫般的豐富質感。慈蘭阿婆陳放舊物的房間,幽暗的光線,深褐色的麻質窗簾,黑栗色的、舊式的老家俬組合成一幅凝重的油畫,將阿婆的厚重歷史推至前臺。“梯級的莊稼地上幾頭水牛正在耕地,農人走在水牛后面掌著扶犁”,“一群白鷺從蔚藍色的天空下拍著翅膀正在練習飛行”,勾勒出一幅生機盎然的春耕圖。王醫生不斷變換顏色的旗袍、蝴蝶結,高跟鞋叩響青云街的娉婷裊娜的背影,更是一幅幅色調大膽奔放的、交織著情感與靈性、帶著溫度與力量、充盈著生命氣息的人物肖像畫。可以說,海男用線條、塊面、色彩、光影等形式構筑了一個表意的世界。埃米爾說過:“一片風景就是一種心理狀態。”(5)看似漫不經心勾勒的風景,實則處處都顯露作家的良苦用心。小說也好,詩歌也好,繪畫也罷,不管形式如何變幻,也不管表達形式有何不同,情感的深度和思想的純度卻是始終如一的。
先鋒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思潮,早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代表作家蘇童、余華、莫言、格非等的創作轉向就已經走向離散與解體。到了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先鋒作家除了馬原、孫甘露、殘雪外,基本上都已經完成各自的創作轉向,“以回歸或‘撤退’的方式,在一個更新的意義上,重新啟用和開發本土的文化資源和文學資源”(6)。這種整體轉向的趨勢,同時影響和波及了受先鋒作家影響的“60后”“70后”作家如畢飛宇、朱文穎等,和以“個人化寫作”著稱的某些同樣帶有先鋒性的女性作家如林白、陳染等。從1997年的《坦言》到2010年《碧色寨之戀》,海男這期間的小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學創作轉向的影響,凸顯故事情節、注重敘事過程,但語言上卻一直保持著詩意的高揚與恣肆。而在《青云街四號》中,海男糅入詩歌、散文、繪畫的元素,執意堅持自己的語言風格與圖像符號,以自己對文學和社會生活的獨特理解,在小說中營構詩意的世界,打造美與善的神性空間,以此尋求文體的突破,探索文體的實驗。小說中的王醫生、“我”、慈蘭阿婆、桂枝阿姨等,都用質樸的愛意堅守著自己的內心世界。海男用自己細膩的筆觸,道出了唯有愛、理解與包容,才能在世界上開出良善之果這一真諦。可以說,“先鋒”的海男從未離開過我們。從這一層面來說,《青云街四號》或許為當代作家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寫作經驗。
注釋:
(1) 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朱雯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2) 梁小娟、海男:《守候靈魂的寫作——海男訪談錄》,《小說評論》2011年第6期。
(3) 張箭飛:《魯迅·詩化小說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4) 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頁。
(5) 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第3冊,臺灣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頁。
(6) 於可訓:《新世紀文學的困境與蛻變》,《江漢論壇》2009年第9期。
作者簡介:梁小娟,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湖南湘潭,411201;尹伊達,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湖南湘潭,411201。
(責任編輯 莊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