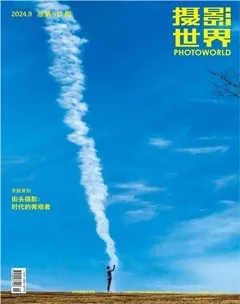上江沿兒








前幾天,朋友在群聊中說,在“爾濱”生活的人幾乎都有種儀式感,那就是——上江沿兒(東北話,意為“去江邊”)。看到這行字,我會心一笑,心想可不是么。
江邊的江,就是指哈爾濱的母親河——松花江。
一轉眼,我來到哈爾濱上學工作已有近九年時間,江邊已記不清去過多少次。心情好時去江邊,心情差時也去江邊,一個人散心時去江邊,三五好友結伴時還是去江邊。松花江上,與夕陽一同落下的,是我喜怒哀樂的回憶。松花江上,隨江水一同遠去的,是我最美好的青春年華。

哈爾濱,松花江穿城而過。長長的江邊,去得最多的還是防洪紀念塔附近那段。
坐地鐵2號線到中央大街地鐵站下車,經過霞曼街,再走過1公里多長的“面包石”街路,就到了防洪紀念塔,塔后就是江邊了。
近半個小時的腳程聽起來挺長,走起來卻并不覺得。漫步在中央大街,舔舔奶香濃郁的馬迭爾冰棍,聽聽陽臺音樂會上國內外樂手的演出,看看富有歐陸風情的特色建筑,再穿過一個地下通道,防洪紀念塔近在眼前,江邊也就馬上到了。

一年四季去江邊的人很多,尤以夏天為最。防洪紀念塔正后方的數十米江岸,臺階直至江水。人們安坐在臺階上,把臺階坐得滿滿的。總能聽到新來到江邊的人問,這都在看啥呢?許多時候,問問題的人也會停下腳步,和大家一起待一會兒,看一看。其實,在江邊就是一種放空,拍拍照,吹吹風,看看夕陽,就足以舒緩心中的煩躁與疲憊。有本地人看到這兒又該說了,什么放空,應該叫“賣呆兒”才對。
松花江畔,很多人來到這里只會待很短一段時間,而“江沿兒”卻一直在這里。總有新友來,也總有故人去。松花江以博大的胸懷,給每個來到江邊的人以短暫卻又久遠的陪伴。
年紀稍長的當地同事告訴我,他們小時候防洪紀念塔附近沒有這么好的景觀。如今,這片江邊越修越好,哈爾濱人去江邊的習慣也“刻進了DNA”。逢年過節“上江沿兒”成了一種執念,不去轉轉就覺得缺點兒啥。


從防洪紀念塔繼續向東走,走過一邊直播一邊唱流行歌曲的年輕男女,走過伴著鼓點起舞的夕陽紅樂團,就到了被稱作老江橋的濱州鐵路橋。這座有著百年歷史的大橋見證了哈爾濱的滄桑巨變,停止通車后被改建成空中公園重新對市民游客開放。登上老江橋,坐在這里,不那么擁擠,相對安靜,視野也更加開闊。
日落時分,坐在老江橋的鋼筋鐵骨之中,高速列車從一旁的新江橋上呼嘯而過,帶來輕微震顫。“這很像一個活力十足的美少年,帶著一個腿腳不便的老嫗起舞”,這是作家遲子建在老江橋上駐足時的感受。橋上的江風比下面要大不少,感受起來也更明顯。夏日的江風不似冬天那般刺骨,像母親輕撫的手,更多了一些溫柔。視線遠處的索道橫跨江南江北,松花江上的游船霓虹閃爍。一百多年中,多少列車曾在老江橋的鐵軌上穿梭而過,多少人又經此往復。


日落后,深藍的天色倒映在被風吹皺的江面。不知是天空把江面看老了,還是江面正仰望著年少時的自己。我喜歡坐在老江橋上“賣呆兒”,總感覺天空和江面離我一樣近,過去和未來離我一樣遠。其實有一陣不來江邊了,再來時發現又有了不小的變化。
靠近江北岸的江面上新建成了一座江上大舞臺,《遇見·哈爾濱》大型實景演出就在這里上演。防洪紀念塔旁的回廊上增加了射燈,情侶在燈下“擺著pose”,甜蜜剪影在圓形燈光中變換。新老江橋也有了新的亮化設計,老江橋上增加了射燈,原來固定的橙金色燈光不再,換成了藍黃交替的顏色。老江橋旁邊的新江橋上,三個巨大圓拱也映上了七彩的流動燈色。
當然,哈爾濱的江邊,美的不止是防洪紀念塔這一片,亦不僅僅在夏季。從江南岸坐游船過江,對岸就是免費的國家5A級景區——太陽島。搭一頂帳篷,帶一本書,賞夏花絢爛,看樹影婆娑,又是閑適美好的一個下午。
冬季更不必說。嚴寒封凍了寬闊的江面,冰雪嘉年華、采冰節、“鉆石海”……可玩可逛的,太多了。當冰層足夠厚時,可以徒步橫穿江面,這是南方城市難以實現的人生新體驗。有了上個冰雪季的火爆出圈,我想今年哈爾濱的冬天一定會帶來新的驚喜。
一座城市,有了江河就有了靈魂。哈爾濱名字的含義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天鵝”,也有人說是“渡口”或“打魚泡”,但無論哪種解釋都與松花江有著不解之緣。
于我而言,松花江見證了我的成長,以壯美的風光激發了我對攝影的熱愛,更用豪邁的氣質舒張了我的性格,流淌不息的松花江水亦如我所從事的記者這份職業,總是奔赴、再奔赴。我深愛著松花江的廣闊、淡然、包容……
我想,每個在哈爾濱生活的人都對松花江有著自己的喜愛之情,可表達的方式卻又殊途同歸,直接而又熱烈,那就是——走啊,“上江沿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