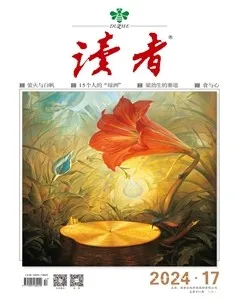一對單身母女選擇同居養老


巫昂今年50歲,未婚;媽媽林秀莉今年80歲,離異。這對同是單身狀態的母女,選擇了一種特殊的養老方式:在云南普洱的小屋里共同居住、生活。
20多年前,巫昂幫助媽媽逃離實施家暴的父親。她形容自己和媽媽、弟弟是一個“戰團”,一起開始了這個小家庭的“災后重建”。
林秀莉經歷過充斥著家暴的婚姻后,從不催女兒結婚,女兒想怎么樣她都同意。在她的支持之下,巫昂有了一張平靜的書桌。
離開家鄉福建省漳浦縣后,巫昂在復旦大學讀文學專業。畢業后她做過傳統媒體的調查記者,但一直堅持“吃文學這碗飯”。離開機構媒體后,她將寫小說作為自己一生的志業,這幾年又開始畫畫,已經做了21年的自由職業者。
80歲的林秀莉,曾經是那個年代少有的大學生。畢業后她成了縣城里有名的婦產科醫生,28歲時和巫昂的父親結了婚。當時她需要一邊照顧家庭,一邊救治病人,擔子很重。但與此同時,她還承受著丈夫不間斷的家庭暴力。直到55歲時,才在兒女的幫助下逃離她忍受了20多年家暴的婚姻。
艱難地從那個家剝離出來之后,巫昂承諾,要帶媽媽一起生活。
如今,她們真正地生活在一起。她們的準則是,最大限度地為對方保留獨立的空間。在巫昂和林秀莉身上,很少看到母女關系中存在的掙扎、沖突和張力;相反,她們正攜手走在一條寧靜、平和的重建之路上,共同進步,成了“更新版的自己”。
以下是她們的講述。
1
林秀莉:
早年都是為了家庭的名聲。在外人看起來我們的家庭特別好,他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的,我是福建醫學院畢業的,兩個孩子都上復旦大學。所以不管對方給我多少肉體上的侵犯,我都覺得說出去會影響家庭的聲譽。20多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在壓制內心的感受,強忍著不去跟他計較。
但是,到了后來,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末,巫昂已經上研究生了,她弟弟也上了本科,孩子給了我動力。巫昂跟我說,她親眼看到她父親打我以后,從小心里就有一個計劃:如果以后我要跟他離婚,她跟弟弟會帶我上法院。
孩子發聲以后,我覺得自己應該擺脫這個人,不能再讓他這樣無端地傷害我。
巫昂在意見書里說:“我從小就下定決心,在我有能力的時候要把我媽媽解救出來。”
但我得到的支持太少了。第一次開庭那一天早上,我七八個高中同學都跑到醫院,阻止我們去法院。我兒子對他們說:“我媽媽挨打的時候你們都在哪里?”
以前他會干涉我所有的生活,好看的衣服、鞋子我都不能穿,更不要說化妝。我很喜歡唱歌跳舞,但他強迫我退出文宣隊。一旦我的職位晉級了,他的臉色就不好,不跟我一起走。他為什么那么恨我,我也不知道原因。
離婚之后,我感覺自由了。我可以穿上我喜歡的衣服,跟其他人一樣,化妝打扮,自由地去唱歌跳舞。
巫昂:
從我記事起,父親的家暴是沒有間斷過的。他隨時都會發怒,我媽媽非常不容易,她的身體受到很多傷害。
比如她的膝蓋受傷,她說是我父親有一次從后面頂她的腘窩,因為她個子很矮,不到1.5米,就直接跪在了地上,她的半月板被磕碎了。這直接影響了她后半生的生活品質,即使現在她也沒辦法走很長的路。
我作為她的女兒,其實只是一個目擊證人。真正的痛苦是在她的人生如此黃金的20多年里,她都在忍受這段婚姻。
我媽媽完全是凈身出戶。后來我們調侃那個家是我們的“淪陷區”,小時候很寶貴的童年紀念品都沒來得及拿出來,有時候我會突然想起來我的集郵簿、《一千零一夜》都還在“淪陷區”。
我寫詩的時候非常直接地寫過很多這樣的經歷。在我寫了逃離家暴后和母親同居的文章后,很多女孩告訴我,自己的家庭也是這樣的。我覺得大家不應該回到家還得承受這樣的恐懼、暴力和痛苦,就好像生活在戰亂區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和母親有責任讓她們知道,我們的這條路她們也是可以走通的,可以走得很安全、很好,可以靠自己過上一種很安寧的生活。
我曾經想,我媽媽可能在婚姻里活不到60歲,但她現在已經80歲了。我們為她,她也為自己爭取到了今天這么平安快樂的生活。
我覺得女兒天然地應該為母親的觀念和意識,特別是女性主義的觀念和意識換血。
媽媽并不是說不想,或是沒有能力變成2.0、3.0版本的自己,只是她所處的時代沒有有利于女性發展的土壤。所以如果做女兒的不學習,你就沒有能力去為母親換血。
一些中國女性以前是有點兒不愿意直面敏感問題的,比如對女人的處境、婚育的選擇,甚至對掙錢這種事情都有點兒害羞。我覺得這些都沒有什么好羞愧的,你就應該把它們放在桌面上,像男人一樣去討論。
很多人說,對母親進行教育和感染的進度是很慢的,甚至有很多反復,先前改善了的問題過一陣又復發了之類的,所以我覺得和母親交流時還是要有耐心。
你要給她時間,因為她們這幾代人沒怎么接觸過審美教育,或者更先鋒的人生觀。你要給她一些點對點的指導,比如轉發一些有思想深度的文章鏈接,讓她知道世界上有些人不是那么傳統地活著,年輕人有很多不同的活法,但它們依然是可行的,她的女兒也可以過得很幸福。
另外,你要讓媽媽知道你的經濟狀況。如果她知道你的口袋里有錢,她就不會特別擔憂。
我媽媽現在已經成為她前后兩三代人的一個新的影響力中心,她整個人都更新了一版。
她會非常主動地把我傳播給她的東西告訴她的同事、同學、晚輩。她打電話給她那些老年親戚,說他們應該去聽播客,要學會網購,要學習使用App。
2
巫昂:
我跟所有的“70后”一樣,也糾結過,嘗試過建立親密關系。但我媽媽的故事給了我很多警示和思考。
有的同學老是跟我說,“女人最大的價值和最終的歸宿就是婚姻”,對這種陳詞濫調我反駁起來是毫不留情的。他們的下一招就是說“你搞文學也沒掙到什么錢”,我會回應:“你怎么知道?”
我和媽媽有過非常開誠布公的交流。我媽媽的觀點甚至比“90后”的還要前衛,所以她從來不會催婚。
我媽媽有一個很特別的優點:她覺得她的孩子不管做任何選擇都是有道理的,她堅信我是對的。她不以金錢得失來衡量我的成功或者失敗,而是以我是否發揮了自己最應該發揮的能力作為評判標準。
所以哪怕在當年,我選擇放棄媒體行業的高薪職位,進入寫1000字掙30元到50元的文學創作領域,我媽媽也覺得是很好的選擇。這種支持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林秀莉:
我在上醫學院的時候,對婚姻根本沒有什么概念,我也沒有特別愛誰,到最后自己都決定不了。當時有五六個人給我寫信,我拿著信去問我的表姐,她看了看說,這個人是名牌大學的,就這個好了。我當時找對象就是這樣選的。
現在巫昂這么努力地做每一件事,我認為她快樂就好。她想怎么樣我真的都同意。
3
巫昂:
和媽媽一起生活,最重要的是讓我至少擁有了幾年平靜的生活,可以安放一張書桌。因為我們相互支持,讓我覺得自己可以完全不考慮掙錢的問題,我改變了前幾年那種“鐵血戰士”的狀態,變得放松起來,安心地發展我的第二事業。
因為我要帶著媽媽,又是自由職業者,所以不能太晚考慮養老這件事,我從40歲就開始有意識地安排這些事了。我和弟弟、弟妹都很團結,我們就像一個軍團,非常有規劃。
跟媽媽交流之后,我們決定不送她去養老院。她的遺囑很早就處理好了,這沒有什么好避諱和羞愧的。
我們在普洱這邊也有意識地結交了一些當地的朋友,萬一我去出差,也有人能夠隨時過來;如果有必要,我們會請保姆或者護工。
已經在社會上經歷過這么多風雨的人,為什么要在養老面前止步不前或感到恐懼?為什么要害怕死亡?我覺得面對死亡時保持理性是一個在生活中搏斗過的人應有的選擇。
林秀莉:
人變老在生理上是一種自然規律,各個器官衰退,都是正常的。人要正視年齡的增加和身體的退化,不要因為衰老而悲觀喪氣。
我覺得我必須像年輕人一樣充滿活力,所以我常常會想不起自己今年多少歲了。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兩個人。一個是楊絳,她是我最尊崇的人。在看了好多本她的書以后,我從她身上汲取了很大的前行力量。她女兒去世,我說她怎么撐得住,巫昂就會跟我說楊絳是一個怎樣的人。她經歷了那么多的事情,但到100歲以后還在寫作。
另一個是盲人歌手周云蓬,我非常喜歡他。他9歲就失明了,但還是一直堅持讀書。他念了大學,寫作、創作音樂,還到處去巡演,前年血壓升高了,他都沒有停歇。我曾經問他:“你的這種力量是從哪里來的?”他說:“你什么都不要想。”
所以我有什么七想八想、停滯不前的理由呢?我也必須像他們一樣,如果我能活到100歲,我也要學到100歲。
我只想跟上時代,未來我要多學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識。一些人不是說以后會有太空旅行嗎?我總是跟我的老同事們說,要好好活著,以后一起去住太空酒店。有那么一天,我也想登上宇宙飛船去遨游大宇宙,去親自看一下宇宙間的星球。
(海城樓摘自微信公眾號“一條”,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