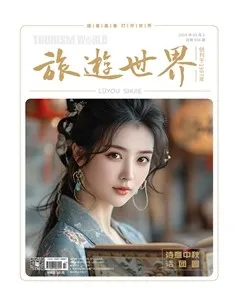泥塑兔子王:泉城記憶,匠心傳承


“臉蛋上沒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畫了一條細線,紅的,上了油,兩個細長白耳朵上淡淡地畫著點淺紅。”老舍在小說《四世同堂》中的這段描寫,指的便是當時風行濟南、北京兩地的泥塑兔子。北京稱其為“兔兒爺”,濟南則叫“兔子王”。
2016 年,泥塑兔子王被山東省認定為第四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兔子王,老濟南中秋節的儀式感
在老濟南有一個特殊習俗,每逢中秋佳節在家中供奉兔子王,讓它以兔神身份接受祭拜。這種習俗源于一個傳說。
相傳,濟南城曾鬧瘟疫,民間無藥可醫,遂請求神明保佑。月宮兔神知曉后銜藥下凡,將仙藥投入遍布泉城的72 處泉水中,百姓喝了泉水,疫病得以祛除。因此,每逢中秋在家中供奉泥塑兔神便成了濟南的民間傳統。
具有濟南特色的兔子王傳承至今,離不開一個人,他就是山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泥塑兔子王代表性傳承人周秉生。在周秉生的爺爺周長海那一代,每逢中秋節,濟南購買和祭拜兔子王的氛圍最為濃厚。那個年代,周家以家庭作坊的形式手工作業,最多的時候有十幾個家庭成員參與,“我們家做的兔子王主要是對外批發,一年之中最忙的時候就在中秋節前半個月。”周秉生介紹說。
解放前,濟南有三十多家做兔子王的,周氏兔子王在其中小有名氣。周秉生的奶奶告訴他,每到賣兔子王的時候,他們家院子里都要準備三個大甕,到過中秋時這些甕就會盛滿了糕點。“這是因為相熟的客戶一般來自糕點店和水果店,他們來定做兔子王時不必付定金,就會順手捎點禮物以表誠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規矩。”周秉生說。由此可見前來訂貨的人之多。
逢兔子王做得多的時候,周秉生的父親周景福就會挑著兩大籃兔子王到位于濟南西門盛唐巷的批發市場售賣,偶爾家里人也會在中秋節當天上街零售。到了周秉生這一代,濟南人中秋節必買兔子王的習俗已淡化,家里也不再以此為生。周秉生十幾歲時,看到父親用泥巴做了一個小兔子王把玩,從此他才開始接觸這門手藝。
16 道工序做出一個兔子王
在周秉生家中的柜子里,盛滿了他和父親做的兔子王,高度從十幾厘米到五十厘米,周景福還做過高達八十厘米的大兔子王。兔子王從頭到腳著色有紅、黃、綠、金四色,身上的每一部分也都有喜慶的寓意。

兔頭人身的兔子王白面紅唇,兩只長耳朵和頭部之間用彈簧相連,可自由擺動,看起來憨態可掬,十分可愛。中空設計的兔子王下方有聯動裝置和一根繩子相連,只要用手一拉露在外面的繩子,兔子王的雙臂就能上下搖動,做出形似搗藥的動作。和北京的兔兒爺及天津的兔二爺相比,這種動態的兔子王屬于濟南特有。
兔子王的種類從姿勢上分坐兔王、站兔王,從性別上分兔子王和兔奶奶,從衣著、坐騎上分大紅袍、大坐虎、中坐虎、小坐虎、小坐墩、兔王坐元寶等。周秉生介紹,周氏兔子王一直用黃河細膠泥為原料,和好泥后醒一晚,第二天就可以“捏子”了,緊接著就是制模,制模后才開始做兔子王,這樣數下來,做一個兔子王從頭到尾整整有16 道大工序。
守正創新,兔子王要有新觀念
現在隨著人們對非遺重視程度的提升,喜愛兔子王的人也逐漸增多,但從事創作的人仍然不多。周秉生說,如今他的女兒周雅萍已能夠熟練制作兔子王,成為周氏兔子王的第五代傳人。今年,周秉生和女兒一起創作了新的兔子王樣式,這只兔子王頭部也是可以活動的,顯得更加活靈活現。新式兔子王身著古色古香的衣袍,雙手交叉舉在胸前,既可以說是拱手作揖,也可以說是在搗藥,外形既有現代人喜愛的萌感,又傳承了傳統樣式的特點,臉譜和用色基本沒變。
“父親曾告誡我,老一輩傳承下來做法和樣式,如果學不會,時間長了這些東西就都消失了。”周秉生說。他也是如此教導女兒的,只有在遵守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才能不失民俗味道。“不為賣多少兔子王,而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老濟南的手藝。”這句話,周秉生總掛在嘴邊。這位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泥塑兔子王代表性傳承人,對守護、傳承、創新這一手工技藝,始終抱有執念。
如今,泥塑兔子王已成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周秉生說,他打算搜集整理更多有關兔子王的資料,創新更多樣式,讓兔子王進入越來越多人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