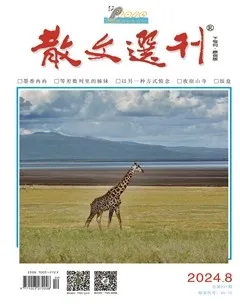蘆花姑娘
盛夏里,坑塘的青蛙老早地把韓家酄村叫醒了。
我拉開窗簾,推開窗子,一團薄霧飄了進來,遮住了視線。忽而薄霧又偷偷地溜出了屋子,不知飄到哪里去了。在離屋子十幾米處的坑邊上站著一位二十出頭的姑娘。她穿著白紗裙和藍紗無袖襯衫,身材苗條、長發披肩,顯得清秀飄逸。我的推窗聲顯然驚動了她,她笑瞇瞇地向我張望。
我一時手足無措,慌張地貓下腰,躲閃到墻旮旯,拽過椅子上的衣服迅速穿好,用手指攏了把頭發。
見她還在笑瞇瞇地往這邊看,她竟然沖我婀娜地走來,站在窗前,羞紅著臉跟我說話:“您是工作組的劉老師嗎?”
我詫異地看著她,猶豫著問:“你是?”
她羞答答地低下頭,又偷偷瞟著我說:“我是村里的小學老師,我們經常在《唐山晚報》上看到您寫的散文,聽校長說,您就在我們村下鄉,我想看看真人兒。”
我不好意思地說:“有點兒讓你失望了吧?我寫得不好,是鬧著玩兒的。”
“劉老師忒謙虛,您寫的就是我們身邊兒的事兒,特生動、特真實!”她又說,“劉老師,您今天還得上課去。哪天我請您到家里吃頓便飯行嗎?我特想跟您請教。”
我趕忙說:“不用吃飯,有空兒咱們隨便聊聊,請教談不上,我還要向你們年輕人學習呢!”
她問:“您的手機號是?”
我剛報給她,手機就響了,她說:“這是我的號,我叫董蘆花。”說完,她把我手機搶過去,幾下就把她的名字儲上了。她說:“劉老師,您就算答應啦啊?不能食言啊?”
說完,她就像河渠里的一朵水蓮花,隨著潺潺的流水在一團薄霧里漂走了,漂出老遠,又回頭望了我一眼。
蘆花沒有食言,一個周六的早晨,她果然打來了電話,讓我中午到她家去吃飯。
我趕忙說:“哎呀!今天不巧,我已經答應董伯付了,今天在他家的魚鋪上吃去,咱們改天吧!謝謝啊!”
“不行!劉老師,您可是答應過我的,我爸早起就把大公雞殺了,還撈了一條大鯉魚,人家好不容易才盼到這一天嘛!”我聽出她那焦急耍瘋的樣子。
“這……這……我還有兩個隊友呢。”
“您讓他倆去伯付家吃唄,我想讓您一個人來。”
這咋跟他們說呢?我心里嘀咕著,最后支支吾吾似乎勉強地答應了下來。
到了中午,我只好編了一個漏洞百出的理由,跟他們請假,汝龍和伯付非常不滿意,對我急赤白臉。
我走在大街上有種心慌的感覺,生怕碰見熟人,還好街上無人。我按照蘆花在電話那頭指引的路線,穿過兩趟街后,才看到她站在街的中央沖我招手。她穿了件紅裙子、白色T 恤衫和一雙白色厚底兒涼鞋,散發扎成了牛尾辮兒。她羞澀地紅著臉微笑著把我讓進院子里。
院落寬敞潔凈,有三間正房和三間廂房。正房的窗前種著一溜茉莉花,青白色的花朵噴薄著芳香。我有些發怯地透過窗戶往屋里望,想找到她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屋子里沒人。她意會到了這些,趕忙說:“別找了,家里就我自己,我媽在我姐家伺候月子呢,我爸在魚鋪上不回來。”
她在廂房里的廚房燉著雞,在正房的灶臺里熬著鯉魚,堂屋的地上放著一張矮腳的長方形飯桌,飯桌上已經擺好了一盤黃瓜炒雞蛋、一盤青椒炒河蝦、一盤醉蟹。
她說:“劉老師,您先上西屋坐會兒,雞跟魚馬上就好。”
我掀門簾進了西屋,屋子很干凈,墻上有她的照片,炕的被單是藍花格子的,夏涼被疊得整齊,枕巾是棗紅色的。看得出這一定是她的房間。屋子的北面有一個大衣柜和一張寫字臺,寫字臺上擺著一溜書籍,有《唐詩三百首》《蕭紅文集》《冰心文集》《大浴女》《十萬個為什么》等。
“劉老師,開飯咧!”她掀簾子露著一雙黑亮迷人的眼睛叫我。
她已經把魚和雞端上飯桌。飯桌上還有一瓶白酒,兩個小酒盅兒。
“蘆花,你也會喝酒?”
蘆花靦腆地說:“劉老師,我知道您會喝酒的,您的許多文章里都有喝酒的情景,今天就讓蘆花陪您喝個痛快!”
“那好,倒上。”我們并肩而坐。
我見那酒竟是“山莊皇家窖藏12 年”。
我說:“這可是河北的名酒啊,據說康熙皇帝在承德平泉圍獵時,就用此酒宴請過大臣們。你是怎么得到的?”
蘆花笑著說:“我是托在城里住的老師捎來的,我只告訴他買瓶好酒,要那種有一定歷史文化的名酒,結果他就買來了這個,您喜歡就好。”
我連忙說:“好、好,好酒,我很喜歡,只是別這么破費,下不為例啊。”
“劉老師,咱們對詩吧,我說上句,您接下句,接不上來就罰酒一杯,您看怎樣?”
我說:“可以,要是接上來了呢?”
“那就都喝唄!”
“好!你說吧!”
說實話,我會的唐詩實在有限,這小女子伶牙俐齒的,我很快就敗下陣來,我磕磕巴巴地對不上來,只好認罰。后來她看我一個人喝,著實沒了意思,就陪我一同受罰。酒到濃處,我們都不再拘謹,她對我的稱呼也不是劉老師了,改叫劉兄了。“劉兄,咱們來一樽。”說著,雙手端著酒盅跟我碰一下就一飲而盡。接下來她再吟詩一首,再和她的劉兄來一樽。
我的天,她還真像結婚前的李清照!
就這么一陣廝殺,大半瓶酒下去了,我們都有點兒擱不住。我說:“不行啦、不行啦,不能再喝了。”
蘆花說:“沒事兒,劉兄,咱們來個一醉方休。”說著她就搖晃著身子去抓瓶子倒酒,已經醉了的她一把沒抓住,把酒瓶碰倒在飯桌上,一些白酒灑在了炒菜里。我趕忙把瓶子搶過來,把她攙扶住,她身子軟綿綿的,順勢就癱在了我的懷里。這可咋好唉!我把她抱起來放在西屋的炕上。她的嘴里還一個勁兒劉兄、劉兄地喊個不停。
我站在那兒,不知所措,生怕他的父親突然闖進來說不清楚。我稍微冷靜了一下,把夏涼被拿過來給她蓋上,給她脫下涼鞋,又倒了一杯熱水放在椅子上,回到堂屋又把餐桌收拾了一番,洗刷了碗筷。聽她有了鼾聲,就悄悄地退出了屋子,把堂屋的門輕輕帶上,出了院子把大門帶上。我還是有點兒不放心,就這么走了?萬一來串門子的,正趕上是個壞人,乘人之危怎么辦?我的責任可就大了……躊躇半天,想進去看看。一推大門,鎖上了。還好,有鎖,我總算放心地離去。
第二天早上,她打來電話,問我喝多了沒有。她說半夜醒來,發現自己沒枕枕頭、沒脫衣服很是詫異,想了半天,才想起跟我喝酒的事。
“很抱歉,連飯都沒讓您吃一口,”她還說,“這次不算,等下次一定讓您喝好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