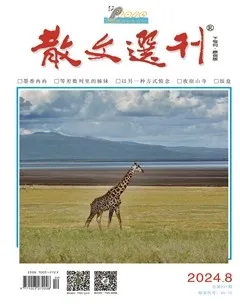漸漸深起來的蒼涼
暮色從村口涌進的時候,我獨自一人站在村口,好似一個迷路的孩子打量一座突然出現在眼里的村莊。那棵虬枝虬干的老槐樹蕩然無存,時間改變了一切,可時間不能救贖一切。
老槐樹曾經蔥蘢遮日,從茂密的枝葉里打下來的日光斑駁在我曾經少年的臉上,風從遠方來,帶來眺望的風情。老槐樹不只是一棵樹,對于村莊來說,它是游子回到故鄉看到的第一個親人。
遠遠地,看到老槐樹那高聳入云的樹冠,那份回到家鄉的溫暖宛如樹下的那灣涌泉汩汩而出,蕩漾心湖。旅途上的風塵和疲憊抖落一地,離鄉背井的凄苦和無助煙消云散。在老槐樹的眼里,多大都是它的孩子,多好都是它的孩子,多不好也還是它的孩子。眾生平等,是老槐樹恪守的神性。老槐樹是神樹,在村莊里是不宣而知的秘密。很多驅魔辟邪的民間祭祀都在它的身下一一發生,紅絲巾系滿它低垂的枝干。隔三岔五還有一堆堆的紙錢灰燼,遇到調皮的風,灰燼一飛沖天。
小時候我體弱多病,父親選擇一個黃道吉日讓我認下老槐樹為義父,祈望老槐樹庇佑我。自此,我順風順水地長大成人,負笈求學,直至工作。無論是一臉得意還是一身落魄,我總不會忘記我還有一個義父和父母親一樣在鄉下望我歸來。我常常回去,回去的第一時間就是放下所有的行囊,在義父龐大的樹蔭里享受清涼或安撫,聽它在風里給我的聲聲叮嚀。可現在是誰謀殺了我的義父,也抹殺了我關于村莊的第一印象?
后來細細詢問母親,才知道老槐樹是自己倒下了,一開始沒誰敢動它,是村里通靈的那位巫婆建議用來修建土地廟。于是,老槐樹被鋸成木板,撐起了整整一座土地廟。無數次我都不敢靠近土地廟,我生怕聽見義父支離破碎的呻吟。如同枝葉,各自有枯榮。時間的長廊里,大地上的萬物都是一陣急促的穿堂風。
經不起時光,一棵千年古樹尚且如此,那生育我的村莊呢?青草歸來,除了村主干道是水泥打成的,灰著臉,其余的小路都被青草覆蓋,通向一棟棟舊房子的幾乎挪不開腳步。田園將蕪,而現在我置身的村莊已經荒蕪,那空空蕩蕩的田野沒有稻禾簇立的身影,板結的一片,咧開干涸的嘴。良田數年不種,好比無人居住的房屋自動開裂。良田其實也不多了,只要靠近馬路的都被一棟棟五光十色的樓房占據。這些年,房子是村莊里長得最為茂盛的作物,可再茂盛的作物也結不出果腹的稻子了。可這么瘋長的作物只是大地上的裝飾。所有的新房子都雕梁畫棟,瓷磚折射最后的夕光刺痛我的眼睛。一座座新房子如這個時代一樣無限的榮光。
村莊里的鄉親一生最熱衷兩件事。一是送書,一度鄉親們以送孩子讀書為榮,誰家的孩子考學出去,哪怕再不濟也是光宗耀祖。有孩子在外工作,父母走在田埂路上都有勁兒,好像泥土不沾腳。二是建房。一生為人就要修建一棟好房子,房子好,兒子能娶得好,女兒能嫁得好。可這些年鄉親們已然喪失了送書的熱情,農家子弟即使讀大學出來還得打工。慢慢地,有很多父母不主張孩子多讀書,而寧愿把錢省下來建房,房子看得見、摸得著,還能指望娶個好媳婦。一窩蜂,房子如蜂,叮在一丘丘好田上。
富麗堂皇的房子一扇扇大門緊閉,好似暮年失語的老人,一言不發地呆立在夕照里,暮色是唯一的衣衫。偶爾吱呀一聲,走出一個老態龍鐘的老人或跳出一個歡呼雀躍的孩子,見不到一個青壯年。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條生活之路。可對于村莊來說,離鄉謀生是唯一之路。他們把低人一等的凄苦拋撒在異鄉的土地上,把思鄉之苦、思親之痛遺落在熟稔的村莊里。離開的和留下的都是苦,這些苦釀成深沉的靜默在村里貯存。還不是很黑的天色,一家家都關門閉戶了,只有微弱的燈光告訴世界,這里還依稀有人煙。外面的世界越來越繁華,村里的風景也越來越繁華,可人影兒越來越稀少,人氣越來越淡薄。沒有狗叫之聲,偶爾傳來的是電視聲。因為青壯年不在家,一戶戶人家早早關門,孩子自然也被關在了家里。一個個心靈都變得孤寂。
而我那時候的童年和少年是何等的歡悅,沒有星星的夜晚,我們齊聚在石拱橋上聽老爺爺講《三國演義》《聊齋》和《楊家將》,那些說書人滋養了我的年少時光。有星星的夜晚,我們那一大群孩子或玩兒丟手絹或捉迷藏,有時候成群結隊地去草地里捉螢火蟲。那些螢火蟲一閃一閃地在我們手上的瓶子里,點亮我們深深淺淺的夢境。
而現在,提前進入寂夜的村莊對我來說是多么的生疏。我好比一個不安的游魂,在宮殿里游走,到處是觸目的光彩,唯獨找不到出口的光亮。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可以不光鮮,但一定要光亮。我在我摯愛的這片土地上找不到內心的光亮了。
新房子都坐落在過去先人揮汗種植的良田上,而諸多的土墻老房子依舊在原地,歲月的風里,它們先后傾身彎腰,相繼露出滄桑的眼神,相繼顯出不堪的負荷,相繼吐出深沉的寂寥。曾經這些老房子里人丁興旺、五畜繁衍,白天歡聲笑語,夜晚熱鬧喧騰,而今,沒有人煙,沒有人氣,一切都是殘敗的。老房子里神龕上的先人還在否?他們愿意遷居到新房子去嗎?先人在每年的中元節還能沿著那些老路回到老房子嗎?他們可會在這個變幻無常的村莊里迷路?也許,在他們的世界里,世界還是當初的模樣,是他們熟悉和喜歡的那個村莊。老房子隨風送來陳腐的氣息,不時有瓦片墜落的回響。
我躊躇不前,離開了就回不去了,只能在可憐的記憶里尋找陸離的光影。頭頂的星星迷離清淺,似祖先深邃幽遠的眼神。夜不深,村莊的睡眠已經很深了。行走的腳步惹不來一聲熟悉的犬吠,無奈的嘆息驚不走一只小小的青蛙,深深厚厚的寂靜包裹我。
一點兒夜露打在我的額頭上,我不禁一愣,旋即明白那不是清涼,是蒼涼,是漸漸深起來的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