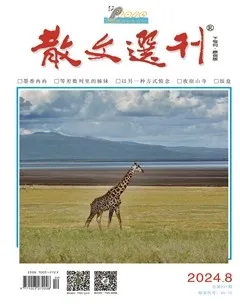蒲公英的愛
我是由奶奶撫養長大的,奶奶與蒲公英占據了我童年的主要版面。
春風輕輕一吹,嫩綠的草芽從后山坡的雜草間冒出頭,被輕柔的雨水洗過,被細碎的陽光暖過,蒲公英就咧嘴笑了,笑得金燦燦的,笑得滿地打滾兒,笑得四下撒歡兒,笑得滿世界都有了童話的味道。活潑、詩意、爛漫,這是我眼里的蒲公英。
奶奶眼里的蒲公英卻不是這樣。奶奶說蒲公英可以充饑,是“ 窮苦人的救命菜”。當蒲公英葉子很嫩時,奶奶就扛著鋤頭帶我去挖蒲公英。她把蒲公英連根挖起,我撿拾在竹筐里。在我們奶孫倆的配合下,籃筐里的蒲公英越來越多。奶奶將嫩嫩的蒲公英清炒或涼拌,就是我清甜可口的美食。
一過清明,金燦燦的蒲公英開滿了原野,奶奶就挖得更多了。這時的蒲公英可食還可入藥。太陽照在奶奶黝黑的臉上,奶奶顧不上擦拭,只是躬身勞作。實在太累了,奶奶坐在草甸上休息,任汗珠在額頭上閃亮還不忘把蒲公英編成謎語給我猜:“一個小球毛茸茸,好像棉絮好像絨。對它輕輕吹口氣,許多傘兵飛天空。”
奶奶把蒲公英洗凈曬干,賣到藥材農副產品收購站,雖然幾毛錢一斤,但多少可以貼補家用。偶爾我有個頭疼腦熱,奶奶還會用晾曬好的蒲公英泡茶給我喝。幾杯茶水過后,我的病就奇跡般的好了。在我的內心深處,蒲公英是衣食父母,也是古方良醫。
蒲公英,童年時我親切地叫它黃花苗、婆婆丁,長大后,我從書里知道,《唐本草》釋名耩耨草、金簪草、黃花地丁。《唐本草》集解,保昇曰:“蒲公英草生平澤田園中。
莖、葉似苦苣,斷之有白汁,堪生啖。”蒲公英食用歷史久遠。《本草綱目》載蒲公英于菜部,李時珍曰:“地丁江之南北頗多,他處亦有之,嶺南絕無。小科布地,四散而生,莖、葉、花、絮并似苦苣,但小耳。嫩苗可食。”又記載它的藥效,說它色味甘,平,無毒,主治婦人乳癰腫,水煮汁飲及封之,立消;解食毒,散滯氣,化熱毒,消惡腫、結核、丁腫。
遠嫁離家后,每年春天,我都會選擇一個陽光明媚的周末,去郊外挖蒲公英。
于是,我就像奶奶一樣,彎腰挖蒲公英,將新鮮的蒲公英清炒或涼拌,還學會了用蒲公英攤餅和制作標本。我把蒲公英洗凈、焯水、剁碎。在面粉里放一點兒菜籽油和適量的鹽,打入幾顆雞蛋,根據一定的比例調水,和上稍軟的面團,在里面裹上剁碎的蒲公英,再揉光滑,放進油鍋里,用手拍成薄餅,正反翻動煎烤,幾分鐘后,一鍋香脆的蒲公英餅就做熟了。蒲公英餅外酥里嫩,清香撲鼻,令人口舌生津,欲罷不能。
對那些顏值高、有眼緣的蒲公英,我就將它們進行修剪,制作成標本。標本里有我骨子里的鄉土氣息和唯美情懷。
我將蒲公英餅與晾干的蒲公英以及標本一起打包,托順豐快遞郵寄給奶奶,這件事我堅持了多年。我很慶幸,我的奶奶一直住在原址,讓我這株蒲公英無論飄多遠,都知道自己生命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