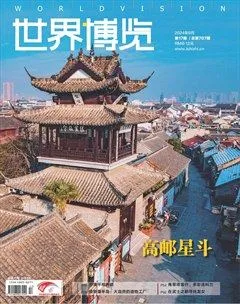普洱江湖


普洱茶可謂家喻戶曉。作為一種產自云南的茶葉,在茶馬古道的加持下,它響亮的名氣、昂貴的價格、紛繁的種類似乎古已有之,理所當然。但對于人類學家張靜紅來說,普洱茶卻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云南的成長經歷和人類學家的敏銳洞察,驅使她去探究普洱茶背后的故事。
正宗茶葉如何被“建構”
從2007年開始,張靜紅輾轉多地,從西雙版納的邊地茶山到中國香港、臺灣的高檔茶樓,跟隨普洱茶的生產、消費鏈,對其進行了長期的民族志田野調查,于2014年出版英文著作《Puer Tea:Ancient Caravans and Urban Chic》,該書于2015年7月被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ICA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授予2013—2015年度英文社會科學杰出圖書獎。作者在英文版基礎上以中文重寫,并綜合過去近十年的回訪與變化,終于在2023年出版《生熟有道——普洱茶的山林、市井和江湖》。借用作者的話,“‘回望’故鄉意味著‘轉熟為生’,需要跳出自己熟悉的場域,站在另一個文化的視角,以關愛但又不無反思的眼光來重新審視本土文化。”在這樣一個對故鄉再發現的過程中,作者將普洱茶的前世今生一一展現。

作者以4個主題架構本書,分別是春生、夏熱、秋愁、冬藏,既對應了普洱茶生產周期的四季節點,又以季節的特征暗示了普洱茶所經歷的跌宕起伏,比如“春生”的主題隱喻了普洱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商業價值的持續升溫。在“春生”的開篇,作者寫到她在香港茶樓偶遇兩餅民國時期的老茶,其票據指引她來到了易武——一座位于中國和老撾邊境的深山小鎮,隸屬于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勐臘縣。這座磚瓦青石建造、茶山環抱的古樸小鎮,見證過普洱茶的輝煌歷史,出現過眾多紅極一時的制茶商號。在這一部分,或許是受到影視人類學訓練的影響,作者通過極富畫面感的民族志敘述與充實的史料結合,回溯了清末民初的馬幫貿易,20世紀50年代的物質匱乏,改革開放的繁榮,再到新世紀的后現代消費語境。在呈現普洱茶歷史縱深的同時勾勒出邊陲茶鄉和茶農的起起落落,以及產茶技術的演進。
在作者看來,普洱茶能有如今的景觀,90年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易武的手工制茶始于17世紀,隨著現代化茶廠在西雙版納其他地區的出現而逐漸沒落,直到20世紀90年代,臺灣茶人到訪易武,才使得這一失落的制茶工藝重新興起。普洱茶經過幾十年旅行,又回到了它的出發地,由此聯結起了一個廣袤的時空網絡。同時到來的還有“正山”“越陳越香”“可以喝的古董”等本土傳統之外的概念。正是這些概念為日后普洱茶的商業炒作和口味建構埋下伏筆。
“建構”是本書的關鍵詞之一。作者將生動的民族志敘述與人類學理論融合在一起,通過多種理論視角關照普洱茶的傳奇如何被建構,又是如何被消費,由此洞悉其背后錯綜而廣闊的圖景。20世紀90年代,臺灣茶人造訪易武,正是源自對“正宗”和“正山想象”的狂熱。作者將對于“正宗”的建構與猶太學者瓦爾特·本雅明的“靈暈”(Aura)理論相聯系,揭示了二者都是對某種不可復制的“本真性”的狂熱。瓦爾特·本雅明在其《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中探討了藝術的本質、功能與人類感知方式的關系。本雅明認為,藝術的靈暈來自原作獨一無二的“本真性”,如盧浮宮中僅有的《蒙娜麗莎》;而攝影、電影和復印畫作為現代復制技術的產物,挑戰了人們對于藝術靈暈的認知。易武手工普洱茶的復興體現了后現代語境下消費者對于“靈暈”的追求。但不同的是,喝熟茶并非易武本地人的習慣,因此臺灣茶人并沒有看到他們所期待的大量陳放數十年的所謂真品。于是他們轉而關注易武新茶的制作,請當地人復原了手工制茶的工藝,結合易武本地悠久的茶文化歷史,共同建構起何為“正宗”的新標準。在與西方理論的對話中,這樣一種“靈活的轉化”指向了一種獨屬于中國文化特有的概念——江湖。
中國社會的“江湖”文化
“江湖”作為全書的另一個關鍵詞,蘊含著多層次的意義。它既指普洱茶市場的混亂和風險,也反映了全球化與本土互動中,在地性所開辟的新可能。“易武正山”的話語形成導致普洱茶價格飆升,使這個原本鮮有人問津的小鎮,每到春天都擠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甚至海外的茶商前來收購茶葉。在巨大經濟利益驅使下,茶葉來源變得魚龍混雜,冒充“正宗”的現象層出不窮,因而在茶商與茶商之間,茶商與茶農之間,形成了“江湖”的第一層含義。
行走普洱江湖,茶商不僅需要具備識別茶葉品類與產地的高超技能,更重要的是理解一種交織著人情的文化邏輯。作者巧妙地借用了結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關于食物“生”與“熟”二元對立的理論,來解讀茶商與茶農之間的江湖關系。列維-斯特勞斯認為,食物在由生到熟的過程中,越多人為干預,食物越遠離自然,越接近文化。普洱茶從生到熟的過程,體現了從自然向文化的轉化。而這一過程同樣可以啟發我們理解茶商與茶農之間的互動。外來的茶商與本地茶農之間的關系,也經歷了類似的“生”與“熟”的轉化。對立與合作的張力背后,更多的是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經營規模較小的茶商通常會選擇與易武本地家庭建立合作關系。這種合作并非通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而是基于互相信任的口頭約定。經過長時間同吃同住、生意往來,而逐漸建立起的人際紐帶,雖然基于金錢利益,卻在“時間的打磨中融入了越來越多的人情”。茶商收購茶葉的過程,也是一個被本地文化接納的過程。相較于象征現代理性科層制的茶葉公司,這種帶有江湖氣息的合作方式似乎與“正宗”普洱茶手作的方式有更多共鳴,但同時也預示了普洱茶整體的混亂與生機。

本書中,“江湖”的第二層含義更接近于武俠小說中與廟堂相對的社會空間,一個注重經驗、個性和靈活性的場域。面對普洱茶市場魚龍混雜的現狀,許多人呼吁建立統一的官方標準,正本清源,像法國紅酒一樣,從生產到品鑒,每個環節都有明確的規則。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關于普洱茶的統一標準始終在搖擺,更多地呈現為一種在茶農、茶商、收藏家與消費者之間達成的默契。作者認為,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與中國本土的江湖文化密切相關。相較于一般意義上的忠義和爭斗,在本書中,江湖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象征中國人對真相和自由的浪漫追求與實踐。普洱茶的走紅出現在21世紀初的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化使各地聯系緊密,地方差異和界限逐漸縮小和模糊。然而,這并非一種單向的影響。如后現代理論家大衛·哈維所言,全球化帶來的同質性反而促使地方以不同方式建構并強調自己的在地性。普洱茶的手工傳統、與自然的聯系,以及作為地方身份認同的象征意義,使其與江湖文化相近,也體現了一種在地性。這也注定了普洱茶是“多變的、標準模糊的、靠人情關系的。或者說這種模糊、曖昧與多元,造成混亂的同時,也為普洱茶提供著持續的生機”。
《生熟有道》以生動的民族志敘述、詳實的史料和清晰的論證,為中國的飲食人類學提供了一個研究范本。通過追溯普洱茶的時空旅行,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看到了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在不同時間、空間以及人際關系網絡里發生的多層互動,同時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普洱茶如何在跨地區與跨文化脈絡中被發現、建構、消費。如作者所說:“理解中國江湖文化的本質,有助于解讀今天普洱茶魚龍混雜的局勢。”普洱茶的江湖,本質上也是人的江湖。在人與茶的相互依存中,在人與人的合作較量中,行動者們的生存之道、解決問題的方式必定為我們帶來新的思考與啟示。
(責編:劉婕)
普洱茶的分類

根據張靜紅介紹,目前市場上的普洱茶主要有三類。第一類“生普洱”是茶葉采摘之后,經過炒茶、揉捻、曬干等粗制環節得到毛茶,再經過揀梗、壓緊和包裝等環節后得到成品即生茶,口感近似綠茶。第二類“老生茶”是在生普的基礎上,經過長時間存放和自然發酵而來。第三類“熟普洱”是在生茶的基礎上經過專業的人工發酵技術或稱“渥堆”,在短時間內實現由生轉熟的黑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