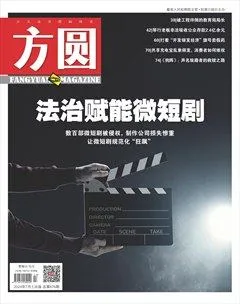《狗陣》:聲名狼藉者的救贖之路






此時只有城內的瘋子忙碌起來,他懷揣著赤峽鎮所有門鎖的鑰匙,將所有動物一一放出。赤峽鎮再次被填滿,只是這次成了動物的王國,孔雀躍上了蒙塵的鋼琴,老虎優雅地在街中散步,流浪狗們不再躲躲藏藏……
近期上映的電影《狗陣》可以放進“境遇電影”這個電影認知模型中來解讀。所謂“境遇電影”,簡單來講,關注的重點是角色主體與情境的相遇。導演管虎駕輕就熟地將人物背景放置到中國西北地區壯麗而荒涼的景色之上,鏡頭聚焦一個沉默的刑滿釋放人員二郎,講述他回到故鄉加入當地的打狗隊,在捕狗過程中與一只黑狗建立感情,從而相互救贖的故事。
可以說,《狗陣》是一部純粹以人為軸心講述故事與闡述導演思想的反類型電影。與傳統語境中人物與觀眾之間呈現類似“主體與客體”對立關系不同,《狗陣》的觀感將二者合一,當二郎在銀幕之上騎士般地歷險時,觀眾則化身白馬,與之共同經歷。
之所以能很好地利用“感同身受”這個必要中介,有賴于導演管虎對當下個體生命經驗的細膩體認。變化發展的時代,管虎不介意回頭講一個發生在16年前的故事,在他看來,可以借電影中寓言式的人事捕捉當下的一種集體情緒,而這樣的記錄,如管虎所說,“是可以超越任何時代階段的”。

《狗陣》在國內上映前,已在5月沖進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官方單元。這是繼2006年《江城夏日》后,時隔18年華語電影再次奪得“一種關注”單元最佳影片大獎。該單元以影片獨特的審美和新穎奇異的小眾風格而聞名,旨在表彰和鼓勵具有創新性和獨特視角的電影作品。擔任本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評審團主席的加拿大導演格扎維埃·多蘭稱贊這是一部“大師級導演作品”。
赤峽鎮的空間敘事
萬物都對我們不利,更準確地說,萬物都是冷漠而淡然的——這是《狗陣》開場帶給人的觀感。攝影機用遠景及全景展現著大自然隨機無心的面貌,西北戈壁灘上飛沙走石,灰黑色的山丘如游蛇起伏,上生粉刺樣纏結的矮樹,一派荒涼景態。打破這種平靜的是屏幕右下角山坡突然奔出的狗陣,一群流浪狗以泄洪之勢沖下公路,致使一輛目的地是赤峽鎮的公車側翻,人狗沖突出現在故事伊始。
主人公二郎在驚魂未定的人群中,著舊紅色上衣,始終不發一言。經由前來救援的警察查驗,二郎身份確定,他是此地10年前因過失殺人入獄的風云人物,剛剛出獄。
二郎在片中一直是失語的存在,導演管虎認為這個特質可以用來表現人物的“隔絕或抗拒”。語言一旦失去,人物就會用形體去表達,所以觀眾才會看到一個佝僂著肩背的彭于晏,這有別于他在其他作品里的性感表現。
而對于電影來說,身體是最高級別的語言之一,這不單是因為它的直接,更重要的是它就是我們本身。為了呈現整個世界對人的這種“摩擦感”,管虎不僅在技術上采用數字轉膠片的顆粒感畫質,對空間的利用也上升為高度的自覺,也就是說,他讓整個赤峽鎮成了二郎這個沉默的身體需要去突破的障礙。
我們來看管虎對赤峽鎮這個物理空間的營造。跟隨二郎返鄉的步伐,觀眾進入一片獵奇之地——衰敗的赤峽鎮到處都是空置的樓宇,街坊上隨處安置著老弱之人,說明年輕人的大量外流,流浪狗泛濫成災,大喇叭上高歌猛進的播音腔是無關緊要的背景音,反襯著眼前蕭索的一切。
二郎的歸來是一枚石子被拋入靜水,激起陣陣水波。餐館的老板、獨居的鄰居、耀叔及二郎的仇人胡屠夫等角色紛紛登場,與二郎發生對話和碰撞,場景豐富到飯店、胡屠夫的羊肉店、二郎的家、二郎父親避世的動物園以及廢棄的游樂場。
還有些空間用來安置角色自身的經驗感受,比如二郎與黑狗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是在一片廢棄的居民樓間,內急的二郎無意間闖入黑狗的領地,在其撒尿的地方如廁,惹動黑狗對其狂吠。這才有了之后二郎報復性捕狗,被其咬傷的情節。
看似瑣碎日常,實則是邀請觀眾,一步步進入二郎的價值系統,他從黑狗被驅逐的境遇中看到了同樣得不到接納的自己,這為二郎對黑狗的同情提供了情感基礎。

僅從故事層面上看,《狗陣》的確是一部非常簡單的電影,影片以線性敘事為主導,講述二郎與黑狗從互相對立到相知相惜的過程。它的出色來自通過空間所營造的敘事動力,赤峽鎮如同一個少有人關注的舞臺,映射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在這里,掉隊之人與流浪狗的命運被懸置,凸顯人物在空間中的沖撞與抽離。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影片中的空間不再是一個容器,空間本身就是意義建構的方式,空間不只為了故事服務,也為創作者的美學和世界觀服務。
警惕人類中心主義
《狗陣》作為一部聚焦于狗的電影,自然會涉及人跟動物關系的討論。導演管虎本人也養狗,他認為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但他在電影中卻刻意剝離了黑狗身上的寵物屬性,這從他選取的黑狗品種中可以看出,影片中的黑狗屬于中華細獵犬,身形精瘦沒有半點兒呆萌氣質,反而與二郎的形象有著某種相似性,這強調了二者作為兩個獨立個體的存在。
影片中,二者親密關系的建立也頗為波折。在被黑狗咬傷后,二郎加入耀叔組織的捕狗隊,但在目睹同伴對狗的暴烈與不當交易后,二郎產生了排斥情緒,這從他悄悄歸還小女孩的寵物狗,放走被圍堵的流浪狗可以看出。但其他人對狗的態度卻出奇一致,電影中有這樣兩幕:一幕是抓狗現場,當地記者跑來采訪捕狗隊成員,一位成員說附近馬上有廠子要建了,狗卻到處跑,不抓不行;另一幕是放走流浪狗的二郎被同伴拳腳相向,同伴質問他“狗咬了這么多人,你卻把它放了,安的什么心”。
赤峽鎮要發展,動物反而成了最大阻礙。這兩種熟悉的語境,反映出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這種思想由來已久,支配著人類對動物的基本態度,鼓勵著人性中的傲慢、殘暴、麻木和自私,致使動物被驅逐到道德的荒原之上。
管虎在電影中呈現出了這種思維帶給動物們鋪天蓋地的浩劫,受到驅逐的不僅是鎮上的流浪狗們,還有即將關閉的動物園里的瘦猴、孔雀和老虎。不僅如此,鎮子不遠處胡屠夫的屠宰場里,那些因吃了藥而生命垂危的羊以及那些蛇的處境,無不凸顯人在宇宙中的核心位置。
為了引導人類反觀自身,管虎巧妙利用胡屠夫這個角色,他不僅是二郎當年過失致死年輕人的叔叔,與二郎有仇,給二郎不停制造回鄉的障礙,他還是鎮上積極入世追趕潮流的創業典型,當人人都沒有錢賺的時候,他卻能將業務從羊肉館拓展到養蛇賣蛇,發家致富。他的廣告聲稱“不打藥”“原生態”,但在片中二郎去屠宰場找狗的鏡頭里,分明能看到胡屠夫羊圈中隨時倒地的白羊。
電影后半段,地震來了,象征著來自大自然的審判,胡屠夫的住處在地震中鬧了蛇災,這個養蛇先進戶終于被反噬……此處設置,不能不說是導演用心良苦的點化。
米蘭·昆德拉曾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寫道:“真正的人性之善,只有在它的承受者毫無力量的情況下,才能盡其純粹、盡其自由地展現出來。人類的真正道德考驗,最根本的考驗,就在于你怎么對待這些命運完全由人類來擺布的生命:動物。”
以這個標準來看,片中二郎對弱者的庇護是真正的人性之善。這表現在風暴夜他與黑狗的相依為命,以及他與黑狗在十日隔離中建立起來的友情。片中狗陣第二次出現,是在黑狗生命垂危之時,二郎用摩托車把它載回家,路遇漫山遍野的狗群,此時的狗陣全無電影開場時的那種奔突,而是靜默站立,如同歡迎同類的歸來。受到觸動的二郎選擇下車,推著像英雄一樣的黑狗,在狗陣的注視下緩緩前行。
我們能看到管虎在《狗陣》中的努力,他試圖提出一種偉大的構想,在這個構想中,動物不再是由人類觀看與界定的客體、對象,而是與人相互救贖,和諧共處,這是一個觸及人的存在困境,進而反思現代性的問題。
影片靠近結尾處那個超現實主義風格的日全食片段,擁有著全片最大的暖意,導演憑借非凡的空間場面調度能力,完成了這樣一場迷人夢境——日全食來了,赤峽鎮的人從各個地方奔涌而出,他們或步行或騎行,逐漸匯集到流浪狗們曾經蹲踞的山梁上抬頭看天,此時只有城內的瘋子忙碌起來,他懷揣著赤峽鎮所有門鎖的鑰匙,將所有動物一一放出,赤峽鎮再次被填滿,只是這次成了動物的王國,孔雀躍上了蒙塵的鋼琴,老虎優雅地在街中散步,流浪狗們不再躲躲藏藏……
在如此動人的隱喻空間中,蘊含著創作者虛化時空的真正的創建意義。
那些聲名狼藉者
無論是《斗牛》里被人們看作傻子的牛二,《殺生》里瘋瘋癲癲的牛結實,《老炮兒》里跟不上時代發展的北京大爺,還是《八佰》《金剛川》這種商業大制作中嵌入普通人的視角,關注時代進程下普通人的命運走向,是管虎一直以來創作表達的重心。
而管虎之所以拍攝《狗陣》,也是源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天,這個本該普天同慶的日子里,卻傳來老家親人去世的消息。管虎想要去打撈那些被遺忘和遮蔽的個體生命故事,他認為這是一個電影拍攝者的應盡職責,哪怕他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聲名狼藉者的寂寞。
為什么我們要關注那些聲名狼藉者?
《狗陣》讓我想到了福柯,這位法國偉大的哲學家,早在20世紀,福柯就具體關注了那些聲名狼藉者的生活,他以巨大的悲憫和憤慨,用文字將那些歷史上的罪犯故事勾勒出來。福柯認為,每個時代都有所謂的聲名狼藉者,社會的秘密更多是由這些聲名狼藉者揭示出來的。人的生命不是日神阿波羅式的穩定和不變,同時還具備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歡。福柯最后指出,所有的怪人或罪犯,我們都不應該拋棄歷史去尋找他們的成因。這使他們的故事能夠劃破理性的黑夜,告誡人們警惕理性的過度發育。
福柯將人的生命看成是一件有待塑造的藝術品,這與《狗陣》的價值觀點不謀而合。有關重塑與再造,電影中有一處非常自覺且有意味的情節設置——出赤峽鎮到外面的世界需要跨越一個鴻溝,二郎的第一次跨越,是被尋仇的胡屠夫一干人等逼迫,但后因黑狗的叫聲阻攔而放棄;第二次嘗試,是在尋找失散黑狗的途中,二郎發動摩托車試圖飛躍過去,卻以人車落坑而告終;第三次是在影片結束,此時黑狗已死,親人已逝,二郎背著黑狗的后代,決意離開困住自己的赤峽鎮。當觀眾以為“事不過三”,二郎肯定可以跨越眼前的障礙,從此意氣風發之時,人車還是卡在了此處,二郎還是從坑里狼狽地爬出。
這才是真正的人生,導演說:“人生就是永遠過不了的坎,可此時他的心態不一樣了,所以整部電影他跟狗的感覺就不一樣了。”的確如此,對于當下每個個體而言,即便是道路上鴻溝依舊,只要保有“再上路”的勇氣,人終究能夠達成所愿,成為另一個不同于原初的自己,從而讓生命成為一件有自我風格的藝術品。

劇情簡介:
十余年前的西北小鎮,剛出獄的二郎(彭于晏 飾)重歸故土,面對偏見,面對防備,他不知該如何開啟新生活。迫于生計加入打狗隊后,二郎拯救了一只流浪黑狗,他也在和黑狗的相處中獲得了再次上路的勇氣。生命在暗處的綻放更兇猛有力,一人一狗在互相救贖中,擁抱著彼此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