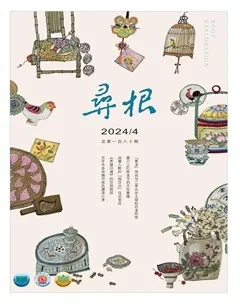漫談兩晉官員釋褐與家世門第的關系

眾所周知,兩晉是中國古代門閥士族制度成熟穩固的時期,其發展形態與此前的戰國秦漢及以后的唐宋元明清截然不同,最顯著的特點莫過于身份地位繼承制和資源權益世襲制的盛行,由此塑造了階級固化、對流停滯的封閉式社會結構。門閥士族制度在這一時期起到支配作用,家世門第為決定因素,清濁流品是游戲規則,旨在按照不同家境出身彝倫攸敘、各司其職,達到各得其所、涇渭分明的理想格局。這種“世卿世祿”的貴族制原理集中反映在體制內的仕進層面,尤其是登仕首獲正式官職的環節“釋褐”。“釋褐”,顧名思義就是脫掉庶民穿著的由獸毛或粗麻編織的衣服,換上官服搖身一變成為官僚的過程;它又稱“起家”,意為士子脫離各自的私家,而在國家的公共場域實現同皇帝新的人際結合。作為政治生涯之起步,釋褐或起家又被賦予“出身”資格的含義,濃縮幾乎全部家世信息和對未來前程的預期。最早研究六朝釋褐起家問題的是日本學者宮崎市定,他說:“弄清楚九品官制的輪廓,就可以推測連接九品官制和中正鄉品的是起家之制。在現實中規定貴族門第高下的,除此起家之制外,別無其他。這在當時的社會里,大概是大家都十分清楚而無須特別指出的情況。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它變得最為模糊不清。其模糊程度不僅僅對于我們這些外國人,就是對中國人來說,似乎也完全一樣。”(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韓、劉建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也就是說,釋褐起家可以體現家世門第,而弄清家世門第則是六朝史研究中解決一系列問題的突破口。
以釋褐起家反觀家世門第,前提是兩者按特定比例匹配關聯。受宮崎市定的影響,學界普遍關注起家官品與人物鄉品之間的數量關系。宮崎市定提出著名論斷:“獲得鄉品二、三品者,可以從六、七品的上士身份起家。其次,獲得鄉品四、五品者,可以從八、九品的下士身份起家。……要言之,制定了起家的官品大概比鄉品低四等,當起家官品晉升四等時,官品與鄉品等級一致的原則。然而,在實施過程中,想來會允許在上下浮動一個品級的范圍內酌情調整。”(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從理論上講,所謂“鄉品”實則是借清議鄉論之名行銓量門第之實,因為鄉黨評議人物的道義行為與其在鄉里社會中的責任貢獻緊密掛鉤,高門大族實力強,自然責任重、貢獻多,加之資源豐厚,在培育卓越人格和知識素養方面得天獨厚,高門第本身就意味著高品質,反之亦然,時人便直接以門第評估士人了,鄉品后來逐漸蛻變為單純表示門第的門品。不過,魏晉士族體制初成,閥閱壁壘尚未完全固化,階級流動的大門也未徹底關閉,才學、德性、業績等非門第要素及中正官主觀意愿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鄉品等級。如《晉書》卷四六載燕國霍原舉寒素科被中正劉沈評為鄉品二品。《世說新語·賢媛篇》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載,卑微的陶侃因緣際會,經十郡中正羊薦舉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而且鄉品并非固定不變,會因各種變故隨機調整。《通典》卷十四載:“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闕,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李含、郄詵、韓預皆因名節,夏侯湛因賢良考試成績欠佳而降鄉品。受意外因素的干擾,鄉品會出現背離門第的現象,在此情況下探討鄉品與起家官品的對應勢必產生誤差。鑒于此,筆者有個不成熟的想法,即跨越鄉品,將鄉品所代表的核心內容家世門第與起家官直接掛鉤,這樣可以盡量濾除鄉品評議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更能彰顯士族社會唯門第是從的本質。
為弄清釋褐起家與家世門第的關系,而不再糾結其與鄉品的搭配比例,茲搜集《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起家28事例(如右表)加以分析。
28事例的搜集篩選遵循兩條標準:第一,登仕必有明確標識,如起家、釋褐、解褐諸語詞,杜絕把傳記履歷的首位官職簡單視為起家官的現象。這是因為當時官貴仕進以職務眾多為榮,履歷蕪雜冗長,史家撰史無法面面俱到,只得截取某個輝煌的片段,除起家外,特別留意出身門第準許跨越的資格線和所能達到的終點線。易言之,史傳所載履歷缺少標識的首項官職,雖不排除起家官的可能,抑或為具備身份象征意義的某個顯職。故筆者甄別起家事例采取寧缺毋濫的態度,以確保結論的穩妥可靠。第二,起家人物的世系官資必須明確,上限追溯至曾祖,畢竟士族多為晚近顯貴,三代百年足夠積淀家業。聯想后來南齊御史中丞沈約彈劾與富陽滿璋聯姻的東海王源,辨其門第即從位登八命的曾祖王雅開始(蕭統、李善:《六臣注文選》卷四十,中華書局,2012年)。北魏江陽王元繼追憶:“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為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魏書》卷一百八《禮志二》,中華書局,1974年)據曾祖以降三世官資核算閥閱等第,或許是魏晉積習的延續。史傳若未記曾祖,暫且以父祖為準。
起家官及其品級,《通典》卷三七《職官·秩品二》一查便知,困擾筆者的是世資門第的核定。祝總斌先生系統剖析六朝士族的層級構造,他在“二品系資”的基礎上繼續拓展,指出二品鄉品是由累世五品以上官資換來的(個別可適度延伸至六、七品的清官部分),在官品一至五品范圍內又以三品劃界區分一流高門和一般高門(祝總斌:《材不材齋史學叢稿》,中華書局,2009年)。這似乎還透露出一條隱含信息,即一流高門授予鄉品一品,一般高門授予鄉品二品。我們知道,九品官人法鄉品設九等,但歸屬高門士族的卻只有一、二兩等,是為上品,豈不恰好對應一流和一般高門?聯系日后北魏孝文帝厘定胡漢姓族的量化標準,胡人的“姓”與“族”,漢人的“甲乙”和“丙丁”之間,約略同以三品劃界(劉軍:《論北魏士族的門第等級——以釋褐為中心的考察》,《西南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六朝士族的等級體系又被古代日本模仿,五品以上的堂上貴族,三品以上稱“貴”,四、五品稱“通貴”,權力待遇迥然有別。有理由相信,北魏和古代日本的貴族制都是魏晉典章的翻版,禮失而求諸野,據此反觀制度母體何嘗不可。世資不只一代官爵,只好采取計算均值的辦法綜合衡量,均值一至三品為鄉品一品之一流高門,四、五品為鄉品二品之一般高門,再由此探尋門第與起家官的搭配關系。
通過28例材料,我們從兩個角度進行統計分析。先以起家官品為基準,四品官起家1例,五品官起家2例,固定對應一流高門,且世資均為一品。六品官起家15例,對應一流高門者4例,其中1例世資一品,3例世資三品;對應一般高門者11例,其中3例世資四品,3例世資五品,3例世資六品,2例世資七品。七品官起家9例,其中對應一流高門者4例,1例世資一品,1例世資二品,2例世資三品;對應一般高門者5例,3例世資四品,2例世資五品。八品官起家1例,對應一般高門,世資四品。再以世資均值為基準,一流高門四品起家1例,五品起家2例,六品起家4例,七品起家4例;一般高門六品起家11例,七品起家5例,八品起家1例。通過兩方面的數量統計,可大致推導如下結論:
首先,28例中絕大多數人物的世資在五品以上,少數為六、七品清官,俱系士族身份無疑。其釋褐起家的層級分布在四至八品間。乍看起來無甚稀奇,但如果將六朝官品與上古宗法內爵分封及秦漢祿秩串聯起來,便不難發現問題的端倪。中國古人習慣把宗法內爵、秦漢祿秩和六朝官品三類完全不同的事物置于同一發展線路上,認為相互間存在緊密的關聯。宗法內爵序列中的公卿,對應祿秩萬石至中二千石,官品一至三品;大夫對應祿秩二千石,官品四、五品;上士對應祿秩千石至六百石,官品六、七品;下士對應祿秩六百至二百石,官品八、九品。庶民之府史胥徒對應祿秩百石以下之斗食小史、官品流外品(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由此說來,起家官四、五品相當于內爵大夫和祿秩二千石,六、七品相當于內爵上士和祿秩千石至六百石,八品相當于內爵下士和祿秩六百至二百石。我們知道,內爵士以上皆屬貴族階級,士又分上士和下士,前者是貴族的起點,后者為庶民的終點,由此在士庶之間形成過渡緩沖帶,以調解階層間的關系。按照宗法制嫡長子繼承的原則,大夫的嫡長子繼承大夫職位,余下別子分封為上士;上士的嫡長子繼承上士職位,余下別子則為庶民,庶民奮斗尚可躋身下士,成為最低級的貴族。這樣的話,四、五品起家者可視為大夫的嫡長子,六、七品起家者可視為大夫的別子或上士的嫡長子,而八品起家者則視為奮斗成功的庶民。他們覆蓋了宗法貴族的底緣,自然也就成為六朝判定士族身份的準入資格線。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宗法內爵還是門閥士族,在理念上均未完全封閉士庶流動的大門,而是酌情為庶民升進預留一定的空間,以保持社會應有的活力,這個良好的初衷直到南北朝仍然保持,只是縫隙狹窄、作用有限而已。就貴族內部來看,五品以上起家和六品以下起家是大夫與士之質的差別,兩者地位之高下,應體現在各自的門第差異上。
其次,門第等級與起家官品絕非精確的定點對位,而是概略式的區域對位,所以,不必過分糾結鄉品與起家官品究竟差幾級的命題。大致而言,內爵大夫層位的四、五品高階起家是一流高門的特權,宮崎市定指出,四品是臣下絕對不可能獲得的起家官,屬于“宗室選”的特殊層位;五品官起家則多為三公子弟,超越了中正所能評議的范圍(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可見,四、五品起家者非但出自一流高門,而且必須位極人臣抑或皇室血脈,四品起家的司馬貴為宗室元老,五品起家的何尊、王濟皆三公之后,足為明證;除此之外,世資遜色的一流高門釋褐只能就任六、七品官,雙方的差距好比大夫的嫡長子和別子。六品是一般高門起家的上限,如果一般高門正常授予二品鄉品的話,那么起家官品的確比鄉品低四級,宮崎市定顯然以此作為綜合銓量的基準線,未必士族都以六品起家,只要折中起來達到這個平均水準即可。也就是說,二品鄉品七品以下起家者與一品鄉品五品以上起家者互相抵消,均值恰好為六品,當然宮崎市定還有其他方面的考慮,促使他視六品為貴族線的最優解。不過,這樣一來,一流高門中宗室和三公子弟以下者的鄉品就不能是一品,而是退居二品了,其與祝總斌先生門第層級劃分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一般高門釋褐以六、七品釋褐為常態,符合內爵上士及其嫡長子的身份,別子就只能以八品下士起家了,28例中恰有1例八品釋褐者,完整補齊了擬制宗法貴族的分封體系。足證,古人以門閥士族比擬宗法貴族是有一定道理的,或者說是模仿宗法貴族的構造機理設計閥閱流品規則。
再次,衡量士族門第與起家官的關系,不能只看官品的表面文章,還要留意職務的效力屬性。起家官品與門第差距未及四級者,主要有四類:一是東宮及王國屬員,如王文學、太子舍人;二是幕府僚佐,如相國參軍、征西參軍、護軍參軍;三是清望上選的文職,如秘書郎、佐著作郎;四是官府的實權要職,如尚書郎、縣令。前兩類均可享受國主或府主的人脈資源,借其勢力搭建日后升進的跳板。后兩類則以崇高的聲望度和實際權力攫取政治資源。總之,都能以豐厚的利益回報補償起家環節暫時的低落。實際上,只要對家世背景和個人能力充滿自信,根本不必計較仕途起跑線的前后,士族釋褐降階倒轉也是比較常見的現象。與其在本品末流擁堵,不如選擇次等上選;與其深陷競爭旋渦,不如保持“止足”心態退而求其次。
最后,宮崎市定鄉品與起家官品相差四級的理論,確如很多學者所說只是趨勢概略性的,因偶然因素造成的個別偏差勢所難免。他為此設定了誤差修正量,即基準值上下各浮動一級,還從史料學的角度特別強調:“我們在正史列傳中能見到的人物經歷,更多屬于打破標準形式的特殊情況。但是,如果因為個例人物的情況不相符合,就完全否定原則的存在,那就失之偏頗了。”(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韓先生補充解釋:“可以原則上認同宮崎的判斷。至于是否嚴格按照相差四級授官,恐怕就未必了,這樣的例證不難找到,畢竟那是一個人治的社會,左右的因素頗多。但是,因為執行上的浮動而欲徹底否定鄉品和官品之間的大致對應關系,把具體操作上困難重重的人事完全理解為隨心所欲的長官意志,那就偏差太遠了。有制度就有規矩,一定的準則實際上有利于官府的具體執行,卻限制不了特權階層的法外運作。準則和特權反映為常例和破例的情況,兩者并存,并不是非此即彼或者相互否定的關系。”(《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譯者序)依筆者愚見,只需作兩方面的思路調整,即可規避上面煩瑣的說明。跨越鄉品,把釋褐起家同閥閱世資直接掛鉤已如前述,以最大限度減少清議鄉論等主觀因素對硬性制度的干擾。再有,分析起家官品與門第等級關系時,變定點對位為區域對位,以各自上限為基準衡量整體差距,一流高門和一般高門釋褐的上限分別是四、五品和六品官,若兩者理論上分授一、二品鄉品,則起家官品與門第鄉品差四級的結論確鑿無疑。不過,應當注意到,起家官品是向下兼容的,以四、五品官為上限的一流高門可以六、七品官釋褐,以六品為上限的一般高門可以七、八品官釋褐,兼容的部分與上限都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如此一來,既能體現不同門第間的落差,又能解釋相互重疊的交集,何必宮崎市定那般浪費唇舌。
綜上所述,門閥化是兩晉社會的典型特征,不同家世出身者在身份等級體系中均有固定的位置,其個性發展和人生旅程被宿命般決定。就政治權力的分配而言,仕途的起點、終點以及連接二者的晉升通道與閥閱世資保持密切的關聯。尤其是官場最為注重的釋褐起家,更是具有標榜門第的特殊功效。它與門第等級的比例對應關系實則是流品秩序的集中反映。宮崎市定提出的起家官品與鄉品相差四級的著名論斷有合理的成分,但是無法解釋眾多的特例,因而存在改進的余地。鄉品固然應與門等合流,但畢竟還受人為因素的左右,遠不如先世官爵世資穩定可靠,直接探討釋褐起家與先世官資背景的關系更能展現門閥體制之特質。所謂四等差,僅指各級起家的上限而言,至于向下兼容的部分自然就不成立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古鮮卑拓跋氏士族化進程研究”(項目編號:19BZS05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