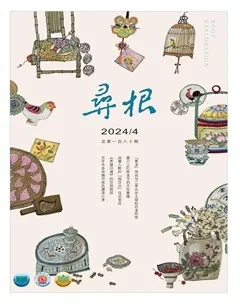民國女理發(fā)師與女子理發(fā)業(yè)
“頭發(fā)”在近現(xiàn)代中國內(nèi)蘊(yùn)深刻的政治意涵與社會(huì)功能。辛亥以降,中華民國臨時(shí)政府頒布剪發(fā)令,掀起自上而下的男子剪辮風(fēng)潮。受其影響,部分女學(xué)生起而響應(yīng),率先剪去頭發(fā),但此舉反遭學(xué)校及地方政府抵制,這與民國當(dāng)局始終力倡廢禁纏足形成鮮明對(duì)比。“五四”前后,女子剪發(fā)問題重又為輿論所重,“女子自決”口號(hào)的提出及國民革命的推進(jìn)終使女子剪發(fā)運(yùn)動(dòng)勢(shì)不可遏。
女理發(fā)師的出現(xiàn)與女理發(fā)店的興起
學(xué)界通常認(rèn)為,中國倡導(dǎo)女性剪發(fā)的第一人是《女界鐘》作者金一(金天翮)。金氏在《女界鐘》第3節(jié)“女子的品性”中主張:“今西方志士,知識(shí)進(jìn)化,截發(fā)以求衛(wèi)生,吾以為女子進(jìn)化,亦當(dāng)(自)求截發(fā)始。”但何者為近代中國第一位女理發(fā)師,學(xué)界則尚無定論。女學(xué)生群體是民國初年開展剪發(fā)實(shí)踐的主力軍,1912年湖南衡粹女校某生便組織“女子剪發(fā)會(huì)”,但女學(xué)生僅是互相為對(duì)方簡(jiǎn)單剪去辮子抑或發(fā)簪,并不可能在未接受訓(xùn)練的前提下?lián)u身一變成為理發(fā)師。至20世紀(jì)20年代,女子剪發(fā)的熱度較之民國初期甚至顯露出退潮的傾向,“到了近來,非但實(shí)行不見增加,連討論和研究的筆墨都不見了”。女子剪發(fā)未如男子剪發(fā)般形成潮流,時(shí)人將其歸結(jié)為“怯于進(jìn)取舊俗”。具體而言,家庭學(xué)校的阻撓、社會(huì)層面的非議及外國并無女子剪發(fā)先例均可能是讓女子對(duì)剪發(fā)望而卻步的動(dòng)因。然而,剪發(fā)可能減損容顏美觀或許才是女性不愿嘗試“削去青絲”的首要理由。輿論界對(duì)女子“剪發(fā)”的討論往往只停留于其是否有益,恰恰忽視了頭發(fā)長(zhǎng)度及發(fā)型發(fā)式等實(shí)踐層面的問題。換言之,在當(dāng)時(shí)并沒有多少人清楚應(yīng)如何為女子剪發(fā),“初剪發(fā)時(shí),都不知該梳什么發(fā)式好,連理發(fā)店的師傅也很感為難,因從來沒有設(shè)計(jì)過婦女的短發(fā),故只好揀個(gè)現(xiàn)成,按當(dāng)時(shí)最流行的男發(fā)樣式來剪理了”。套用為男子剪發(fā)的成法,成品自然可想而知。
有鑒于此,很難相信20世紀(jì)20年代末期女理發(fā)師的出現(xiàn)是女子剪發(fā)需求旺盛所致。由于男子剪發(fā)更為普及,理發(fā)店管理者雇傭女理發(fā)師,很大程度上與其希望利用女理發(fā)師這一噱頭招徠男性顧客有關(guān)。1918年,上海一理發(fā)店始起用女理發(fā)師,這是迄今為止最早見于近代報(bào)刊的記載:
大新街某理發(fā)店主為擴(kuò)充營業(yè)起見,異想天開,特用中國年輕婦女八人司理發(fā)之職,婦女已于去年冬間練習(xí),至今其剪發(fā)修面而及挖耳拷背等皆與男子無異,各種化妝品應(yīng)有盡有,并有某煙供奉,招待周到……其開幕期約在陰歷八月,初想屆時(shí)一般登徒子定必歡迎,是亦一種別開生面之新營業(yè)也。
1920年,北京一理發(fā)店也聘用女理發(fā)師:
北京孫公園錫金會(huì)館附近春記理發(fā)店內(nèi)近有一少婦在內(nèi)做理發(fā)師,為人理發(fā)。此婦年約十八九,妖冶可鄙。好奇者莫不趨之若鶩,大有門庭如市概云云。
顯然,風(fēng)姿綽約的女理發(fā)師的確對(duì)“好奇者”及“登徒子”有強(qiáng)大的吸引力。女理發(fā)師為男子理發(fā),無形中打破了長(zhǎng)期橫亙于民間的“男女之大防”,男性欣然往之,理發(fā)店的生意也水漲船高。但必須注意的是,男女隔離仍是北洋政府調(diào)適兩性交往規(guī)范的道德準(zhǔn)則。
在作為職業(yè)的女理發(fā)師出現(xiàn)后,坊間開始呼喚專為女子服務(wù)的理發(fā)女技師及理發(fā)場(chǎng)所。有論者直言,女性剪發(fā)難成氣候的最大阻力在于熟練女理發(fā)師的數(shù)量嚴(yán)重不足,“自己剪頭是剪不成了,同性的梳頭媽是不會(huì)的,男性的理發(fā)匠嗎?以中國沒智識(shí)的男性輕蔑女性的惡習(xí)的結(jié)果,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所以就感覺得很是不便,阻礙了剪發(fā)的勇氣。因此我覺得于提倡女子剪發(fā)的時(shí)候,同時(shí)要提倡女性剪發(fā)匠的職業(yè)問題”。同時(shí)亦有人力陳開辦以女子為主要消費(fèi)對(duì)象的理發(fā)館的益處。一批支持剪發(fā)的女學(xué)生乘此東風(fēng),在“女子自決”口號(hào)的鼓舞下開始籌建女理發(fā)館。1922年,長(zhǎng)沙柑子園口吉慶街理發(fā)館正式開業(yè),理發(fā)師皆為女學(xué)生,且技藝相當(dāng)嫻熟,“對(duì)于女子之新式頭簪,如東洋頭、麻花頭、麻姑頭、燕尾巴頭、辮子盤龍頭,形形式式,修飾適宜,手術(shù)精良”。此外,她們亦能為男子剪發(fā),但并不提供為男子捶背、捏腿等服務(wù)。這與由剃頭鋪轉(zhuǎn)設(shè)而成的理發(fā)店劃清了界限,亦清晰地反映理發(fā)店偏重女性剪發(fā)的定位與女權(quán)意識(shí)的初步覺醒。
在利益與社會(huì)訴求的驅(qū)使下,華北地區(qū)的女理發(fā)店亦開始冒頭。北京理發(fā)工人徐省三與其妻子王氏鑒于北京無女子理發(fā)處,申請(qǐng)創(chuàng)設(shè)一處西式理發(fā)館,但卻被警廳以有傷風(fēng)化為由一口回絕,“以該商場(chǎng)系公共游覽處所,若以男子與婦女理發(fā),殊與觀瞻不雅,遂批駁不準(zhǔn)成立”。徐省三的努力無疾而終,此后二三年間,北京城內(nèi)遲遲未有女子理發(fā)店。1925年,女士黨雅蘭遂擬籌資花費(fèi)重金從上海聘請(qǐng)理發(fā)女技師,設(shè)立北京文明女子理發(fā)所。北京女子理發(fā)店開設(shè)舉步維艱,與京津冀及東三省一帶警廳的高壓態(tài)度難脫干系。1926年,直隸保安總司令兼省長(zhǎng)褚玉璞頒布《天津禁止剪發(fā)布告》,明令“凡屬婦女,一律不準(zhǔn)剪發(fā)”以“維持風(fēng)化”;同年,奉天省長(zhǎng)公署亦發(fā)布訓(xùn)令,稱“若不一并從嚴(yán)禁止,實(shí)不足以敦風(fēng)化而正人心”,可見傳統(tǒng)兩性倫理道德的殘余依舊揮之不去。
較之于北京,由于滬上女性多視剪短發(fā)為時(shí)尚,且上海較早受到國民革命波及,置辦女子理發(fā)營業(yè)場(chǎng)所面臨的困難要小得多。孫傳芳盤踞上海時(shí),據(jù)傳上海對(duì)女子剪發(fā)嚴(yán)加管控,“在他的勢(shì)力范圍內(nèi),只要男子是學(xué)生裝或穿西服,女子剪發(fā)者,均視為間諜,隨便拘捕監(jiān)禁槍斃”,其間理發(fā)店只能夾縫求生,慘淡經(jīng)營。1927年初,孫主力土崩瓦解,國民革命軍進(jìn)軍上海及南京,孫傳芳先前針對(duì)女子剪發(fā)頒布的禁令便形同虛設(shè),“革命軍興以來,勃然而起者,厥唯女子剪發(fā)一事。其來也似潮,沛然莫能御”。繼龍泉女子浴室另辟一女子修發(fā)所后,1927年7月16日,上海女青年會(huì)開辦女子理發(fā)所,所內(nèi)理發(fā)師皆為曾接受女青年會(huì)培訓(xùn)的女子。7月27日,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特別委員會(huì)婦女運(yùn)動(dòng)部部長(zhǎng)廖世劭頒布女子剪發(fā)令,女子剪發(fā)潮更一發(fā)不可收。
有論者認(rèn)為,時(shí)人的性別隔離主張是民國女子理發(fā)場(chǎng)所的出發(fā)點(diǎn),未免有將這一現(xiàn)象發(fā)生發(fā)展的前因后果簡(jiǎn)單化之嫌。一樂也、新新、華新等老牌男士理發(fā)店均已在1926年末或1927年開始為女子剪發(fā),“滬上自女子盛倡剪發(fā)后,各大理發(fā)店,如一樂也、萬國、東亞、兩新、升新發(fā)、華洋、華新、成記等,莫不女賓滿座,應(yīng)接不暇”。說明善于捕捉風(fēng)向的投資者無法對(duì)龐大的女性剪發(fā)群體坐視不管。“男女授受不親”的羈絆在利潤(rùn)面前顯得微不足道,暴露了社會(huì)基層與地方政府在處理兩性關(guān)系態(tài)度上的殊異與分層。部分女子亦已卸下心中的堤防,“男女同剪”成為既成事實(shí)。然而,大部分女性仍難以接受到男士理發(fā)師主導(dǎo)的中國理發(fā)店剪發(fā),時(shí)人觀察到,“有許多剪發(fā)女子,他們都上外國理發(fā)店去,我去了幾次,東亞、一樂也等處,沒有碰到一個(gè)女子”。由于長(zhǎng)期的倫理道德規(guī)訓(xùn),傳統(tǒng)女性不得不仰仗于梳頭婆在內(nèi)閉環(huán)境內(nèi)整飭容貌。盡管梳頭婆因現(xiàn)代理發(fā)業(yè)沖擊而走向沒落,但其影響卻很難轉(zhuǎn)瞬即逝。應(yīng)當(dāng)說,專事女子理發(fā)業(yè)務(wù)的理發(fā)店是這一時(shí)期女性消費(fèi)心理所促成的特定消費(fèi)需求的產(chǎn)物,是女性理發(fā)慣性的自然邏輯延伸,與所謂背離“女子剪發(fā)倡議之初的解放內(nèi)涵”無涉。
女光公司始末
1927年末,女光公司在上海宣告成立。在女光之前,滬上尚無系統(tǒng)的女子理發(fā)培訓(xùn)機(jī)構(gòu),女性理發(fā)師資質(zhì)蕪雜,理發(fā)水平難有保證。作為女子理發(fā)培訓(xùn)的先行者,女光公司為近代上海女子理發(fā)業(yè)乃至全國女子剪發(f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女光公司的宗旨在于振興女性就業(yè),“在消極方面說,男子去代女子理發(fā),還不如女子自代女子理發(fā)的適宜。在積極方面說,男子去代女子理發(fā),女子何獨(dú)不可代男子理發(fā)。我們本此宗旨,向前進(jìn)攻,做一個(gè)改革事業(yè)的先導(dǎo)”。為此,女光公司主要經(jīng)營兩項(xiàng)業(yè)務(wù):一是創(chuàng)辦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二是經(jīng)營女子理發(fā)店。頗為值得注意的是,女光公司發(fā)起者均為女界精英,擁有政界背景。各界名流亦鼎力支持女光公司,胡適、劉文島、徐志摩等人皆為女光公司贊助背書。此外,女光公司亦有較為宏偉的擴(kuò)張?jiān)妇埃骸安粏卧谏虾R徊海乙茝V到國內(nèi)各大商埠,使得女子在職業(yè)界中,站一個(gè)相當(dāng)?shù)牡匚弧!?/p>
在女光公司的構(gòu)想中,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與女子理發(fā)店是聯(lián)系緊密的整體。從專科學(xué)校畢業(yè)的女學(xué)生,便將上崗執(zhí)業(yè),成為女光公司女理發(fā)師團(tuán)隊(duì)中的一分子。正因如此,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僅招募20人,人數(shù)相當(dāng)有限。但報(bào)名者的積極性則令女光公司猝不及防,由是不得不增設(shè)學(xué)額10人。為保證教學(xué)品質(zhì),女光公司花費(fèi)重金聘請(qǐng)法國理發(fā)匠授課。或許是出于節(jié)省經(jīng)費(fèi)與急于開業(yè),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具有鮮明的速成特質(zhì),學(xué)生在2個(gè)月內(nèi)便須修習(xí)完理發(fā)術(shù)、衛(wèi)生學(xué)、化裝術(shù)、社會(huì)心理、商店組織管理、商業(yè)簿記、美術(shù)、外國語等課程。12月22日,第一屆學(xué)生畢業(yè)。隨后,女光公司便緊鑼密鼓地籌備理發(fā)店開業(yè)事宜并大肆宣傳,“分送各界贈(zèng)券,歡迎仕女到公司理發(fā),不收費(fèi)用”。
1928年1月1日,女光公司理發(fā)店開業(yè),時(shí)人對(duì)其極盡溢美之詞,稱之為“中國用女子理發(fā)師之開創(chuàng)者”。因理發(fā)價(jià)格優(yōu)惠,不少人在好奇心的驅(qū)使下前往女光公司體驗(yàn),并對(duì)女理發(fā)師們的手藝贊譽(yù)有加:
女剪發(fā)員,一例著白色制服,上繡紅色女光公司中西文名。……為余修建者,其年事二十以內(nèi),手術(shù)至敏妙,殊不弱于男子,惟身材略短,微嫌椅高……甚欽折主人之善選擇,剪發(fā)雖小道,亦必其人性性情溫婉,心思靈巧,成績(jī)斯佳。女光諸人,則都溫婉靈巧……彼即戴一口具,狀如漏斗,人言先施等大理發(fā)所皆有之。
諸多女技師初不因主顧多而草率從事。
以上反饋皆出自男客,當(dāng)中不乏具有凝視與窺探色彩的描寫。令人遺憾的是,從所見史料中,無從得知女性顧客在女光公司理發(fā)時(shí)的真實(shí)感受與女客的占比情況。但可以肯定的是,女光公司生意一派欣欣向榮,“開幕以來,營業(yè)發(fā)達(dá),內(nèi)部設(shè)備精究,女職員藝術(shù)高尚,且招待周到。最近分送學(xué)界優(yōu)待券,照價(jià)八折,故前往修發(fā)者,成爭(zhēng)先恐后云”。
但出人意料的是,女光公司理發(fā)所不到半年便閉店歇業(yè)。對(duì)其短命而亡的原因,時(shí)人概括為以下五點(diǎn):選址偏僻,價(jià)格過高,技術(shù)平常,工資開支過大及同業(yè)競(jìng)爭(zhēng)激烈。這些說法可能不無道理,但至少在“技術(shù)平常”這一條上,未免與其他顧客的評(píng)價(jià)產(chǎn)生抵牾。事實(shí)上,女光公司無法堅(jiān)持營業(yè)的最大原因在于無人主事。1928年春,女光公司發(fā)起人之一鄭毓秀遠(yuǎn)渡法國留學(xué),而廖世劭則因積勞成疾于上海病逝。群龍無首,女光公司理發(fā)所自然無法繼續(xù)勉力支撐。上海女理發(fā)室格局也隨之大變,天香女子理發(fā)社、美容女子理發(fā)館與神仙理發(fā)室呈三足鼎立之勢(shì)。值得玩味的是,三家理發(fā)店都不約而同爭(zhēng)搶“女光出品”的女理發(fā)師,如美容女子理發(fā)館“鑒于女子理發(fā)室技能精巧,特多方設(shè)法聘到女光第一屆及第二屆最優(yōu)等畢業(yè)女技師十二人,特多方設(shè)法聘女光第一屆及第二屆最優(yōu)等畢業(yè)女技師十二人”;神仙理發(fā)室“所有職員,亦俱改用女子,都系女光第一屆之畢業(yè)生,手藝無不純熟”。這無疑從另一個(gè)側(cè)面再次證明:女光公司的解體無法完全歸咎于女性理發(fā)師的職業(yè)素質(zhì)不足。
盡管女光公司未長(zhǎng)成女子理發(fā)業(yè)的常青樹,但它所開創(chuàng)的女子理發(fā)培訓(xùn)事業(yè)卻并未就此止步。女光公司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前兩屆學(xué)生如期畢業(yè)后,教導(dǎo)主任沈叔夏“以是項(xiàng)新事業(yè),有提倡之必要”,自任校長(zhǎng)繼續(xù)開設(shè)上海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每期招生人數(shù)介于十五人至三十人,學(xué)生學(xué)時(shí)通常為三個(gè)月,畢業(yè)后學(xué)校將代為介紹工作,優(yōu)秀畢業(yè)生可赴國華等上海本地大理發(fā)店就職。1929年,沈叔夏更主導(dǎo)創(chuàng)辦具有消費(fèi)合作社性質(zhì)的第一女子理發(fā)社,為學(xué)員提供實(shí)習(xí)機(jī)會(huì)。截至1932年,該校已累計(jì)招募十六屆學(xué)生,畢業(yè)學(xué)生逾三百人。同年,上海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更名為上海女子理發(fā)傳習(xí)所,并免除學(xué)生一切學(xué)費(fèi),“于國難期中,免費(fèi)招生(學(xué)費(fèi)全免),凡失業(yè)婦女有志此項(xiàng)職業(yè)者,盡興乎來”。而后,沈叔夏嘗試在南京新設(shè)女子理發(fā)學(xué)校,但由于授課教師為男性,前來報(bào)名上課者門可羅雀,上海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招生也早已陷入瓶頸,“蕭條冷落,慘淡異常,以視當(dāng)年門庭若市,不勝今昔之戚也”。1935年,上海女子理發(fā)傳習(xí)所停止招生,喧囂多年的女子理發(fā)培訓(xùn)事業(yè)無奈就此沉寂。
概言之,女光公司的發(fā)展歷程是近代女子理發(fā)事業(yè)前進(jìn)軌跡的一個(gè)縮影:女光公司“朝生夕死”,似如近代女理發(fā)師事業(yè)起初轟轟烈烈,隨后卻愈發(fā)停滯不前,漸露敗相;學(xué)校管制與培養(yǎng)使女理發(fā)師進(jìn)一步邁向現(xiàn)代化與職業(yè)化,但女理發(fā)師的擇業(yè)之路卻仍布滿坎坷。除此之外,是何因素推動(dòng)女性投身女理發(fā)師行業(yè)仍不甚明朗。
女理發(fā)師的出身與境遇
蔣美華指出,近代以來,婦女就業(yè)觀念不斷強(qiáng)化,就業(yè)隊(duì)伍不斷擴(kuò)大,就業(yè)領(lǐng)域不斷拓展;但婦女就業(yè)人數(shù)與全國婦女相比只占很小比例,婦女在同行業(yè)中與男子相比微不足道,且就業(yè)婦女受教育程度較低,整體素質(zhì)一般。總體而言,女理發(fā)師亦概莫能外。但其亦有顯著的特殊性:在這個(gè)基數(shù)不大的團(tuán)體中,既有熱心于女子運(yùn)動(dòng)的進(jìn)步人士,也有因生活所迫被迫轉(zhuǎn)行的困窘生民。清代以來,民間多視剪發(fā)為賤業(yè),但為習(xí)得一門剪發(fā)手藝,多數(shù)女理發(fā)師不得不付出高額代價(jià);為謀得穩(wěn)定工作,她們中的某些人甚至需要遠(yuǎn)走他鄉(xiāng)。
在民國報(bào)刊中,絕大多數(shù)以女理發(fā)師為主體的評(píng)論皆出自他者視角,極少見到女理發(fā)師為這份職業(yè)現(xiàn)身說法,而周凌敏恰恰是一個(gè)特例。周凌敏曾任女光公司及神仙理發(fā)室理發(fā)技師,曾多次刊文表白一名女理發(fā)師的心跡。如談到為人理發(fā)的困難時(shí),她坦承她將兩類顧客視為畏途:一是身材魁梧者,“普通理發(fā)的時(shí)間,起碼總要半個(gè)鐘頭,我踮起兩只腳尖,伸高一雙手,在他頭上理發(fā),要這許多辰光,真是吃力非常”;二是外國人,“外國人的胡須,比較上來得多而且硬……恐怕剃開他的面皮”。談到本國理發(fā)師的弊端時(shí),周凌敏則痛心地指出:“外國理發(fā)室的布置注重于清潔簡(jiǎn)單,我國人則偏偏要繁復(fù)華麗,所以新開的理發(fā)室,都要花整千元錢去考究裝潢。這種浪費(fèi),實(shí)在是毫無價(jià)值”。周凌敏能夠抒發(fā)意見縱情褒貶,與其受教育程度和國民黨黨員身份密不可分:
厥后青天白日飛展滬埠,外子參予戎機(jī),余遂注意于黨務(wù)工作,凡有集會(huì),無不列席……同志僉以余熱心工作,因謬舉余為婦女部長(zhǎng)……自問雖無殊績(jī),差可告無罪于吾黨,然因生性率真,不習(xí)慣鉆營阿諛之術(shù),竟受腐化者聯(lián)絡(luò)之攻擊,致遷職于遠(yuǎn)方……即日引退,稍事休養(yǎng)。
適女光公司,以謀女子職業(yè)而招請(qǐng)職員,余遂應(yīng)募而往,迄茲數(shù)月,蒙主事者之優(yōu)待,及外界之謬許,私心竊慰,且較之黨務(wù)工作,尤覺有苦樂之判,從此安心守己,對(duì)于黨務(wù),擬完全脫離。
按:該篇系女工公司女理發(fā)師周凌敏女士所作,女士曾畢業(yè)某女校,學(xué)貫中西,尤工書法……
周凌敏“見了‘職業(yè)無男女’‘職業(yè)無貴賤’的兩句話,毅然決然地去做那人人不屑做的理發(fā)師務(wù)”,無愧于民國女界精英中身體力行者。但周凌敏這樣的婦運(yùn)倡導(dǎo)者在女理發(fā)師群體中畢竟是極少數(shù)。正如前文所述,女學(xué)生是女理發(fā)師的主體,這從女光公司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的招生宣言中可見一斑:“凡高小畢業(yè)或有相當(dāng)程度,而年在十六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皆可考入本公司。”南京女理發(fā)師年齡普遍在十八至三十歲之間,“其程度均在小學(xué)生之上,而常識(shí)之豐富,閱世之老練,舉止之得體,遠(yuǎn)非一般伏處國中之小姐太太所能及”。嚴(yán)苛的年齡和學(xué)歷門檻既維護(hù)了女理發(fā)師的先鋒特質(zhì),也在無形中將一些有志于從業(yè)但年齡稍長(zhǎng)且無文化基礎(chǔ)的婦女拒之門外。
然而,亦有相當(dāng)一部分女理發(fā)師在替人剪發(fā)前從事其他職業(yè),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便是娼妓業(yè)與女子理發(fā)業(yè)的關(guān)系。妓女在近代女子剪發(fā)潮中兼具雙重標(biāo)簽:她們既是剪發(fā)的積極參與者,也是女子理發(fā)事業(yè)的擁護(hù)者。為招徠顧客和吸引眼球,妓女往往剪去長(zhǎng)發(fā),剪短頭發(fā)的女學(xué)生被時(shí)人譏為“妓化”,足見妓女剪發(fā)之流行。而受1928年南京“廢娼運(yùn)動(dòng)”的影響,無錫部分妓女也果斷加入了女理發(fā)師的行業(yè),時(shí)人對(duì)此不無贊許之意,“無業(yè)女子,及廢娼革妓之戚戚謀生者,盍一習(xí)此技,得正適之歸宿耶”。不過,也有聲音質(zhì)疑她們能否常駐,“等到發(fā)業(yè)一落千丈的時(shí)節(jié),理發(fā)師不免感到過剩……那些從娼妓蛻變而來的女發(fā)師,或許就要還原過去,重理她們舊業(yè)呢”。
農(nóng)民同樣是女理發(fā)師人員構(gòu)成中的一部分。20世紀(jì)30年代初“農(nóng)村危機(jī)”的爆發(fā)使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瀕臨崩潰,進(jìn)而引發(fā)較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業(yè)人口離村潮。一批農(nóng)村婦女來到城市后,遂開始學(xué)習(xí)理發(fā)技術(shù)以圖維持生計(jì),“晚近以來,農(nóng)村崩潰,經(jīng)濟(jì)不景,而尤以順德蠶桑女工最受打擊,以此種職業(yè),亦為謀生之一。于是紛起參加學(xué)習(xí),學(xué)生日多,畢業(yè)日眾”。
無論是何種出身,女理發(fā)師在上崗前均需在女子理發(fā)培訓(xùn)機(jī)構(gòu)中接受培訓(xùn),而培訓(xùn)費(fèi)對(duì)她們而言往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以女光公司上海女子理發(fā)傳習(xí)所為例,“入學(xué)時(shí)一次繳納二十元學(xué)費(fèi),書籍用具自備,如需膳宿月繳洋十二元”。與之相對(duì)的是,1929年上海市男工每月平均工資為15.43元,女工則更少。再如廣州女子理發(fā)習(xí)藝社等理發(fā)習(xí)藝所,“征收學(xué)費(fèi)七八十元不等”“所費(fèi)頗巨,約需百元左右”,而1935年廣州火柴業(yè)男工每月工資為15元,女工每月平均工資為9元。各地女理發(fā)師的工資與理發(fā)店當(dāng)月的營業(yè)額和個(gè)人素質(zhì)掛鉤:在廣州,“每人月中所入,無一定數(shù)目;有每月可得七八十元者,五六十元者,三四十元者不等,操理發(fā)職業(yè)女子,間為有夫之婦,亦有未結(jié)婚者,多數(shù)困于家計(jì),出而工作”;在重慶,“她們的手藝,因?yàn)橛懈呦碌牟煌悦吭滤玫膱?bào)酬,亦多寡不一,報(bào)酬高的每月每人能得一百元,報(bào)酬低的則在二三十元上下,學(xué)徒每月仍有三四元至五六元”。可見對(duì)于民國時(shí)期的女性而言,女理發(fā)師的薪酬已殊為可觀。
地域流動(dòng)則是女理發(fā)師求職過程中的常見現(xiàn)象。“廣東幫”是上海女子理發(fā)業(yè)的重要派別,1926年開設(shè)的“美麗閣女子理發(fā)所”內(nèi)20名美發(fā)師、美容師及助工皆為廣東女青年。上海女子專科理發(fā)學(xué)校學(xué)生畢業(yè)后散于全國各地理發(fā)店就職,“統(tǒng)計(jì)本埠二十人,首都十八人,漢口四人,哈爾濱六人,寧波五人,南洋仰光二人,其余武昌、南昌、廣西、廣州、常熟、如皋、南翔、嘉善等處均二人,近大連來校聘請(qǐng)技師十一人,月薪七十元;宜昌二人,月薪六十元。”國內(nèi)跋涉最遠(yuǎn)者至哈爾濱,一度使巡警生疑,學(xué)生許桂英則交代稱:“系上海女子理發(fā)專科學(xué)校學(xué)生,現(xiàn)由李云甫招往哈爾濱理發(fā)館工作,每月薪資五十五元”。更有甚者遠(yuǎn)赴越南、暹羅等國華僑所開理發(fā)店工作。
工作之余,女理發(fā)師亦迫切希望通過其他途徑提升和實(shí)現(xiàn)個(gè)人及社會(huì)價(jià)值。當(dāng)時(shí)的剪發(fā)男性留意到,一些年輕女理發(fā)師下班后并未立刻回家,反而到另處學(xué)習(xí)外語,“她們催促著給我理發(fā)的女郎快些竣事,說大家要去,她們相互的稱呼是用蜜斯黃、蜜斯李。我問替我理發(fā)店女郎,你們忙著到什么地方去呀?她和緩地告訴我,她們每晚九時(shí)以后,要到一個(gè)法國女人家去學(xué)習(xí)法文。”九一八事變后,一些女理發(fā)師們感于國仇家恨,主動(dòng)為東北義勇軍籌款,“實(shí)行節(jié)衣縮食,將每日所積之款,置于撲滿中,作為捐助義軍糧械之需”,從中不難窺見民國女理發(fā)師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與強(qiáng)烈的愛國情懷。
兩性競(jìng)爭(zhēng)中的女子理發(fā)業(yè)
先前已有學(xué)者指出,女理發(fā)師的崛起是梳頭婆逐漸退出歷史舞臺(tái)的一個(gè)誘因。而事實(shí)上,女子理發(fā)業(yè)的野蠻生長(zhǎng),起先亦猛烈沖擊了男子理發(fā)師的生存空間,但隨著男女理發(fā)業(yè)競(jìng)爭(zhēng)的不斷演化,女子理發(fā)業(yè)反倒?jié)u入下風(fēng),甚至有消亡之虞。在上海與廣州兩座口岸城市內(nèi),女子理發(fā)業(yè)的發(fā)展模式幾乎如出一轍,而嶺南男女理發(fā)師之間的直接矛盾,較之江南更為尖銳突出。
江浙女子理發(fā)業(yè)勃發(fā)之際,其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同業(yè)競(jìng)爭(zhēng)的糾葛之中。1927年7月29日,理發(fā)匠金氏因擬開設(shè)女子理發(fā)室,呈請(qǐng)公安局備案。為爭(zhēng)取有司首肯,金氏強(qiáng)調(diào)女子理發(fā)室開設(shè)的必要性:“今當(dāng)省黨部婦女部通令全省婦女一律剪發(fā)之時(shí),上項(xiàng)設(shè)備誠有不可緩者。”公安局的確無意阻攔女子理發(fā)店開張,但當(dāng)?shù)乩戆l(fā)同業(yè)公所對(duì)此卻頗有微詞,指責(zé)金氏的做法破壞了行規(guī):
民等素開理發(fā)店為生,同業(yè)向有公所,由同業(yè)推舉,按年輪值經(jīng)理公所事務(wù),舊有業(yè)規(guī),創(chuàng)設(shè)理發(fā)店,須離老店十間門面以外,方可開設(shè),同業(yè)無不遵守,歷無違背,因此素稱相安。茲有金調(diào)良自崇安寺新新書局內(nèi)創(chuàng)設(shè)女子理發(fā)店……伏查金調(diào)良創(chuàng)店地址東面有美容軒,西面有和源公司理發(fā)店,新新書局介乎期間,與該兩理發(fā)店相距不過四五間門面,殊與舊規(guī)不合,況且同業(yè)中寡孤,藉店生活者甚多,設(shè)或舊規(guī)破壞,勢(shì)必效尤踵起。
因此,警廳不得不收回成命,重又勒令無錫總工會(huì)跟進(jìn)此事。盡管同業(yè)公所提出的訴求合情合理,但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女理發(fā)師并不受其時(shí)由老派男性理發(fā)師掌舵的同業(yè)公會(huì)所庇護(hù),倘若女子理發(fā)師不結(jié)成同盟抱團(tuán)取暖,在實(shí)際工作中難免左支右絀。或許考慮到這一點(diǎn),上海的女子理發(fā)工會(huì)于1928年率先成立。
然而,女子理發(fā)工會(huì)絕非上海女子理發(fā)業(yè)的保命符。在“剪發(fā)潮涌”后的幾年內(nèi),上海女子理發(fā)業(yè)竟悄無聲息地滑向衰亡。1930年,女理發(fā)師仍是人人艷羨的美差,“女理發(fā)師,也成了新職業(yè),超出于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種了”;女理發(fā)館隨處可見,“理發(fā)鋪大有五步一閣,十步一樓之概”。但在四年后的上海,則很難覓得女理發(fā)店的影蹤,“到了現(xiàn)在,上海僅存了一家女子理發(fā)所,其名叫維多利”。南京女理發(fā)館也不好過,“至二十一年,乾坤、萬國、民生相繼停業(yè)。二十二年,東方遷至貢院街,改名姐妹理發(fā)館,今年新民姐妹均停業(yè),于是南京之女子理發(fā)店,碩果僅存者,只南洋與東方兩家矣”。
江浙滬女子理發(fā)業(yè)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要?dú)w結(jié)于無法留住男性顧客。盡管女子理發(fā)店設(shè)立的初衷是解決女子理發(fā)問題,但就周凌敏收集的數(shù)據(jù)而言,女子理發(fā)店的男性客戶仍舊牢牢占據(jù)半壁江山。
而據(jù)時(shí)人觀察,女性理發(fā)店收費(fèi)普遍較男性理發(fā)店高,“女子理發(fā)館之價(jià)目,往往較同等設(shè)備男子理發(fā)館為高,與最上等男子理發(fā)館相同”,但女理發(fā)師的服務(wù)水平卻不能與較高的收費(fèi)標(biāo)準(zhǔn)相匹配,有論者甚至直言“女子理發(fā)的技術(shù)不如男子”。修業(yè)年限的差距決定了彼時(shí)男女理發(fā)師剪發(fā)技藝的差距:男性理發(fā)學(xué)徒往往要三年方得出師,而女學(xué)生們?cè)诮邮苋齻€(gè)月培訓(xùn)后便可從業(yè)。必須承認(rèn)的是,當(dāng)時(shí)步入女理發(fā)館的男性多持嘗鮮獵奇之心態(tài),倘若女理發(fā)師的剪發(fā)手藝不夠過硬,有理發(fā)需求的男子只會(huì)回歸更為質(zhì)優(yōu)價(jià)廉的男子理發(fā)店,男性顧客的流失可想而知。理發(fā)熱潮退去后,由于女性剪發(fā)的頻率遠(yuǎn)不及男性,女子理發(fā)店無法僅依靠女性顧客生存,每每到了冬季,女理發(fā)館的生意只能仰仗于已與店內(nèi)某一女理發(fā)師建立友誼的“老主顧”,而他們本身“醉翁之意不在酒”。這既是因女子理發(fā)業(yè)快速發(fā)展所遺留的結(jié)構(gòu)性痼疾,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此外,20世紀(jì)20年代的農(nóng)村危機(jī)也是壓垮滬寧女子理發(fā)業(yè)的重要因素。“農(nóng)村破產(chǎn)”的破壞力遠(yuǎn)超鄉(xiāng)村一隅,富庶城市也難逃其輻射,“東南財(cái)富之區(qū),現(xiàn)在亦已凋敝不堪。試看上海電報(bào)所述廢歷年關(guān)上海和其附近內(nèi)地歇業(yè)者至多,可見一斑,南方如此,北方更不待論”。在極不景氣的工商業(yè)環(huán)境下,女子理發(fā)業(yè)很難獨(dú)善其身。
較之于上海,20世紀(jì)30年代廣東地區(qū)男女理發(fā)業(yè)的爭(zhēng)斗更為刺刀見紅,雙方爭(zhēng)執(zhí)的焦點(diǎn)在于理發(fā)工會(huì)問題。在潮汕,盡管女子理發(fā)風(fēng)靡,但當(dāng)?shù)乩戆l(fā)工會(huì)卻拒絕接受女理發(fā)師入會(huì),由是導(dǎo)致女理發(fā)館無法為男子剪發(fā);在佛山,情況則翻轉(zhuǎn)過來:為統(tǒng)一營業(yè)規(guī)章,三水理發(fā)工會(huì)勒令全市理發(fā)女工必須加入工會(huì),否則強(qiáng)制剝奪女理發(fā)師工作權(quán),但各“發(fā)花”則堅(jiān)決反對(duì)加入男性所把持的理發(fā)工會(huì),雙方始終僵持不下。而在廣州,女理發(fā)師則是起初相對(duì)強(qiáng)勢(shì)的一方。1933年,廣州理發(fā)工會(huì)向市政府“大吐苦水”,稱女理發(fā)師數(shù)量激增將放大失業(yè)問題,致使男理發(fā)師丟失經(jīng)濟(jì)來源,因而應(yīng)當(dāng)取締女子理發(fā)訓(xùn)練所。這近乎無理取鬧的要求自然被廣州女理發(fā)師猛烈抨擊。而后,因廣州女子理發(fā)店?duì)I業(yè)時(shí)間較長(zhǎng),廣州理發(fā)工會(huì)恐生意被女理發(fā)師盡數(shù)掠奪,請(qǐng)求女理發(fā)師加入工會(huì)協(xié)調(diào)營業(yè)時(shí)間及營業(yè)價(jià)目,又遭以杜秉珊為代表的女子理發(fā)業(yè)魁首一口回絕。1935年,廣州茶樓男女工人發(fā)生沖突時(shí),女理發(fā)師陣營領(lǐng)袖迅速與女招待方面達(dá)成同盟,雙方“聯(lián)成一氣”以捍衛(wèi)女子職業(yè)。直至“新生活運(yùn)動(dòng)”之風(fēng)刮遍廣州,男女理發(fā)工人之爭(zhēng)才漸次消弭。廣州市新生活運(yùn)動(dòng)促進(jìn)會(huì)代表原打算勸誡女理發(fā)館和男理發(fā)館在工作時(shí)間上保持一致,但在女理發(fā)師的據(jù)理力爭(zhēng)下,市“新運(yùn)會(huì)”最終亦同意女理發(fā)館夜間九點(diǎn)閉店。從這個(gè)角度出發(fā),廣州女子理發(fā)師似已取得了斗爭(zhēng)的完全勝利,但榮光背后實(shí)則暗流涌動(dòng)。就理發(fā)技能而言,廣州女理發(fā)師與男技師相形見絀,這使得廣州女子理發(fā)店面臨著與上海女子理發(fā)業(yè)相似的窘境:就理發(fā)門店而言,女子理發(fā)店數(shù)量因經(jīng)濟(jì)大蕭條日益萎縮,但女子理發(fā)培訓(xùn)方興未艾,這導(dǎo)致女理發(fā)師遠(yuǎn)遠(yuǎn)供大于求。失業(yè)的廣州女理發(fā)工人最多時(shí)逾2000人,迫使杜秉珊帶隊(duì)出省為女理發(fā)師謀職,但這樣的舉措顯然無異于杯水車薪。
由于男子長(zhǎng)期壟斷大量職業(yè),近代女子“走出家門”后,男女職業(yè)工人因就業(yè)機(jī)會(huì)、就業(yè)環(huán)境和就業(yè)待遇產(chǎn)生齟齬并不罕見。倘若暫且不論國內(nèi)國際經(jīng)濟(jì)形勢(shì)動(dòng)蕩的影響,從表面上看,女子理發(fā)業(yè)在20世紀(jì)20年代中期遇挫是女子理發(fā)業(yè)在兩性交鋒中失敗的結(jié)果,但從本質(zhì)上講,擊倒女子理發(fā)業(yè)的是女子理發(fā)業(yè)的自身積弊,而非男子理發(fā)業(yè)的打壓。后者所做的僅是進(jìn)一步曝光這些問題。女子解放的社會(huì)輿論與急功近利的社會(huì)心理裹挾著女子理發(fā)培訓(xùn)事業(yè),使其朝著速成化快餐式的培養(yǎng)方向一往無前,女理發(fā)師難以真正掌握理發(fā)技能;而民國男女理發(fā)業(yè)的激烈競(jìng)爭(zhēng)固化了雙方畛域之見,摧毀了健康的行業(yè)生態(tài),也因此葬送了女子理發(fā)師通過相互交流提升剪發(fā)本領(lǐng)的契機(jī)。作為一項(xiàng)新生事物,女子理發(fā)業(yè)的演進(jìn)趨勢(shì)在相隔千里的兩座城市內(nèi)呈現(xiàn)著相類的面貌,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國女子職業(yè)初創(chuàng)的艱辛與不易。
余 論
作為新興職業(yè)的女理發(fā)師拓寬了近代婦女的就業(yè)渠道,其主導(dǎo)的女子理發(fā)業(yè)是民國女性追求職業(yè)平等的重要平臺(tái)。大體而言,女子理發(fā)業(yè)的普及呈現(xiàn)出先南后北的態(tài)勢(shì)。縱然各地女子理發(fā)業(yè)的發(fā)展階段參差不齊,但無不與盤扎當(dāng)?shù)氐哪凶永戆l(fā)工會(huì)爆發(fā)沖突,且多為高開低走,令人扼腕。一個(gè)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是,20世紀(jì)20年代普通女子礙于“男女有別”的世俗目光,更傾向于到女子理發(fā)店剪發(fā);在20世紀(jì)40年代前后,女子卻更愿意到男子理發(fā)店而非女子理發(fā)店理發(fā)。消費(fèi)觀的理性化與性意識(shí)的開放化何者左右了女性的理發(fā)選擇,尤為值得探究。此外,由于部分地痞無賴常到女理發(fā)館尋釁滋事,女子理發(fā)室成為近代城市治安的新痛點(diǎn),“女子理發(fā)館一多,公安局的事務(wù),也跟著加多”。女理發(fā)館等女性營業(yè)商鋪與警政的交互關(guān)系兼及處理新型女子職業(yè)相關(guān)問題時(shí)治安條例與實(shí)際管理之間的張力,或是日后社會(huì)史領(lǐng)域可供挖潛的方向。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