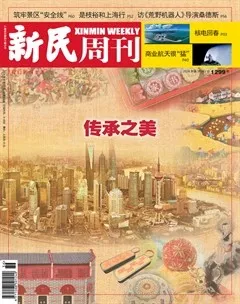“同學”難求

導演
戲劇、寫作、電影
有沒有一個別人的名字,常常與你的名字放在一起,被視為形影不離的?你有期待人生中會收到這樣的禮物嗎?一個上課會相見,下課會想起,于是很開心第二天又可以見到的——同學?
由上述聯想而起,便是為什么要在大學里說“梁祝”。那天中午,我走在港大的校園里,正值午餐時候,放眼之處,都是人頭簇擁。我想起疫情期間在這里拍攝的“一人有一個課室”系列,因而想到其中一位同學所分享的體驗:上了大學三年,沒曾遇上深交的同學。一個人去,一個人回,日復一日,有時候連出門的動力都缺乏。這樣的心情,用今日的詞匯,除了宅,不知道算不算也是一種I人?
雖然事隔好多好多年,但那位同學的狀況我也曾經歷過。那時我還在念初中,被送到外地住讀學習獨立生活,但當一個學期結束,我已回到了香港。家人給我找了一家可以插班的學校,第一天上完課后,我的感覺就是,第二天還要來嗎?那個當插班生要面對的恐懼,用今日的詞匯,不知道算不算就是“社恐”?第二天,我背上書包,上了巴士,但在學校附近找了家茶餐廳,買了幾份報紙,邊吃早餐邊在上面看見附近一家戲院的早場片目。然后去看了一場十點半,接著是十二點半,才像放學那樣,背著書包回了家。并在當晚跟自己說,明天,明天我會恢復正常的學生生活。但是,明天成了逃避明天的借口,“上課”就這樣“日復一日,一個人去,一個人回”,直至整個學期過去,我都沒有回過那家學校。
所以,當我聽到也是出了門卻沒有動力進入教室的那位同學的心境,不期然地,會產生浮想,如果當年的我在上學的路上遇上在上學路上的他,我們又能結得上伴,我們會因此而不被“社恐”影響,找回上學的動力嗎?
“同學”對我來說,到底仍像夢寐以求的人生禮物,只是求之不得。
從小我便沒什么同學緣。我的興趣,不是他們的興趣,我想討論的事情,與他們有距離。因為,很早開始,我已從電視獲得大量未經消化的信息,話題如果是交流的起點,他們更多是校園內,我卻是校園外。這種差異在后來被媒體文化的壯大所消弭,然而在我還是初中學生的年代,我的“同學”因而也難以在校園與教室中找到。當新學期開始,終于由街頭學校(電影院)回歸正式校園的我,還是很快便又投入了另一所學校: 先是出版青年人刊物的媒體,然后就是電視臺。在這兩個地方,我的“同學”全比我年長八到十歲,例如甘國亮,例如鄭丹瑞。為什么經驗與資歷都比我豐富的他們不是“老師”是“同學”?我覺得那跟大家正在為一個新興媒體努力有關,也就相濡以沫。
但再活躍于電視臺,現實中我仍是學生。“同學”對我來說,到底仍像夢寐以求的人生禮物,只是求之不得。就在那個時候,偶然撿到邵氏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的電影原聲卡帶,一聽之下,它把我十四年人生最重要的兩種情懷串聯起來:一是在外地住讀時,初三班的我被放在高三生的宿舍里遇過的“同學”,二是同學又叫“同窗”,這扇通往我所向往的天地的“窗”,在哪里?就是這樣,我開始了往后幾十年的這段“梁祝之旅”,以致由一個聽故事的人,變成說故事的人,故事名叫《梁祝的繼承者們》。
繼而想到,隨著人際關系疏離,個人內心脆弱,一切講求成本效益,害怕被拒絕和失敗而缺乏溝通欲望。加上AI 的普及化,在這樣的時代里,同學已在“被消失”之中。AI與人作為同學的差異在于,后者的交流(可以)建立在不同的性格、背景、經歷之上,在彼此相處的過程中,有助互相學習,而不只是一個“功課/社交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