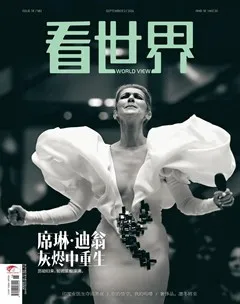奧運團結不了法國

留給馬克龍的時間不多了。
奧運五環旗由美國演員湯姆·克魯斯飛身取走,掛在洛杉磯閃閃發光的“好萊塢”山頭。
為期17天的2024巴黎奧運會,給爭吵不休的法國帶來一個奇跡時刻:觀念分歧、派別林立的法國人涌進賽場,為運動健將吶喊助威,一時間忘了日常與政治上的撕裂和紛爭。
奇跡時刻相隔太久,上一次還是在1998法國世界杯。“完美中鋒”齊達內獨中兩元,帶領法國足球隊大勝巴西。巴黎郊區法蘭西體育場見證他們首次拿下世界杯冠軍。成千上萬的人群涌進香榭麗舍大道和人權廣場,與兩天后法國國慶的狂歡隊伍交織在一起。
巴黎奧運成功舉辦,也讓焦頭爛額的法國總統馬克龍喘了一口氣。6月9日,極右翼黨團在歐洲議會選舉獲得壓倒性的選票。領導中間派的馬克龍,不得不以“自殘式”手段解散國民議會,提前舉行新一屆議會選舉。

馬克龍將于2027年卸任,而老對手瑪麗娜·勒龐的氣勢如日中天。歐盟和法國的權力結構、政治生態大受沖擊,有政治學家判斷馬克龍的政途—“房子將在3年內燒毀”。
馬克龍押下重注—趁著奧運會即將開幕,不如現在就把房子燒掉,看看事情會怎樣。但事實證明,奧運這出緩兵之計并沒有起到效果。左右翼再度對“猶豫不決”的馬克龍發起猛烈攻擊。
隨著奧運閉幕,短時間和解的政壇,重新分崩離析。
奇跡時刻難再現
巴黎奧運會開幕以來,所有不吉利的預言全都落了空,比如交通擁堵、恐怖主義襲擊以及混亂不堪的政治氣氛。此前歐洲議會選舉和法國國民議會選舉呈現的割裂,令人恍如隔世。
巴黎是一座有自己情緒的城市,孤獨,憂郁,悶悶不樂。就像法籍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用電影《藍》影射“自由”—必須服從自然法則、同時作為有限理性存在的個人,飽受實然與應然的落差和拉扯。
開幕式體現出的開放性和多元價值觀,促成了法國社會的暫時性“和解”。
在今天的法國,這一問題有其現實形式:個人要為普世價值犧牲多大的自由?何種政治制度才能保障自由?雖然“極右翼”似乎“面目猙獰”,但不斷增長的選票,顯示了他們對民眾“自由”困境的有力回應。
“文化性條件反射”下,悲觀的法國人本來對奧運會興趣不大,還有民調機構預測巴黎市民大規模“出逃”,以躲避奧運的擁堵和喧囂。比賽開始后,巴黎的氣氛卻好得“難以置信”。連一開始無比絕望的巴黎奧運會組委會主席埃斯坦蓋都如釋重負,聲稱“奇跡時刻”到來。
盡管開幕式有關法國大革命和“最后的晚餐”的場景引發爭議,但開幕式體現出的開放性和多元價值觀,促成了法國社會的暫時性“和解”。
貼在所有法國市政廳的銘言“自由、平等、博愛”,特別是最難理解的“博愛”,忽然降臨大地,讓被右翼和極右翼占為己有的“愛國主義”,重新回到每個人身上。
“紅白藍”交匯的奇跡時刻,上一次發生在26年前。1998年7月12日,中鋒齊達內獨進兩球,法國足球隊三比零獲得世界杯冠軍,在家門口把“三冠王”巴西隊踢得落花流水,順便也為兩日后的“巴士底日”國慶獻上大禮。
1998年6月,歐洲中央銀行剛剛運作,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也在世界杯決賽看臺上為法國隊搖旗吶喊。那時,法國正試圖以歐洲一體化推動國內結構性改革。
奇跡時刻被瑪麗娜·勒龐的父親讓-瑪麗·勒龐打斷。2002年法國總統選舉,讓-瑪麗·勒龐在首輪選舉中擊敗呼聲頗高的時任法國總理、左派社會黨人若斯潘,人氣急升。
讓-瑪麗·勒龐于1972年建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一度以“泡沫政黨”形式存在。1984年,“國民陣線”打出“法國人的法國”口號,在歐洲議會選舉拿到11%選票,存在感大增。
2011年,讓-瑪麗·勒龐將黨魁之位“傳”給小女兒瑪麗娜·勒龐。2015年,因其堅持帶新納粹色彩的反猶主義,被女兒開除黨籍。瑪麗娜·勒龐改造了“排斥移民”和“小政府”的政黨策略,以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建設法國特色福利國家、退出歐元區為主張,吸引了社會弱勢群體和不滿歐洲一體化的階層。

讓-瑪麗·勒龐五度參與總統選舉,也多次因為首輪得票排名較高,在第二輪投票時受到左右翼和中間派的聯合阻擊。
過去之事,今必再行。
今年7月,馬克龍“權宜性”與左翼聯盟合作,同樣要把瑪麗娜·勒龐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拉下馬”—哪怕自己領導的中間派執政聯盟“在一起”敗選也在所不惜。
巴黎燒了嗎
6月9日,歐洲議會選舉結束。極右翼黨團勢如破竹,歐洲政治光譜“向右轉”已成既定事實。其中,法國極右翼政黨最具代表性,“國民陣線”已改名為“國民聯盟”,獲得超31.7%的選票,票數是馬克龍領導的執政黨“復興黨”的兩倍。
瑪麗娜·勒龐放言“組閣”。她的門徒,28歲“國民聯盟”黨魁巴爾德拉,勝選演講已經帶上了“總理口吻”。
當天夜里,依據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第12條賦予總統的權力,馬克龍宣布解散國民議會,提前三年舉行新一屆議會選舉。
然而,沒和總理、議長商量,馬克龍就搶先一步“燒掉房子”,“復興黨”黨內大嘩。中間派執政聯盟“在一起”為表達對馬克龍的冒失不滿,連競選海報都不印他的頭像。
馬克龍出手豪賭,并非利令智昏。
極右翼勢力借歐洲議會選舉崛起,必然沖擊歐盟和法國國內的權力結構和政治生態。于外,這將影響歐洲議會的力量分配,從而改變歐盟的政策和議案。于內,極右翼劍指2027大選,中間派恐難“咸魚翻身”。
好比歐洲冠軍杯和法國足球甲級聯賽關系不是特別大,理論上,歐洲議會選舉的結果并不能動搖馬克龍的總統之位,只是給他后三年的施政帶來更多壓力。
馬克龍想利用這一契機,以迅速回應的姿態,達到“增加同盟”的結果。
按歷史經驗,馬克龍足以靠法國國民臨陣倒戈的“傳統藝能”,洗牌國民議會,并爭取支持自己的中間派陣營拿到多數席位。
此次國民議會重選,假如拿到多數席位,馬克龍在后續三年任期里就可以大刀闊斧推行司法改革、親歐主義等議程。即使沒拿到多數席位,也能打擊“國民聯盟”的氣焰;但也可能拱手讓出多席位的相對優勢地位。
最終,經過兩輪選舉,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憑182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馬克龍領導的中間派執政聯盟“在一起”以163席居第二位;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以143席,列第三位。
面對這一結果,馬克龍承認“敗選”,表示“尊重法國人民的選擇”,但這份“尊重”卻沒有行動的證明。
馬克龍始終選不出理想的溫和派總理,2個月來,新總理人選懸而未決,如今奧運結束,左右兩派的攻擊,鋪天蓋地而來。

2個月來,新總理人選懸而未決,如今奧運結束,左右兩派的攻擊,鋪天蓋地而來。
極右翼“國民聯盟”稱將要對政府發起不信任動議,極左翼“不屈的法蘭西” 稱要啟動彈劾程序。
奧運奇跡時刻曇花一現,政壇撕裂重歸一地雞毛。這個問題,反映出更深層的矛盾:如今的法國,究竟是誰的法國?
誰的法國?
歐洲議會選舉之前,馬克龍已經灰頭土臉。
一,2022年以法律形式強推退休制度改革。法條“到2030年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推遲至64歲”和“2027年時只有繳納43年養老保險的人才能領取退休金”,引發國內震蕩。以“革命老區人”自居的法國人,當場拿出“抗議、示威、罷工”三件套。
二,2023年末頒布新移民法案,提高了外籍人士獲取法國國籍的門檻,嚴格規定了未來三年引入的移民人數。左翼人士痛心疾首,右翼政黨歡欣鼓舞。
三,原定于7月1日發布失業保險改革法令,縮短失業者領取救濟金的時間,領取條件為兩年內有過工作。由于6月30日國民議會首輪投票時,“國民聯盟”大幅度領先,時任總理阿塔爾火速叫停該法令,“穩住”選民。
要知道,中間派馬克龍推動的“前進運動”,不是延長職工工作時間、推遲退休年齡,就是限制工會權力。相比之下,瑪麗娜·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競選綱領是“反對推遲退休年齡”“增加公共福利”等—乍一看似乎比馬克龍“左”多了。
時至今日,以左、右或者極左、極右的標簽去認識法國政黨政治,已經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
其實,早在2004年法國國民議會選舉時,“國民陣線”就呈現出“左翼勒龐”現象—貧窮落后地區、曾經擁護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而如今對社會心懷不滿的男性,大量聚集到讓-瑪麗·勒龐麾下。
如果要區分馬克龍和瑪麗娜·勒龐的傾向,只有一個更為核心的標準:誰的法國。

瑪麗娜·勒龐和巴爾德拉演講,總是站在“紅白藍”法國國旗下。而藍底金星的歐盟旗幟,懸掛在法國每個市政廳和政府辦公室,包括總理官邸馬提翁府和總統府愛麗舍宮—構成馬克龍出鏡最常見的背景。
法國人的法國,還是歐洲人的法國,是每個法國人不得不承受的拷問。
在法籍俄羅斯哲學家科耶夫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法國必須要放棄“一個帝國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目標。《法國國是綱要》實際上為法國指出“新拉丁帝國”的目標,描繪了歐共體和歐盟的最初藍本。
冷戰結束后,法國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一是要確保法國的歐洲主導權,防止德國“卷土重來”;二是發展經濟,推行與多個鄰國互相協調、擴大市場規模的政策,創建一個“為法國準備的歐洲”。
然而,歐盟不斷東擴,眾口難調,法國的主導權不斷稀釋,本來就對東歐有較大影響力的德國,發言權不斷提高。
再也沒有“為法國準備的歐洲”了,反而是法國淹沒在歐洲之中。
今年3月,馬克龍針對烏克蘭危機發言,“派兵論”語驚四座。他有意以戴高樂“戰略自主”理念繼承人的身份,展現法國在歐洲的領導權。
而瑪麗娜·勒龐也打著戴高樂的自由獨立大旗,反復質疑歐盟。
一方面,她指責德國領導歐盟,歐元是德國“定制”貨幣,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慷他人之慨—接收100萬移民,挑剩下的再給別國。一方面,她也對法國當政者不滿,后者看德國、美國的臉色,“不記得法國還有(自己的)工商業利益”。
無論執政或在野,雙方共同訴諸“戴高樂主義”,像一種黑色幽默。對于政治家而言,無非達則歐盟,窮則法國。難就難在執政黨沒法承認自己“窮”。
法國的命運正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藍》:創作“歐共體之歌”的作曲家意外去世,此曲已絕,他的妻子也心灰棄世。偶然間,妻子發現丈夫早已背叛家庭,由此釋下重負,續寫歌曲,重啟人生。
正視歷史的千瘡百孔,才有機會譜寫靈魂真正的自由。
巴黎奧運會的成功,不會改變法國政治局勢,對于麻煩纏身的馬克龍來說,這不過是多了一點喘口氣的時間。
責任編輯 何承波 hcb@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