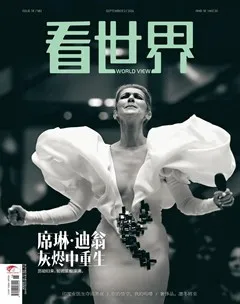男人消失?肯尼亞遍地單親媽媽

“孩子還很小的時候,有一天,男人消失了。”
薇拉是一名30歲的單親媽媽,獨自帶著6歲的兒子杰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貧民窟里生活。多年來,孩子的父親不知所蹤,來自異鄉的薇拉只能靠接洗衣服的零活以及到處借錢,方能勉強養活自己和兒子。
肯尼亞是整個非洲大陸上單親媽媽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2013年,由兩位加拿大社會學家開展的實證研究顯示,大約有60%的肯尼亞女性在45歲之前可能成為單親媽媽。
在這個經濟發展迅猛的東非國家,像薇拉這樣的單親媽媽數不勝數。從社會底層的貧民窟女性到精英階層的白領、金領女性,從二三十歲的年輕女性到已經當外婆的老年女性,單親媽媽以各種樣貌密集地存在于肯尼亞社會之中,甚至因為人數眾多已然成為一個當地人習以為常的群體。
未婚生育
“你和一個男性交往了兩個月,然后你懷孕了。可是兩個月并不足以充分認識這個人。后來你們分手了,你就成為單親媽媽了。”一位內羅畢的年輕藝術家麗茲說。肯尼亞是未婚生育比例最高的非洲國家,大約有30%的肯尼亞女性在未婚狀態下生育了孩子。
和很多現代都市一樣,在內羅畢等地,越來越多情侶選擇同居,而非正式的婚姻。社會價值觀上對性與婚姻剝離的包容、婚姻的高昂經濟門檻、個體對婚姻制度的抗拒等因素,使得同居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實際選擇。
同居在當地還有一個耳熟能詳的俗稱—“來,我們住在一起(Come-we-stay)”。根據2018年肯尼亞人口健康研究中心與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等機構合作開展的一項調研,在25—34歲已建立親密關系的肯尼亞成年人中,高達87%的男性和72%的女性處于同居關系中,而只有8%的男性和19%的女性處于婚姻關系中。
廣泛的同居,加上避孕措施不到位,以及經濟狀況不穩定等因素,使得年輕女性未婚生育的狀況也變得普遍,可是男方卻得以輕松擺脫父職的“束縛”。一位單親媽媽瑪麗表示:“有些男人告訴你,在你們結婚前必須先和他們生一個孩子。(但是)如果你生了,他們就逃跑了。”而不少女性生孩子是希望男方同意結婚,可現實常常事與愿違。雖然,懷孕的確促使了一些情侶走向婚姻,但仍有大量非正式親密關系以失敗告終,女方由此成為單親媽媽。除了感情破裂等個人因素外,當地高額的彩禮也使得即使一些男性想和懷孕的伴侶結婚,卻依舊被婚姻拒之門外。
在所有未婚生育的女性中,最弱勢的當屬未成年媽媽。2022年肯尼亞家庭人口調查顯示,在15—19歲的肯尼亞女性中,有15%已經懷孕或生育,該比例在貧困社區則更高。溫迪是肯尼亞社會正義組織的一名社工,專門負責未成年媽媽群體的幫扶工作。據她介紹,當地未成年女孩早孕的成因有很多,包括性侵犯、早婚以及貧窮等因素。舉一個令人心碎的具體情況,在內羅畢的貧民窟里,一些女孩子僅僅因為買不起衛生巾而和男人睡覺。

在15—19歲的肯尼亞女性中,有15%已經懷孕或生育。
除了上述情況外,還有少數肯尼亞女性因社會壓力而陷入自己并不真正想要的懷孕之中。同中國一樣,肯尼亞女性也面臨著“最佳生育年齡”的壓力。20多歲是女性最具“生產力”的時期,且生育并發癥的風險較低。此外,一些肯尼亞年輕女性還面臨著周遭環境對其生育能力質疑的壓力。
肯尼亞單親媽媽協會創始人安吉麗娜說:“有些人說這是同輩壓力的結果。當所有同齡人都有了孩子,人們開始指責她們不孕不育……所以她們會去誘騙一個男人,只為了懷孕并證明她們是有生育能力的。”
“男人消失了”
除了未婚生育外,肯尼亞已婚女性因婚姻破裂而成為單親媽媽的情況也數不勝數。正如本文開頭薇拉的情況,“男人消失”是最常聽見的無奈解釋。
奈奧米是一位年近半百、身材圓潤的女性,生性開朗的她總是能為生活中的一點小事樂得哈哈大笑。她也是一位單親媽媽,靠著給有錢人家當幫傭,獨自拉扯三個女兒長大。20年前,丈夫不辭而別,她說:“男人跟別的女人過了,就不管自己的孩子了。”

Facebook上可以看到不少女性自豪地標記自己為“母親”而非“妻子”。
實際上,在傳統的肯尼亞社會,父親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可是當今的肯尼亞男性似乎越來越無心或無力承擔父職。內羅畢大學的社會學家肯·奧科博士表示,雖然實際情況頗為復雜,但大量單親媽媽的出現仍應主要歸咎于不負責任的男性。他說:“女性常常因為不負責任的男性而陷入婚前懷孕的困境,但這些男性不愿承擔責任,他們總是消失不見。也有的男性結了婚,卻在孩子出生后不知怎的就收拾行李離開了。”
在眾多的單親媽媽中,也不乏主動離開男人、選擇獨自養育孩子的正能量案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克拉克在研究中便發現,一些肯尼亞女性因為丈夫飲酒過多、未能提供經濟支持或對她或他們的孩子施暴而勇敢地將丈夫趕出家門。
肯尼亞基貝拉貧民窟某公益組織創始人、時年81歲的單親媽媽特里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與其在婚姻中當奴隸,不如選擇自由。”這是她一直對身邊女性說的一句話。
半個多世紀前,已經是四個孩子母親的特里毅然選擇和不負責任的丈夫離婚。之后,她獨自將孩子們撫養成人,每個孩子都上了大學。當然,特里也是幸運的。從偏遠小村莊到城里上大學,從自己擺脫糟糕的婚姻到成立公益組織支持更多單親媽媽,她始終獨立、堅強、勇敢。同時,她也獲得了許多社會資源的支持和幫助,方能一步步走向更自由遼闊的人生。
在女性主義日益增強的當下,也有越來越多的肯尼亞女性積極擁抱單親媽媽的身份。Facebook上可以看到不少女性自豪地標記自己為“母親”而非“妻子”。一些女性在Facebook上時常發布自己孩子的照片,而個人資料里仍顯示為“單身”。
同時,一些女性主義者也呼吁反對污名化單親家庭,因為有些雙親家庭的孩子比單親家庭的孩子過得還要糟糕。一位肯尼亞單親媽媽互助社群的頁面上寫著:“一個有毒的父親對孩子的傷害,比一個缺席的父親更大。”

在夾縫中互助
雖然像特里這樣將四個孩子培養成才的故事非常勵志,但在一個仍為傳統父權制的社會里,肯尼亞單親媽媽的日常境遇還是充滿各種挑戰的。
文首提到的單親媽媽薇拉便總是面臨著各種壓力和煩惱。下半年兒子杰就要上小學了,薇拉正發愁學費要從哪里來,畢竟自己洗一整天衣服的收入(250先令,約合人民幣約14元)還不到孩子一學期學費的1/10。除了經濟困頓外,一個女人獨自帶著孩子在貧民窟生活,還不得不面對切身的安全風險。薇拉租的鐵皮屋緊貼在貧民窟的主路邊上,晚上有好多流浪漢在門口晃蕩,她總是擔心有人會破門而入。
通過多年的追蹤調查,加拿大社會學家克拉克副教授指出:“肯尼亞單親母親往往在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我們發現單親母親與更嚴重的貧困密切相關。就算一些單親母親幸運地找到了有薪工作,她們也很難找到可靠的育兒幫助。”
對于生活和工作上的重重困難,單親媽媽們也在自己的社會網絡中積極尋求幫助,她們最常求助的對象是自己的女性親屬和鄰居。
奈奧米的二女兒也是一位單親媽媽,育有兩個學齡前的女兒。身為外婆的奈奧米主動扛起了養育兩個外孫女的責任,以便二女兒可以在中東安心地工作賺錢。奈奧米出去幫傭賺錢時,她便將兩個外孫女托付給村里的一位修女照顧,她會支付一些工資。
此外,當地還有一些單親媽媽和自己的姐妹互助養育孩子的案例。安妮和安格是一對漂亮的雙胞胎姐妹,兩人都為單親媽媽,都育有一兒一女。姐妹倆在內羅畢的貧民窟里合租了一間鐵皮屋,六人同住。有了妹妹安格在家照顧孩子、打理家務,姐姐安妮得以找到一份在市區酒店里做清潔的穩定工作,月收入能覆蓋六個人的日常開支和孩子們的學費。
除了個體間的互助之外,肯尼亞政府和社會各界也給予了單親媽媽群體一些具體的幫助。肯尼亞單親媽媽協會提供的支持性服務包羅萬象,包括孩子托育、職業技能培訓、小額貸款、家庭咨詢、法律援助等各個方面。
社會正義組織的溫迪自己也是一名單親媽媽,在六年前伴侶意外過世后,陷入抑郁的她被邀請加入了該組織的單親媽媽互助小組。與相似境遇的女性們相互交流、彼此支持的過程給了她極大的療愈力量。在小組里,她也學到了很多知識,使得她日后有能力成為該組織的一名社工。
特約編輯 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