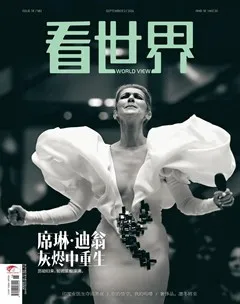花魁與女衒:“吉原”浮世夢一場

鄰近東京地鐵日比谷線的三之輪站,有座名為“凈閑”的寺院,明治時期的著名詩人、小說家永井荷風的文學碑與筆冢便坐落其中。
永井荷風是日本文壇新浪漫派開創者,他感傷當時社會對西方文明的一味模仿與傳統文化的末路,因而醉心江戶文化的浪漫情懷,更熱愛充滿庶民人情的下町文化,認定疲敝墮落的平民生活都有其美感。因此,永井荷風的作品多充滿江戶韻味、描寫花街柳巷生活。
文學碑安置在寺院墓地的一隅,也算適得其所。畢竟此地鄰近吉原游廓,是江戶時期公家牌照的妓院聚集地,紅男綠女外,更吸引許多文人雅士創作出諸多藝文作品。各種俳句、狂歌、聲曲、歌舞伎、浮世繪也以此為主題,是江戶文化重要發祥地。而這凈閑寺,也一點沒與“凈閑”倆字沾邊。
這座僧寺,因作為病死妓女的“投入寺”而聞名。傳說在妓女孤苦病死后,會被剝去衣服,并用破草席包裹扔進寺中,再冠以“某某賣女”的戒名埋葬。據聞在江戶時期吉原的380年歷史中,共有2萬余名妓女埋葬于此。
對吉原的誤讀
一般人談起吉原游廓,會先想起艷冠群芳的花魁,腦海里會出現蜷川實花導演、土屋安娜主演的電影作品《惡女花魁》(2006)。
此外,在安達佑實演出的《花宵道中》(2014)中,即便主題有關身不由己的命運、殘酷的現實,然而影像所呈現的,更著重在各種絢麗奇美的畫面,故事描繪的多是虛假風月場中難以尋覓的有情人與真感情,甚至為此放棄成為武士夫人的翻身機會,滿是幻想與意淫。
但實際上,真正吉原女人的故事,更貼近由樋口一葉原著改編、今井正執導的電影《濁流》(1953)、熊井啟的《大海作證》(2002)、五社英雄的《吉原炎上》(1987)。妓院是男人尋歡作樂的天堂,卻是女人要以命相搏的地獄。
另一個常見的誤讀是關于花魁的。我們常常認定,花魁除了具備沉魚落雁的容貌,更有教養,還多才多藝,精于茶道、花道、香道、舞蹈、三味線,乃至琴棋書畫無所不通,是地位最高的性工作者。甚至傳說花魁的地位比客人更高,有自己挑選服侍對象的權力。客人想見都未必能見得上,而就算見上了,都要經過三次見面,豪擲萬金,才有可能一親芳澤。

無論花魁擁有多大的特權,依舊不能走出吉原的大門,仍是魚缸里的金魚。
首先,由專門引薦客人的茶屋安排第一次見面的“初會”,讓花魁遠遠觀察客人有沒有資格成為自己的入幕賓(其實是測經濟實力)。數日后客人再訪,花魁則離顧客稍近,但同樣不進食、不交談亦不提供服務,最多斟酒,但顧客還沒可能聽花魁呼喚其名。又再幾日,客人終被允許進入花魁的房內,這是第三次見面,爾后才成為“馴染”(也就是常客),花魁待客人也會如陷入愛河的戀人,這時客人將取得一副刻上自己名字的筷子。
傳說,吉原游女心高氣傲,會大擺架子,而客人的地位在花魁面前,根本低到塵埃里了。
魚缸里的金魚
但實情真是如此嗎?真有男人愿意幾次捧場,付了成倍的金額卻沒有得到服務?然后店家表示:我們前兩次都只收錢不會讓您做什么,第三次我們肯定會全心全意待您……江戶時代的男人不會那么傻吧?當客人登樓,花了錢卻得到一張臭臉,誰會想去第二次?所以三次見面才能成為游女的恩客,恐是耳食之論。
日本作家永井義男認為,如此奇怪的吉原傳說,可能源自吉原創建最初,仍存在“太夫”的時代。雖然我們常會混淆“太夫”與“花魁”(興許是被另一部日本漫畫《銀魂》影響),兩者確實皆為性工作者的等級。但事實上,吉原的太夫在寶歷年間便已被廢除(京都的島原則有保留),江戶后期更無所謂太夫。
最初太夫的恩客多是大名、上級武士,或是豪商,性格目中無人,因而太夫可能一氣之下直接離開不提供服務。但從這些“霸總”的角度看,卻是“女人,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這樣的新奇感。到了江戶中后期,時代更易、消費群體從過往的上級武士擴大到庶民階層,消費習慣隨之改變,行業行為自然也有所切換。

即便花魁不像游女般,坐在木格子柵欄內為客人所選,但說到底,無論是上層花魁,抑或下層游女,都只是櫥窗內的商品,不過是供人取樂、排遣的工具。花魁為了出道需要高額的訓練費用,加上各種吃穿用度、下人、侍從的開支,絕對是一筆巨款。所以一切不過是商業上的投資與回報,也自然是價高者得。再從這個角度看花魁,基本就是妓院的宣傳、藉此招攬客人,并幫花魁的恩客炫富、做排場。
畢竟在大眾眼里,花魁絕不僅是煙花柳巷的風俗女,更代表著華麗的戀愛夢,是男人的偶像、女子的時尚教母。能與花魁春宵一度,代表著男人的社經地位,而被花魁拒絕,則代表男子財力不足、身體欠佳、沒有文化、不懂浪漫等,足以宣告其社會性死亡。然而追根究底,都不過是男人的無聊攀比而已。
不難想見,游女們的平均壽命僅有20余歲。
至于花魁比客人有更高的社經地位這個說法,純粹只是在宴席場合中,花魁坐上座,而客人在下座的緣故。這僅僅只是吉原限定的游戲規則,并不適用于現實。
正如無論花魁擁有多大的特權,依舊不能走出吉原的大門,仍是魚缸里的金魚,男人只想它在魚缸里,展現專屬于自己的美。
被賣的女兒
無論游女或花魁,這輩子想走出去,只有幾種可能:28歲退休、自己給自己贖身,或讓恩客掏錢贖身。
而一年365天,就算是月經來潮都要營業,只有新年那一天是公眾假日。至于每日作息更勝“996”,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喜多川歌磨的浮世繪版畫作品《青樓十二時》。休息時間少得可憐,無論日場夜場,都需要服務多名恩客,拼死勞作,以發揮自身最大的商業價值。
不難想見,游女們的平均壽命僅有20余歲。幸運的話,熬到28歲退休,總可以自由了吧?
即便名義上恢復自由身,卻不代表游女沒有妓院各種償還不清的債務,要不留下來做苦工,要不去當私娼還債,收入大減,衛生條件還更差、更容易染上疾病。少數還清利滾利債務的游女,卻已失去生育能力,更多的是在某年某月,被榨盡最后一點剩余價值后,被脫光衣服、包上草席,投入凈閑寺中。
逃跑呢?基本是不可能的。除了遣手婆的時時監視,在發現異狀時,妓樓將迅速組成搜索隊。逃亡的游女越不過環繞吉原的齒黑溝,只能自大門離開,但大門的四郎兵衛會所由官府派人常駐,負責盤查試圖走出大門的女子。即便僥幸逃出,由于娼家間有聯絡網,一家有逃妓,便會在全國各妓樓范圍內被檢視。如果逃跑被帶回,免不了一頓毒打,甚至有人被打死。
天正十八年,德川家康設立江戶幕府,大量離鄉背井的男性從而擁入江戶尋找工作機會,戰國時代告終,失去主君的浪人也來此尋覓新的可能。由于過多單身男性的欲望需要被排解,當時的風俗區又過于分散,不好管理。除有損公共道德,也不利于社會秩序,因而江戶幕府允許在現今日本橋人形町設置公認的吉原妓院。明歷大火之后,舊吉原被燒毀,于是幕府命令吉原搬到當時仍是農田的淺草附近,設立新吉原。



數百年來,“吉原”就是江戶夜生活的代名詞。此地聚集當時最流行的事物,也發展出新的藝術與文化,影響整個社會。
但這個城中之城的上千名娼妓中,有些是為了糊口自愿出賣肉體,但絕大多數都是“女衒”—從日本各地貧窮人家處,以“為父母盡孝”為由買來、賣進青樓的女子。在那個年代,女子只是貨,宜買宜賣。
而對幕府來說,吉原的存在,可以避免單身男子成為社會亂源,還能促進內需、增加稅收,而透過販賣女兒,也使窮人家的生計有了著落,社會安全亦得以維持。
然而,這一切風光華麗的背后,藏著多少吉原女人的辛酸。
特約編輯 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