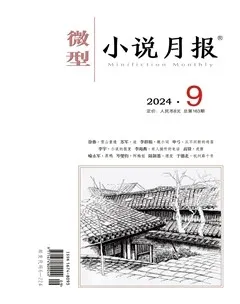理發
老周轉業到地方已有三個年頭了。三年里,每到理發的時候,他都要忍受老婆沒完沒了的嘮叨,全是為了他的發型。不到一寸的短發,從當兵起他就是這樣理的,在腦袋上站立了快二十年了,現在已站出幾根花白的。老婆偏要叫他變一變,留個長發,再吹一吹風。說是要跟得上時代,別整天像工農干部似的。說歸說,每次她還得老老實實拿起推子,像隨軍以前收拾麥茬那樣把丈夫的頭發收拾好。有時,老周都覺得好笑,嫌我像工農干部,當初人的最高理想還不就是當工人嗎?現在跟我扯起時代不時代來了。
老周不肯改掉那個短發,倒不是不忘本或者不想跟時代,沒想那么復雜。他從班長、排長、連長一直到營長,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捏一把推子,嚓嚓嚓給戰士們理平頭。還記得有個新兵不愿意理,從一樓的窗戶飛身而出,光給他們講軍容風紀條令要求自然不夠,老周費了不少心思,還說出了這短發如何如何好看。說著說著,他心里想想還真是那么回事,理出了短發好看的許多道理。跟人家、跟自己說了那么多好處,轉眼自己倒變了?雖說戰士們看不見,但老周自己總覺得不厚道。
“短發好呀,你看那個日本的杜丘,都說是一條漢子。”有閑心時,老周逗她一逗。
“拉倒吧。人家臉上是一道一道肌肉,你呢……”
老周生氣似的繃起胖臉,不再理她。她愛說什么就盡管說什么,只要不誤了給他倒洗腳水,不誤了給他晚飯溫二兩,盡管說。當然,她不敢誤了給他理短發。
不覺到了結婚二十周年,金銀銅鐵,老周也弄不清是哪個婚,二十年前的時光讓他胖臉泛紅。他想了好幾天,覺得要讓老婆驚喜一下有難度,終于咬咬牙說:“我要留長發了,給我吹一吹。”
老婆張大嘴巴呆了好半天,等發現這死東西確實不是作弄她時,滿臉綻開了花。其實老周給她出了個難題,他頭發是該理了,也只是比平頭長一些,就是加化肥,也到不了吹風的地步。
可老婆顧不了那么多,她要的是政策。連著好幾天,她拿兒子的鉛筆頭在紙上畫來畫去,說是設計發型呢。老周等得沒耐心了,催了幾次,說頭上癢死了,還不快理。老婆說別急別急,趁長勢不錯,再堅持幾天。
老周沒辦法,看看她畫的發型,也看不明白,問:“那個方框,麻將豆子上五點一面的是什么?”
“你的臉呀。”老婆深情地說。
老周心有靈犀一點通,明白了那個方框上的五點是他臉上的眉毛、眼睛、嘴。
終于,老婆拿起了推子,在他頭上細細修理著,還不時瞄一眼那紙上的圖樣。老周嘆口氣:“你應該放個大樣才好呢!”
說歸說,接過鏡子,他不能不贊嘆老婆的手藝,不長的頭發還真弄出了一波三折,像那么回事。老婆說是“乘風破浪式”。
老婆不認識似的盯他看半天,接著過來繼續修理起來。忽然,老周覺得有些不對頭,忙看鏡子,竟發現又變成了小平頭。驚呼:“你這是搞什么名堂?”
老婆也吃了一驚,看看他的腦袋,眼角有些發亮:“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光想著咋不見了我的老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