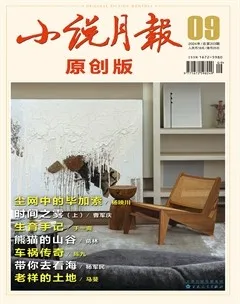畫出塵網中的風景
奉有敬在送兒子上大學的路途中,終于解放了自己畫畫的手,重新撿起了畫筆。隨著火車飛馳徐徐展開的還有奉有敬與畫畫糾葛的前半生。故事回到奉有敬的三十年前,正是他經歷高考這一年。成長在農村的奉有敬并沒有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家中的貧困讓他必須立刻投入為了生存的生活。與此同時,他對于繪畫的熱愛,也在生活磨礪與自然溫養中被徹底激發。這種激發并沒有以火山噴發的方式出現,而是緩慢隱忍地流淌在煩瑣生活的地下,時不時從日常生活的縫隙中滲出,也在日常生活面臨危機的時刻支撐起了一方天地,讓奉有敬渡過難關。
小說中通過繪畫描寫自然,更通過自然講述繪畫。生活之苦和自然之景同時扎進了奉有敬年輕的生命。奉有敬的繪畫風格我們只能從語言的轉述中自行想象,但奉有敬的藝術底色卻通過他的人生歷程了然地擺在了讀者眼前。這是一趟艱辛的藝術之旅,不僅辛苦,還頻頻躲藏。一個想要畫畫的農民,小心翼翼在辛勞討生活的間隙中尋找藝術的空間,他的雙手除了勞動之外,還嘗試握住畫筆涂抹一些僅僅是“美”的顏色,想要抓住具體生活之外抽象的激情。挖沙帶來的體驗震撼了奉有敬,如果說藝術給予創作者以精神上的沖擊,那么勞動本身給予勞動者的體驗也不亞于任何一種藝術。上半身被日光灼傷,下半身被江水冷冷浸泡,肉體感官的矛盾在奉有敬的身體中刻出傷痕,被水泡過的皮膚輕輕劃過就破出血跡,用血作畫成了奉有敬在夜晚的秘密,他成了江邊的“美人魚”,一半在陽光下,一半在深水中,一半感到炙熱,一半備感濕冷,美人魚游泳在奉有敬藝術和生活的交界處,成了奉有敬繪畫生涯的隱喻。奉有敬用血在報紙上畫出了魚群,舊報紙上的血凝固泛著烏青,伴隨著大伯低罵的一句“癲仔”被永遠留在了河邊的小屋中,奉有敬有關畫畫這件事的不被理解與刻意隱藏的基調就此定下。
在開荒的歲月里,奉有敬在自然中與萬物共處,他聆聽大地,又與山巒比肩,他在夜晚和動物們進行著秘密的交流,他被太陽曝曬,他赤裸穿行于林間。自然讓他返璞歸真之后,畫筆又讓這自然的瞬間凝結,他畫出了《陰陽》《長在身上的田七》,奉有敬的畫有了名字,他也在自己的畫中找到了最為舒展的位置。只是好景不長,正如一開始出現的美人魚隱喻。一絲不掛在山林中穿梭的奉有敬被村民傳成瘋子,在村主任兒子婚禮上闖禍后,母親撕碎了奉有敬山上窩棚里的畫,他被當作一個魔障的瘋子,成了一個必須出逃的兒子。
于是奉有敬開始了從寧夏到東北再到山西的人生。在輾轉多地的日子里,他依然盡全力勞動、生活以及愛。在從單身到成家的過程中,他遭遇了欺騙、目睹了死亡、找到了伙伴也定下了家業。畫畫的念頭在一波接一波的生活轉折中暫時按捺下去,但一路上他目睹的人情和風景始終刻在記憶中。小說一開始,奉有敬感嘆高鐵的速度,現代交通工具的極速飛馳折疊了太多風景,在坎坷的生活中他看見“南方山多,北方平原多;南方的水田、北方的麥地、南方的橘子樹、北方的蘋果林”。這些都是他畫中記錄的對象,也是他之所以激動提起畫筆的原因,他看見“每個站點上來操著不同口音帶著不同氣息的人,他會到站臺上買一些吃食,盒飯、餅子、饅頭,飲食習慣也隨地域在變。這些有層次遞進的變化,讓他的不安和心怯一點點平和消化,最后化成對目的地滿心的期待”。這些都是生活的真實細節,是他繪畫吸收的養分與靈感,在這些部分的滋養與刺激下,他的畫才有生氣和激情,“他捏著顏料棒才有感覺,才敢大膽落筆用力涂色”。當他擁有了安穩的后半生,他始終記得的依然是在艱難時刻作畫的心情:“那真是一段永生難忘的時光,就像那些年把皮膚曬脫一層又一層的陽光,不是只停留在皮膚上,而是穿透到血肉里。”
奉有敬是真正的藝術家,真正的藝術家是不會被生活打敗的。對于奉有敬來說,用盡全力生活成了他投入藝術的前提:“他沒覺得干活兒有多累,就算有些累,當坐在窩棚里畫畫時,他會變得輕松快活,仿佛他能靜下來畫畫,是他用勞動換來的,勞作得越累,他畫得越安心。”生活成為他畫畫安心的來源,他的藝術從來沒有脫離過生活,或者說,他的藝術始終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因為繪畫時刻的珍貴,他的整個生活都成了這一珍貴的支撐。藝術家需要專注,真正的專注不是無憂純凈的產物,真正的專注產生于嘈雜、混亂、充滿意外的生活。奉有敬并不是一個通過藝術與現實對抗的憤世嫉俗者,也沒有在生活的打磨中隨波逐流,他不是天才,或者說他沒有天才的際遇,然而他專注地投入藝術,他羞于表達自己繪畫的欲望,但始終維護著內心畫畫的沖動,直到他完成了家庭的使命,直到他經歷了成為媒體采訪的紅人,再直到這一陣風潮過去,他又回到了無人問津的狀態,他始終在畫,他不在意。他最后的畫也有名字,叫《全家福》,他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位置,這個位置的旁邊是家人,是過往的生活。回到小說的題目,畢加索是一位具有極強生命力的畫家,他長壽,他不斷變化更新,他從藍色時期走向超現實主義時期經歷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畢加索”來自他母親具有異域風情的姓氏,然而,他的父親何塞也是一位畫家,一位沒有資格進入美術史討論的“大多數”,在這位畫家的前半生里,他喝酒、做工、畫鴿子,和大部分西班牙勞動人民一樣在閑暇之中找一點藝術的快樂,并不偉大。
藝術與生活之間是怎樣的關系?文學所創造的故事既包含了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作為關系本身的呈現和垂影。塵網,既是奉有敬與藝術相隔、相望的桎梏,也是最后讓他找到歸處的依托。年輕時因為貧窮在謀生的間隙中偷一方天地畫畫,成家后在立業之余等待某一天畫畫的自由,奉有敬看似因為生活之中家庭的羈絆無法盡情畫畫,然而這張生活織成的網,構成了別樣的畫框,從現實編織成的密網透進無盡的風景,這樣的風景,只存在塵網中。
作者簡介:諶幸,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本文為遼寧省社科基金“新時期文學中的稗史傳統研究”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韓新枝張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