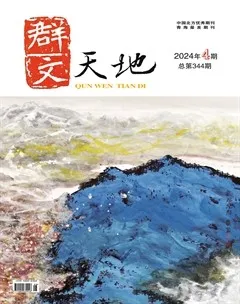農村眉戶劇中鄉土俚語的妙用
元宵節回故鄉,親友邀我去看青海眉戶劇。我想,電視中多少精彩的節目都無暇顧及,何況眉戶劇?但盛情難卻,只得隨眾前往。
露天劇場,幾塊木板續搭在房前臺階上,幾塊紫紅的舊地毯覆蓋在上面,這就是戲臺。樂隊分列在戲臺兩邊,演員從房門里出來就登臺演出。臺下人們自帶矮凳密密麻麻地坐了一院子。
鏗鏘的鑼鼓聲后,一名演員隨樂扭扭捏捏搖擺上臺,觀眾一片笑聲,原來該角色是眉戶劇《小姑賢》中的姚氏(實是妖氏)。這個角色雖先聲奪人,但也不過一丑角而已。隨著劇情的發展和幾出戲劇的展演,劇中通俗、鮮活、生動、幽默詼諧的鄉土語言及其塑造的典型形象、反映人物靈魂的創作手法深深地打動了我。
《小姑賢》中的姚氏說:“娶來的媳婦買來的馬,任我騎來任我打!”姚氏把兒媳比作馬,馬可以隨意鞭打役使,意指兒媳也可以任意打罵奴役。一句俗語,把封建社會刁蠻婆婆的思想觀念和盤托出,她平日對兒媳的挑剔虐待也由此可想而知。姚氏問兒媳婦是否掃了院子,“你如果沒掃院子,我要將你左擰麻花右擰馓子!”“麻花”“馓子”都是青海地區用手工搓擰的油炸食品,姚氏用“左擰麻花右擰馓子”來比喻要用狠辣的手段變換方式狠整兒媳。姚氏看了兒媳掃得干干凈凈的院子并不罷休,說道:“東一笤帚,西一笤帚,好像給灶王爺畫胡子!”據說灶王爺的髭須只有稀疏的幾根,姚氏用這個比喻責罵兒媳掃地不仔細、不干凈。姚氏故意挑剔兒媳納的鞋底是“胡納亂戳,好像是給老驢釘掌!”給壯馬走騾釘掌,要用馬蹄釘有規律地、細密地釘上;至于體弱力衰的老驢,役使的價值不大,給它釘掌,也只是稀疏地胡亂上幾個釘子罷了。姚氏用日常生活中“給老驢釘掌”的事例比喻兒媳鞋底納得不細密、沒規律,以此來否定兒媳的針線活。姚氏主張用暴打、狠罵對付兒媳,她的口頭禪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打倒的媳婦揉倒的面,散(攪動)到的散飯(青海地區一種面食)吃起來黏”。寥寥幾句,就把一個刻薄刁鉆、百般挑剔、虐待兒媳的惡婆婆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小姑賢》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是姚氏的親生女英英。她批評母親辦事不公,對嫂嫂沒錯找錯、百般虐待,搞得家宅不寧。姚氏認為這是兒媳教唆的,就變本加厲地打罵兒媳。英英給哥哥訴苦說:“我說了娘幾句,咱娘就豆角兒拉到瓜架上,怪起嫂嫂來了。”用“豆角兒拉到瓜架上”來比喻姚氏胡亂攀扯,姚氏的蠻橫專斷可見一斑,同時也表現了英英的聰慧機智。英英批評哥哥:“平日像個棉花團團、蜂糖罐罐。”用“棉花團團”比喻性格柔軟,“蜂糖罐罐”比喻待人可親,原本這是個好性格,但在這里英英指出他的這種個性過分地遷就了母親的惡行。語言雖少卻精練,以農村生活中常見的事例作比,抓住本體喻體的相似點,形象地表現了人物各自的特點。
與《小姑賢》相反,現代眉戶劇《打碗記》表現的是現今社會上有些人不贍養父母,甚至虐待老人的內容。用通俗個性化的語言表現人物特性是這出戲劇的一大特點。
陳奶奶的大兒媳孫如意是個典型的“河東獅吼”,她把自己的丈夫訓練成“聽話沒脾氣,叫他打狗不攆雞,咳嗽一聲就會意,讓他上東不奔西”這般唯妻命是從的懦夫。孫如意事事都如意,真好比“吃著甘蔗上樓梯”,但是“心中還有一根刺,老瞎子(指婆母)八十歲還不死……哪一天火葬場去登記,我掐著手指算日期。”這里用了兩個借喻的修辭手法,說明孫如意的日子過得甜美富足,步步登高。她不愿贍養老人并非生活艱難養不了,而是嫌棄婆母,把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時時盼婆母早死,好叫她眼前清凈、心中舒暢。短短幾句,就把一個蠻橫無理、厭棄老人的刁婦嘴臉勾勒出來了。再看題目《打碗記》里的“碗”有什么特殊的含義呢?這是指陳老太的專用碗,老人悲憤地唱:
生病在床難洗碗,飯粑粥糊粘滿碗,
餿味酸氣不離碗,別人當它貓飯碗。
吃飽也是這一碗,挨餓還是這一碗,
你要想再添一碗,不是拍桌就打碗。
扮演陳奶奶的演員唱到這里時淚流滿面,臺下唏噓一片。從這只糊滿粥粑、帶有餿味的“貓飯碗”可看出陳奶奶悲痛辛苦的生活。這種以小見大、概括力很強的創作手法極強地表現了故事內容。這只飯碗被陳奶奶的孫媳,也就是孫如意的兒媳白玲稱為“千金難買”的“傳家寶”,并說要學婆婆的樣子,將來要用這只碗“孝敬”自己的婆婆,這里用“傳家寶”“孝敬”等反語來警示孫如意應當改惡從善,否則,奶奶的遭遇就是婆婆的遭遇。戲中有“婆婆的樣子,媳婦的鞋”的諧音雙關指物借意,“樣子”即鞋樣子,做鞋先得用紙剪出鞋樣子,這里指孫如意虐待婆婆的種種惡行給兒媳留下了樣子,將來媳婦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眾人的教育下,孫如意覺醒了,她表示要痛改前非、孝敬老人。這個“貓飯碗”也被白玲砸了。
反映農村家庭生活的《小兩口算賬》,運用新穎恰當的比喻、趣味性極強的歇后語等鮮活語言,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展現了喜劇的特點:
年輕婦女高彩云唱:“日子過得節節高,好似甘泉醉人心。”這個比喻恰當地體現了高彩云家的日子過得甜美舒暢,但也存在一些小矛盾。“我丈夫孫福從田間干活回來,用錐子扎也不動彈。”這里故意言過其實,用夸張的手法渲染了孫福有舊觀念、擺架子的性格特點。孫福勞動回來讓妻子給他抖去身上的灰塵,但他又埋怨妻子抖土的動作是“趕馬車繞鞭子,勁往耳朵上繞著哩。”馬駕轅、人趕車,手中順執長鞭,馬若不老實拉車,鞭鞘就在耳朵上晃悠,時不時抽兩下。孫福用這個比喻挑剔妻子高彩云給他抖土時手重并錯位。孫福挑剔妻子送來的洗臉水是“滾水鍋里燙羊肚子——褪我的皮哩”。要除去羊肚子表面的一層黑皮,須用開水燙,那么給孫福送來的洗臉水是否燙得褪皮呢?顯然是夸張,這個夸張歇后語渲染了喜劇氣氛。高彩云給丈夫端來了可口的飯菜,但孫福說:“你做的飯真是面糊糊灌羊肺肺——給我出氣著哩”。沒有“面糊糊灌羊肺肺”這種做法,這是胡鬧,但把面糊糊灌到羊肺子里,卻能冒出氣泡。這個歇后語既有生動的喻義,又有巧妙的諧音,意思是飯做得不可口,吃飯是惹他生氣。
為了讓丈夫體會操持家務的辛勞,高彩云和丈夫互換崗位,她到田間勞動,丈夫在家干活。高彩云在外干活回來,讓丈夫給她抖土,故意挑剔說:“你抖土是二桿子打鐵——死砸”。青海方言“二桿子”,即缺少心眼、言行莽撞之人。這個歇后語的后面部分“死砸”是對前面部分的解釋,意思是手重且沒有眼色。比“繞鞭子”程度深。高彩云認為孫福送來的洗臉水是“懷里揣冰——涼透心”。此句是歇后語,意思是水太涼,與水太熱相呼應。孫福上飯,拿出焦煳的餅子,高彩云忍俊不禁:“哎喲,這是哪一國的洋點心!圓不圓,方不方,黑乎乎的。”她咬了一口故意吐掉:“把人苦死了!我不吃這煳羊頭,我要吃飯。”這里用了反語——洋點心、借喻——煳羊頭兩種修辭格,幽默地諷刺了孫福做的饃既難看又難吃,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
孫福認為自己在野外干活收入多,妻子操持家務收入少,對家庭貢獻小,理應侍候他。針對丈夫殘存的舊觀念,高彩云提出兩人細算創收的賬,結果高彩云的收入超過了丈夫。孫福尷尬地說:“這算來算去,我倒成了孫猴子的武器——金箍棒(精光棒)了。”這是個諧音歇后語,它的后一部分借助音近現象表達語意,言在“金箍棒”而意在“精光棒”。“精光棒”是青海方言,即窮光蛋。事實教育了孫福,他轉變了思想,心服口服地說:“我成了賣肉的收了攤子——牌子沒有了,架子也沒有了”。又是一個諧音歇后語,言在此而意在彼。賣肉需要掛肉的架子,但這里的架子實指頭腦里殘存著舊觀念從而表現出的種種言行。架子沒有了,就是受到了教育,轉變了思想。
以上這些聯珠妙語都取材于農村生活,也就是以當地農民的語言塑造生活中的各類典型形象,反映了他們的生活。聽著這樣的戲劇語言,仿佛聞到了泥土的氣息,使人輕松愜意、陶醉其中。
像這樣的語言現象在《三親家》《糊涂盆砸鍋》《冤家親》等戲中比比皆是:
“滿天星星頂不上一個月牙兒,十個丫頭頂不上一個瘸娃兒。”這個比喻反映了農村部分人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
“只盼生個頂梁柱,卻偏偏生了個女嬌娥,好像冰水身上潑,霎時從頭涼到腳。”“頂梁柱”借喻男孩,后兩句是夸張兼比喻。這些辭格的運用深刻地表現了農村某些人看重男孩、輕視女孩的思想。
“我敢敲鼓,就不怕鼓響。”比喻說話辦事不怕別人知道。
兒媳生了女孩婆婆不高興,但在親家的質問下她又否認自己的錯誤,這是《三親家》中的一句精彩比喻:“誰噘嘴板臉了?凈是磨道里找驢蹄子哩!”“驢蹄子”即驢蹄印,毛驢轉磨壓碾,在磨道里留下蹄痕,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在“磨道里找驢蹄子”是沒事找事,反問辭格否定了“噘嘴板臉”,比喻句是對反問句的進一步解釋。
“扔了一塊瓦,換來一塊磚”“辣子遇上胡椒面”。這里用了借代、比喻兩種辭格,說明雙方旗鼓相當,互遇對手。
“不曾開言心撲騰,好似屠夫來念經。”用屠夫念經假裝慈悲來比喻心虛尷尬的處境。
“無兄無弟一枝梅。”“一枝梅”比喻獨生女。
“兒女親家是金刀難斷的親戚。”金刀雖堅硬鋒利,但割不斷親戚的情誼。這里比喻姻親情誼的牢固,是任何力量斷不了的。
“她指雞罵狗。”即指桑罵槐。借代的辭格,部分代整體,以“指雞罵狗”的做法借代一切蠻不講理、繞彎子罵人的行為。
“我這里金針點穴來將她。”比喻以特殊的方法治思想上的毛病。
《糊涂盆砸鍋》中的二嫂是個嘴尖舌巧、少干活的人,小姑子喜鳳稱她為百靈鳥。針對她的特點,喜鳳說:“百靈鳥,你別作踐人了,哪怕是成了精的百靈鳥,喜鳳我今天也要當當餓老雕。”成了精的百靈鳥,說得好聽,唱得悅耳,這里比喻喜鳳的二嫂能說會道。“成了精”帶有貶義,即二嫂除了會唱外,還是個好吃懶做、耍奸打滑之人。“餓老雕”捕食百靈、麻雀等鳥類,極其敏捷勇猛,這里比喻喜鳳要碰一碰二嫂,治治她的懶病。
《糊涂盆砸鍋》中的張得發老漢說:“小喜鳳你想造反,這個家你攪成了亂麻團。”用“亂麻團”來比喻家亂無頭緒。
喜鳳批評自己的爹張得發的家規是“茄子黃瓜一鍋煮,葫蘆豆角一地爬。”這里用對偶、比喻兩種辭格來說明張得發老漢遇事裝糊涂,勤人多干不多得、懶人越養越奸猾、苦樂不均的糊涂家規。
“你真是紅火處賣母豬肉哩。”“紅火處”青海方言,即人多熱鬧處。母豬是下豬仔的,它的肉不能吃,或不好吃,既然如此,就不能賣了。但有人趁著人多雜亂時也“賣母豬肉”賺錢,比喻渾水摸魚。
“面沒撈完,湯又上來了。”借喻一件事未完,另一件事又來了。
“眼下還不到火候,汽不圓咋能揭鍋?”燒水時鍋蓋邊沿冒出的汽圓了,說明水開了,可以揭鍋蓋了。這個比喻句中用了兩個否定副詞“不”,說明辦事時機不成熟。
“你船不坐,橋不走,想把河過。”比喻不付出勞動就想收獲。
“強扭的瓜不甜。”比喻凡事不可勉強。
“我給你鋪路搭橋。”比喻創造條件。
“人常說:‘娃落草(地),火燒房,新媳婦上轎,狼攆羊’,這四大件事別人都幫。”這個排比句說明有重要的事情別人都會幫忙。
“這叫挖了樹根不傷皮,巧取雞蛋不殺雞,卷起褲子把腿洗,踩石過河不沾泥。”這個排比句使語勢得到加強,感情進一步加深,充分說明辦事要用妥當巧妙的方法。
戲劇中除了運用多種修辭格強化語言的表現力外,還運用歇后語、諺語、慣用語等多種熟語,簡明生動、通俗有趣地表現內容。
“我打破頭還拿扇子扇哩——怕啥”。頭被打破后不能著風,但“我”還拿扇子風,說明此人膽子大。所以,這個歇后語的后一部分“怕啥”二字對前一部分作了解釋。
“人家是豬八戒進廚房——光吃不干”。這是個喻義歇后語,諷刺了好吃懶做之人。
“土地承包經營路廣,如同酒曲和面——發頭大”。這個歇后語中“酒曲和面”是個比喻,解釋部分“發頭大”是它的轉義,即土地承包能發家致富。
“口袋里賣毛——不見面”。這個歇后語表示做事不公開。
“大年三十借蒸籠——你蒸的叫人家煮嗎”。歇后語,意借東西不是時候。
“水中放炮——沒聲響”。歇后語,意做事白費功夫。
“若要公道,打個顛倒。”慣用語,意換位思考。
“一物降一物,蜈蚣把蟒捉。”這個通俗且含義深刻的諺語揭示了一個道理,即小事物能夠用巧妙的方法戰勝大事物。
以上這些比喻、夸張、排比、歇后語、慣用語等都源于農村日常生活或口語,就地取材,信手拈來,靈活運用,鮮明生動,鄉土氣息濃,聽起來那么自然熨帖,讀起來口角留香,回味無窮。
戲散人靜,我徘徊在簡陋的戲臺前沉思良久,人民群眾中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只要深入下去,就會在這鮮活的源頭,開掘出智慧的清泉,創作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精品。
(作者簡介:巨月秀,女,退休高級教師,多次被評為西寧市優秀教師。曾出版散文集《夕陽拾零》,合著出版《藏密祖師蓮花生》。搜集、整理出版了蒲文成先生《藏學論文集》和《蒲文成書法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