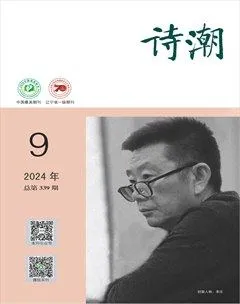楊克詩歌代表作品選
蝶舞:往事之三
軟軟濕濕的笑聲
浸潤
大化電站工地 1978
七月流火
三朵蝴蝶花三名小憩的女工
悠悠斜靠在凌空的排架上
柔情似水純潔似水
鮮亮亮的笑聲
突然
自一匹繃斷的竹篾
滴
落 翩翩
作生命之翔舞
波之舞浪之舞峰之舞谷之舞
霓裳之舞飛天之舞羽人之舞
優美得讓鋼筋水泥流淚讓傻呆呆的男人流淚
胡子拉碴的工地
竟這樣給輕盈盈摘去
笑聲三朵
大山的陰影死亡的陰影
流出一管燦燦音樂
1986年
北方田野
鳥兒的鳴叫消失于這片寂靜
紫漲的高粱粒溢出母性之美
所有的玉米葉鋒芒已鈍
我的血脈
在我皮膚之外的南方流動
已經那樣遙遠
遠處的林子,一只蘋果落地
像露珠悄然無聲
這才真正是我的家園
心平氣和像冰層下的湖泊
浸在古井里紋絲不動的黃昏
渾然博大的沉默
深入我的骨髓
生命既成為又不成為這片風景
從此即使漂泊在另一水域
也像繭中的蠶兒一樣安寧
秋天的語言誕生于這片寂靜
1987年
在商品中散步
在商品中散步 嘈嘈盈耳
生命本身也是一種消費
無數活動的人形
在光潔均勻的物體表面奔跑
腳的風暴 大時代的背景音樂
我心境光明 渾身散發吉祥
感官在享受中舒張
以純銀的觸覺撫摸城市的高度
現代伊甸園 拜物的
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
聆聽福音 感謝生活的賜予
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
我由此返回物質 回到人類的根
從另一個意義上重新進入人生
懷著虔誠和敬畏 祈禱
為新世紀加冕
黃金的雨水中 靈魂再度受洗
1992年9月5日
石 油
一
結構現代文明的是液體的巖石
石頭內部的冷焰
零度激情,綿長的黑色睡眠
保持在時間的深淵
水與火兩種絕對不相容的元素
在事物的核心完美結合
蟄伏的黑馬
永恒的午夜之血,停止呼吸的波浪
誰也無法涉過的光明河流
上下馳騁
從一個世界進入另一個世界
二
石油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
而是轉換,從地獄到天堂
從一種形態變為另一種形態
火焰是尖銳的預言
瑰麗的夢境在死的光華中誕生
火中盛開的石油看不見花朵
20世紀是最黑亮的果實
接連之聲不絕,石油在混沌流淌
生死回環的石油氣象萬千
廣大無邊的氣息
浸淫物的空間,甚至精神的空間
塑料器皿,凡士林,化纖織物
石油在一切感覺不到石油的地方洶涌
石油是新時代的馬匹、柴、布、噴泉
金蘋果,是黑暗的也是最燦爛的
今天石油的運動就是人的運動
石油寫下的歷史比墨更黑
三
就像水中的波痕,傷害是隱秘的
大自然在一滴石油里山窮水盡
靈魂陷落,油井解不了人心的渴意
游走奔騰的石油難以界定
在石油的逼視中
回光返照的綠色是最純美的境地
一塵不染的月光,干凈的美
在汽車的后視鏡里無法挽留
1993年5月6日
熱 愛
打開鋼琴,一排潔白的牙齒閃亮
音樂開口說話
打開鋼琴
我看見十個小矮人騎一匹斑馬奔跑縷縷濃云
在大海的銀浪上翻滾
一條條黑皮鞭下羊羔咩咩地叫
雪地里一只只烏鶇眨動眼睛
搖搖晃晃的企鵝,一分為二胸和背涇渭分明
生命是一個整體
打開鋼琴
曹植來回踱著七步
黑夜與白晝,一寸一寸轉換
1994年2月24日
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
夢幻之樹 黃昏在它的背后大面積沉落
逆光中它顯得那樣清晰
生命的軀干微妙波動
為誰明媚 銀色的線條如此炫目
空氣中輻射著絕不消失的洋溢的美
訴說生存的萬丈光芒
此刻它是精神的災難
在一種高貴氣質的涵蓋中
我們深深傾倒
成為匍匐的植物
誰的手在擰低太陽的燈芯
唯有它光焰上升
欲望的花朵 這個季節里看不見的花朵
被最后的激情吹向高處
我們的靈魂在它的枝葉上飛
當晦暗漸近 萬物沉淪
心靈的風景中
黑色的剪影 意味著一切
1994年11月30日
在東莞遇見一小塊稻田
廠房的腳趾縫
矮腳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它的根錨
疲憊地張著
憤怒的手 想從泥水里
摳出鳥聲和蟲叫
從一片亮汪汪的陽光里
我看見禾葉
聳起的背脊
一株株稻穗在拔節
谷粒灌漿 在夏風中微微笑著
跟我交談
頓時我從喧囂浮躁的汪洋大海里
擰干自己
像一件白襯衣
昨天我怎么也沒想到
在東莞
我竟然遇見一小塊稻田
青黃的稻穗
一直晃在
欣喜和悲痛的瞬間
2001年
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
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我的祖國
碩大而飽滿的天地之果
它懷抱著親密無間的子民
裸露的肌膚護著水晶的心
億萬兒女手牽著手
在枝頭上酸酸甜甜微笑
多汁的秋天啊是臨盆的孕婦
我想記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戶
我撫摸石榴內部微黃色的果膜
就是在撫摸我新鮮的祖國
我看見相鄰的一個個省份
向陽的東部靠著背陰的西部
我看見頭戴花冠的高原女兒
每一個的臉蛋兒都紅撲撲
穿石榴裙的姐妹啊亭亭玉立
石榴花的嘴唇凝紅欲滴
我還看見石榴的一道裂口
那些風餐露宿的兄弟
我至親至愛的好兄弟啊
他們土黃色的堅硬背脊
忍受著龜裂土地的艱辛
每一根青筋都代表他們的苦
我發現他們的手掌非常耐看
我發現手掌的溝壑是無聲的叫喊
痛楚喊醒了大片的葉子
它們沿著春風的誘惑瘋長
主干以及許多枝干接受了感召
枝干又分蘗縱橫交錯的枝條
枝條上神采飛揚的花團錦簇
那雨水潑不滅它們的火焰
一朵一朵呀既重又輕
花蕾的風鈴搖醒了黎明
太陽這頭金毛雄獅還沒有老
它已跳上樹枝開始了舞蹈
我佇立在輝煌的夢想里
凝視每一棵朝向天空的石榴樹
如同一個公民謙卑地彎腰
掏出一顆拳拳的心
豐韻的身子掛著滿樹的微笑
2006年
高 秋
此時北方的長街寬闊而安靜
四合院從容入夢 如此幸福的午夜
我聽見頭頂上有一張樹葉在干燥中脆響
人很小 風很強勁
秋天的星空高起來了
路燈足以照徹一個人內心的角落
我獨自沿著林蔭道往前走
突然想抱抱路邊的一棵大樹
這些挺立天地間的高大靈魂
沒有一根枝丫我想棲息
我只想更靠近這個世界
2009年9月18日
死亡短信
車子疾馳在去往醫院的路上
我看見天空瞬間敞開了
它澄明高曠,最深處影影綽綽
難道這么快就出界了?
靈魂漫游
好似有一雙隱形翅膀在等我
等我去赴某個既定的約會
在地上移動了幾十年
天空此刻與我重新聯通
是的,我也會像那朵浮云虛無縹緲
澹澹的,淡淡的,沒有邊際
也許,那兒再無信號,我不在服務區
世間再無我的音信
這一刻我斜躺在后座上
心境祥和,仿若干凈的水面
只一眼就洞悉了宇宙內存的奧秘
生命只是一條微不足道的信息
攜帶它的密碼
被復制到這個世界
隨后被刪除,轉發至另一個時空
某只看不見的手,輕輕按動軟鍵
睜眼表示拒絕 閉眼意味接受
我陷入平靜 坦然接受命運的騰挪
我不知道神在哪里
死亡突然變得一點都不可怕
無非在東土關機,再去西天充電
就像轉發一條短信這樣稀松平常
2012年
誰告訴我石峁的郵編
入其 ,我想給荼女寫封信
四千兩百年前,那時還沒有文字
甲骨卜辭也契刻不了我的深情
文明的前夜,她在石峁
遺址那時還不是遺址
從內甕城寄到外甕城,可有猿聲
穿過古地圖,所有的字皆生僻字
仿佛密碼,她讀不懂不要緊
就像我此刻讀不懂彩繪幾何紋
四十八個人殉頭骨,多為少女
她們是荼女的姐妹,是她祖母的祖母?
云遮霧罩時期,一切皆影影幢幢
哪怕其后千年的申公豹
豹額圓睛確有其人,何為傳說
山海經確有山海
還是神話或想象的海市蜃樓?
當覆蓋的黃土被大風吹盡
塬墚赫然聳立一座孤城
石頭大道通向城臺,我繞過石垣上的
木架構,走進她家石砌的院落
出其東門,赤縣,華夏,神州
歷史之前,其實就是文字之前
她到底是甲骨和詩經的先祖
或是遷徙他鄉湮滅了的異族
我將信寄到甕城,朝代一直甕中捉鱉
石頭像和玉人面高鼻深目
我到了陜西神木,卻一直
到不了她的石峁。地理上的起伏
暗示心理上的連綿
至于信寄與不寄
石峁本就在那兒,而她也許只在夢中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