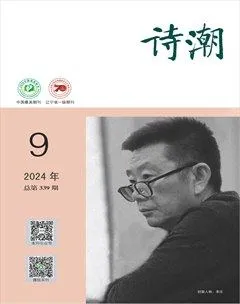麥須的詩 [組詩]
卡佛的量子時刻
我在讀美國人雷蒙德·卡佛的
《到2020年》——
像是春天掉下的樟樹葉子
一個陌生人和一些熟知的生活
他寫得很好,但這不能讓我停止發笑
他說:“那時我們中的哪些人
將會被留下,衰老、恍惚、口齒不清”
他死于1988年的2月,是肺癌
我笑得很大聲,隔壁辦公室小姑娘
的臉在門口晃了一下
之后我開始沉默,我發現
的確不是他,而是我和此刻,2024年的4月
但我仍然在2020年的昏暗里摸索
我想起我的那些朋友,想起
那些不值一提的往事
如果不是他,我將如何悄悄地沉沒
那么應該是他賦予的這個時刻
2024的2020,或是1988年前的某個夜晚
它們交疊著,是作為他的一次復活
還是那些晚凋的樟樹葉子?也許我早已死去
“他用手指摸索你的靈魂”
一個叫作狄金森的女人
和一個不叫狄金森的女人
或是一個狄金森和另一個狄金森
她們裹著圍裙,帶花邊的和不帶花邊的
走進廚房,點蠟燭或是煤油燈
有窗戶的話就可以
看看窗外,黑有兩個原因
沒有光或者沒有窗
但都不要緊,黑是一些石頭
可以摸著,尖銳的
長牙齒的,軟綿綿的
凹陷的,空蕩蕩的,墜落的
除了烤面包,也烤紅薯
蛋和魚,用嘴吃的和不用嘴吃的
煎和炸,端去給父親和別的男人
還有一些是花草和云朵,或是孤影
她們曾抓鬮或接受洗禮
也曾喝下湯藥或享用葬禮
她們寫或者不寫,聽莫扎特或是雀語
她們在廚房,在地里,也在紙上
她說:我還活著,我猜
“當你起航前往伊薩卡”
無須告訴我
你將要去往哪里
也無須告訴我
你為何要動身離去
伊薩卡,伊薩卡,遙遠的伊薩卡
烏云在翻滾,遮住
更寬廣的海,天空的額頭
黑鐵一般沒有絲毫光亮
落葉的帆影在旋轉
伊薩卡,伊薩卡,無盡的伊薩卡
閉上嘴,不要再說話
風暴里只有風暴,當你跳上船頭
砍斷纜繩,只有那無比巨大的
瞬間,那永不沉沒的瞬間
伊薩卡,伊薩卡,沒有手的伊薩卡
弗羅斯特的小徑
現在它們同樣在我的
林子里,從迷霧遮擋的遠處
行進到我的面前
行進到所有人的面前
一直就在,不是嗎
遠在我們出發之前的存在
相向而行的交會
無論路邊會長出什么樣的花草
再遲一點我會拋開這樣的
惶惑,當黃昏降臨
一幅早已繪就的長卷鋪陳將盡
攏起手,回味那些繁復
拆解成的細節,你有三個
選擇,其一,其二,非一非二
但絕不會出現第四個
“人不能同時擁有一種生活
以及對這種生活的贊美”,我們
自然而然地相信懷疑
竭盡全力去面對每一次選擇
并以此確定,我們選擇了無人的那條
石川啄木與和尚良寬
持花逃逸的良寬和尚
于今晨坐化
握著不停漏下的沙的啄木
也因咳嗽離世
手扶他們的靈柩
想著不曾見過的他們的模樣
——扮孩子的老人
扮老人的孩子
無二的頑皮,為偷吃園中海棠果子的某人
畫 皮
比如那只鬼
那原本不具形態的存在
那張因極度悲傷和恐懼變得
猙獰的綠臉
你得在語言里描摹另一張臉
小心翼翼的,如同變色龍
悄悄固定其體色
細微的吸收與融合
你一直知道
必須掩埋一部分真相
即便只是無知
那張綠臉之后的綠臉
指引你成為自我中的自我
更多的鎮靜劑
來自窗欞外更多的眼
更多的你看著
你的赤裸,而你仍是鬼
仍在夜里脫去皮囊
梭視,巡游,總在嘗試
一口咬下自己的頭顱
眾 神
有些事物我們看不見
但不影響它的存在
以一億種或只是一種方式
進入我們,圍繞我們
選擇是玄妙的,或是
不愿看見,或是不能看見
那個被放大的盲點
是樹葉,也是摘星的高樓
或是不需要看見,或是
看見本身的背離
或是不被河流所接受
而存在,或只是因為消失
我可以為你描述一只甲蟲
也可以為你描述一具
干癟的被螞蟻抬著的尸體
但你要注意,你聽到的或只是
一條腿,一根手指
或只是某一只甲蟲,某一具尸體
你永遠不會想進入的不僅是
另一個靈魂,也是另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