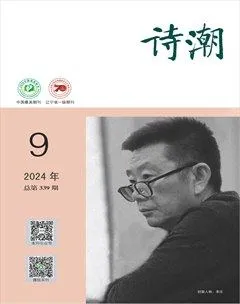詩之思[2024·第一輯]

1
人世中,唯有無常堪與說永恒,唯有無常堪與說生生世世。
2
是日日誦讀的經文幫我找到了這片密密的叢林,是這片密密的叢林幫我找到了今日之泉子。
3
詩人是這有病的一群。而一首偉大的詩歌又終因一個人的徒勞,而重獲那太樸之身。
4
在我成長過程中一個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是我的羞澀與愧疚嗎?是生命深處一種如此單純的力,是一首永遠無法完成的詩,幫我安然度過了,人世無所不在的沼澤與陷阱。
5
不要為技藝或年齡憂心。我們需要時時警醒的是,我們是否依然能夠心無旁騖地去看,去理解這人世。
6
當我廣為人知,我還是我嗎?而杜甫、屈原、陶淵明廣為人知的是他們的名,而不是詩,不是他們之所以成為他們的,那顆為空無與人世之悲歡所穿鑿的心。
7
荷花帶給我的震驚,并非此刻的美與繁華,而是它終于無可挽回的凋零。
8
我是在江南的持續教育,以及二十年如一日地與西湖朝夕相處中得以與今日之我相遇的。
9
當山脊上的岔道顯現,我選擇了人跡罕至的一條。并非是我對少、對無執著,而是我越來越傾心于,那唯有寂靜與幽暗方得相遇的美景。
10
是世世代代的文人成就了這湖,以及這沿岸的山山水水嗎?
或許,也是這湖以及沿岸的山山水水成就了生活并浸潤于其間的詩與人。
11
每一個人、每一粒微塵都是一個微型宇宙,都攜帶著宇宙全部的信息。
或許,正是這樣的秘密領悟,終于觸發了眾生平等、萬物有靈的,一種東方式的偉大辨認。
12
只有認識到物質的有限以及局限性的永恒不滅,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一個繁盛而荒涼的人世。
13
相對于李白、杜甫,我更希望能成為另一個陳子昂,并因對風骨與興寄的標舉,而終于用青山雕琢出人世從未顯現過的永恒。
14
不,不是干枯,而是這冬日枝頭蘊含的一種如此光潔、純凈、飽滿的力給予我深深的吸引。
15
在歲末,那為陽光注滿的花、草,以及一顆如此飽滿的心萬古長新。
16
我愛著這遒勁的枯枝,我愛著這隱忍的人世,我愛著這繁華落盡后,從無數光禿的柳條上垂掛下來的,一張張大地素凈的面容。
17
在疾馳的行旅中,一只在車窗前方低低盤旋的大雁讓我感動,當它穿越了如此浩渺的宇宙, 來與我相見。
18
我是王維,也是杜甫,我是李白,也是幽州臺上悵然落淚的陳子昂,我是整個盛唐呀。
我還可能是誰?我還能否再一次成為那最初的自己?我還能否——從宇宙的子宮中,再一次捧出一個如此偉大的人世?
19
這世上最繁盛而華貴的都市的見證者們去了哪里?你會是一個新的見證者嗎?當你再一次說出了美與繁華,當你用凝視在沿湖的山崖上,再一次敲鑿出了一行尚未被辨認,而已然為青苔所浸沒的文字。
20
不,不是慢,是慢到極致時,寂靜終于贈予你的,一雙從你身體至深處,得以俯視整個宇宙的眼睛。
21
永恒是這人世最堅固的荒涼,是終于將全部的未來與往昔熔鑄在一起時,那永無止境的蒼茫。
22
人倫是我們試圖從一個整體來審視人世的一種世代相續的努力,是我們在通往我們所自的本來處的漫漫征程中,那必須被發明出的束縛與憑借。
23
我愿意承接一場體內的暴風疾雨,如果它終究帶來的,是一個你此刻所見,而干凈如洗的人世。
24
整個世界、整個宇宙的意義,都在于我們歷經幾億億年的存續后,最終能否重獲那無善亦無惡的絕境。
25
只有在黃賓虹之后,新安畫派才是完整的。那是對倪云林的蕭瑟、荒涼與冷寂的借鑒與體悟中,重新發明出的一條儒者,但又絕不僅僅屬于儒者的凱旋之路。
26
如果說日常生活與偉大作品之間的敵意如此古老,甚至始于宇宙的誕生與人世的重臨,那么,所有偉大的作品又終究成全于它與日常生活相認的,電閃雷鳴同樣是春風化雨的一瞬。
27
東方文明的勝境在于一種愛與慈悲的袒露,西方文明的愛與慈悲并非是不存在的,而是更深地隱沒在了神的烈怒,與重新化萬物為齏粉的一種毀滅的力中。
28
物終究是有限的,無論花草樹木還是日月星辰,無論是大地、天空還是宇宙仿若的無窮。
29
再也沒有什么可以讓我憂心忡忡的了,除了尚處年幼的女兒點點與越來越年邁的父母,除了善良但又時有孩子般任性的阿朱,除了那依然隱沒在一個時代濃霧深處的,漢語之未來。
30
你起于無,起于一粒精子與一顆卵子在曠遠中的相遇,起于人世萬古長新的悵惘,起于萬物那共有的必死。
31
所謂的拙是指元氣包孕未泄時,人世本來的飽滿與豐盈。
32
死亡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一片樹葉凋零所引發的,宇宙深處劇烈的戰栗。
33
每個周末,你沿著北山路、西泠橋、孤山、白堤、斷橋的行走,作為日課,作為你對西湖山水一周一次,一周數次的寫生,作為你的心終于一次次從你的目光所及處汩汩而出的一瞬。
34
只有道,只有真理,只有空無使一棵樹成為了一棵樹,使人世成為了這人世。而剩余的,如落葉的飄零,如樹木的腐朽,如這人世一次次的曲終人散,而又循環往復。
35
并非繁華落盡,而是大地深處生生不息的力,通過這些光禿的樹枝與嶙峋的山石來與我相遇。
36
任何的制度、規則、技術與法都不應該是冰冷的。或者說,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偉大的民族還需要從制度、規則、技術與法深處的遠方中去重獲這人世的溫暖與慰藉。
38
當我讀到“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好像閃電從天這一邊一閃,直照到天那邊,只是他必須受許多苦,又被這世代所棄絕”(《路加福音·17》)時,我的眼淚滾落下來。
這何曾不是屈原、但丁的命運,這何曾不是陶淵明、杜甫的命運,這何曾不是佛陀與穆罕默德的命運,這何曾不是你毅然決然并終于成為自己時,那必須獨自去認領的道路!
39
不要恃那不可恃之物,直到你再一次發明出空無。
40
生命中那些不為你所樂見的依然作為一份禮物,是你終于成為了你,一首詩終于成為一首詩的那些偉大的緣起。
41
詩是一塊玉不斷地從大地,從巖石深處浮出的漫漫征程嗎?不,詩是空無因我們的凝視而從玉,從巖石,從大地那共同的至深處緩緩浮現的悄無聲息,而又永無止境……
42
弘一的寂靜是正的,倪云林的幽冷是正的,黃賓虹的渾厚華滋是正的,米芾的揮灑自如與王鐸的縱橫捭闔同樣通往著一種偉大的中正。
43
沒有法就沒有天地,沒有法就不會有這因你的悲與喜而再一次隆起的,綿延不絕的人世。
44
知音帶來的溫暖,是你確信你在人世并不孤單,即使你們互為一種極少,即使你們相隔無數的世紀。
45
只有真正理解了悖論,我們才可能承受住一次來自真理的注視。
46
陰與陽都終究是突兀的,如果它們終于不能迎來彼此消融,而萬物得以重新孕育的一瞬。
47
那些驚懼著我的,從來不會是迅疾的,而是緩慢而不絕如縷,是仿若無盡而又悄無聲息……
48
人世的至善通過你的心寫在了臉上,人世的歡喜與絕望穿越大地至深處晃動不止的針眼后,終于熔鑄出你頭頂仿若無盡的蔚藍。
49
沒有比不偏不倚更溫潤的漢語了,沒有比自然而然更飽滿而富足的人世……
50
不,不是語言,而是你在一往無前時,這人世之孤絕將你挽留。
51
我終于可以坦然面對生死了。而我終于沒有辜負漢語,辜負語言與萬物深處的道或空無透過如此紛繁的人世完成的,對一位詩人的揀選與辨認。
52
你不僅僅生活在此刻,你不僅僅生活在這個時代,你不僅僅要為漢語活著,你不僅僅要去成為屈原、陶淵明、但丁的同時代人,你還必須再一次說出一個本來的人世。
53
堅持,堅持一條歧路,甚至是一條相反的道路,直至你為這人世重新開掘出了一條偉大的通衢。
54
許多在你曾經的寫作之路上仿佛不可逾越的天塹與山峰,包括最初你周圍的友人,包括在你的前行中不斷給你以養分的米沃什、布羅茨基、沃爾科特……他們已化為在你今天回望中的山巒起伏,以及曾為你的步履丈量過的,一條煙云深處若隱若現的道路。
55
命運一直厚待于我,它用一次次的峰回路轉,來向我描述了這人世的無常與永無止境。
56
自從我發明出道與真理等詞語后,我以為不再有更遠的遠方,直到驀然回首時,我再一次看見了青山那仿若靜止的奔騰。
57
阿羅漢是一張或是一張張修行圓滿,而依然保留著這人世之奇崛的面容。
58
詩是為那顆終于安住的心準備的,是我們在通往幽暗與寂靜的永無止境中,那所有的惶惑與不得安寧。
59
一首偉大的詩對應于你終其一生的徒勞,對應于一枚銀針落向大地時那巨大的轟鳴。
60
漢語的魅力依然是在源頭上的,是對空無的一種如此殊勝理解,并終于吐露出這為你我所見的壯麗山河。
61
詩的艱難是一個人真誠地面對這世界的艱難,是一個人毅然決然去成為自己時,那一次次獨自認領下的歡喜與絕望。
62
三日不讀經,你口中呼出的氣已有了異味。
十日不讀經,你應羞于與鏡中那張略帶猙獰的臉龐相認了……
63
至美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以及那注定與絕望相伴隨的永恒。
64
王陽明說,持志如心痛。
這是一種將整個人世凝聚于一的專注,直至你終于將這徹心之痛,轉化成宇宙最初的澄明。
65
真正的張力不是那個孩童手里被拉成滿月的彈弓,而是這世界之所以成為這世界的,黑洞般飽滿的靜寂。
66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無旁騖而又不置身事外,就像—道不遠人,就像空無甚至永不舍棄,那些猙獰與絕望的面容。
67
生命中無處不是偶然,并經由那從一個堅不可摧的核中生長出的藤蔓,而連綴成這人世的蜿蜒。
68
我們所有的執著都會化身為一個我們看不見的巨獸所張開的血盆大口。
69
每一種表達都是對的,而我孜孜以求的是一個本來的人世。
70
不是憤怒出詩人,而是一塊被推向深潭的巨石在為飛濺的浪花賦形。
71
詩源于過剩亦源于貧乏,源于一個絕對的平衡點,或空無之永不可及。
72
所有的愛與恨都源于我們心中的執著,而我們又必須去愛我們目力所不及處,愛那宇宙的來與去處的微茫、寂寞與孤獨。
73
每一朵浪花都是有意義的,就像每一顆露珠,每一朵鮮花,每一粒星辰,就像我們正穿越的一個茫茫人世。
74
一個時代或許會辜負你,但只有一個不怨天不尤人者才配得上生生世世。
75
一切都源于一個樸素的愿望——去成為一個單純詩人,一切都源于你因終其一生的徒勞而終于寫下的一首無字的詩。
76
這從來是一個至純至善的世界,這從來作為一個險惡的江湖,而你從來是那個歷經滄桑的人。
77
還要經歷怎樣的風霜,我才能配得上這一池的殘荷?
78
不是在尋一首詩,而是我聽見了大地之寂靜。
79
語言或者說詩在根本處是人。或者說,人世有著怎樣的美與善,詩才能企及怎樣的真與圓滿。
80
知音永遠是稀少的,假如你不甘于平庸,假如你立志,并終于成為一名詩人。
81
詩人可以與官員、商人發生關系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而詩人與官員、商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又作為自由、獨立最好的試金石,并幫助一首詩終于成為一首詩,一個詩人終于成為一個詩人。
82
任何你所恃的都在生成,一種嶄新的羈絆與束縛。
83
所有的言說都是成立的,在各自所是的層面上。
譬如嵇康的“聲無哀樂”。聲,包括萬物在本質處是無“哀樂”的,而“哀樂”又是聲音終于成為聲音,你終于成為你的那些偉大的沮喪或標志。
84
相對于空間,我更信賴于時間的甄別,就像空間對物質的考驗可能會更嚴苛,而時間對應的是精神,是道之凱旋,是人心在千年變遷中終于得以保全下來的永恒。
85
“一帶一路”對應于一個時代,一個民族那偉大的夢想,對應于我們對整體性世界永遠的鄉愁。它與詩有著一份相同的初心:去成為這世界重回一個整體的力。而它又極度契合現代漢語當下最重要的關切:經過一百年來對西方的全面借鑒,是時候我們必須去說出一種東方或漢語的辨認了,一種對這個世界最精微的理解,一種可以反哺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的愛與慈悲。
86
散文詩存在的前提在于它作為詩的王國中一個邊遠而又日益重要的省份。但如果有一天它試圖從詩的王國中獨立出去,即意味著覆滅或終結。或者說,它必須依然如此簡潔,如此凝練,如此飽滿而又不得不用一種更寬大,接近于散文的容器將它整個盛放進去。
87
所有的生生滅滅都不是生生滅滅,而是無窮無盡的天塹與斷崖,是我們通往道與真理的無數的棧道或通衢。
88
在一場大雪過去很久之后,只有沿湖亭臺的屋瓦依然是白色的。
而你仿佛突然間回到了多年之前,那個你第一次從經文中品嘗到甘醇的薄暮。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