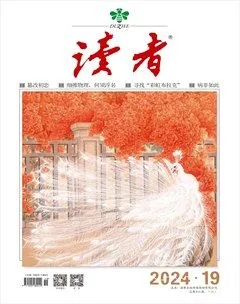火車大巴扎

“巴扎”,源自波斯語,意為集市、農貿市場。
2015年,我坐上從廣州出發的慢車,去北京見在那里讀書的女友。硬座,兩天一夜。背包里除了幾件衣物,還有一本美國作家保羅·索魯的《火車大巴扎》。喧嘩、擁擠、人來人往,車廂內混雜著體味、浸泡太久的紅燒牛肉面味兒和煤的氣息,這是我關于綠皮火車的記憶。高鐵時代呼嘯而來,將緩慢、過時的綠皮火車拋在身后。
1973年,同“數字游民”遍布的時代尚有距離。所謂旅居者,通俗來講,基本是無業游民。保羅·索魯這年32歲,出版過幾本小說,作品反響平平,收入只夠他在倫敦旅居。
電影《革命之路》拍得老辣,一個在世俗意義上不太成功的文藝愛好者,面對中年危機通常有兩種出路——要么偷情,要么遠行。在中年“白男”眼中,亞洲,東方,異域,種種婀娜搖曳的姿態,與情人無甚分別。在維多利亞車站7號站臺,保羅·索魯攥緊手心里那宛如一份滿分答卷的洲際列車車票。
1975年面世的《火車大巴扎》,是保羅·索魯橫跨歐亞大陸之旅的記錄。4個月的時間,他遍乘各式火車:曼德勒快車、馬來西亞“金箭號”、越南的當地火車,以及那些名噪一時的線路——東方快車、北方之星、西伯利亞橫貫線。窗外景致變換,車廂內永遠是一片鬧市景象。高談闊論、竊竊私語、爭吵、叫賣等,密集的臺詞日夜糾纏不休,這是獨屬于綠皮火車的劇本。
所有交通工具中,火車最為篤定,有始有終。出發后的列車,無論如何延誤,終會遵循軌道、抵達終點。每站經停時,又有廣播反復提醒。
這種確定性、方向感,是對話的底氣。在綠皮火車時代,乘客之間全程不閑聊而面面相覷,幾乎是天方夜譚。尤其是長途列車,其座位和床榻設計僅從經濟實用性角度考慮,與人體工程學背道而馳。或坐或臥,過不了許久乘客便會四肢僵直。如果不靠閑談打發時間,幾乎等于受刑。
火車上的對話,如同地圖上鋪陳開來的鐵路網,看似雜亂隨意、蜿蜒蛇行,實則井然有序,無非向東、向南、向西或向北。剛登上列車的乘客,未在人群中坐定,免不了先消受一番盤問。怎么稱呼、鄉關何處、做什么工作、去哪里公干……流程好似舊時幫會“拜碼頭”,先將家底交代清楚,才能放心落座吃酒。幾個來回,關系升溫,話題便像冰面崩解時的細密紋路,往四面八方發散開去。
國際局勢、家長里短、中醫養生、致富之道……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綠皮火車就是最早的聊天室。講真話、假話,聊鄉野瑣事、都市怪談,百無禁忌。現場聽眾投入、動容、鼓掌、落淚、咒罵,但也自持分寸。
如同看午夜場的肥皂劇,八八六十四集,九九八十一難,過目即忘,是一種溫馨的無情。話不投機時,便起身去打熱水、上洗手間,彼此心照不宣——可以了,到此為止。聊到興起,調座位、分享自帶的吃食還不夠,再就著怪味胡豆碰個杯,仿佛多年未見的老友相聚。
“瓜子、飲料、礦泉水,兩邊乘客收收腿。”列車售貨員的吆喝聲打斷持續的鼾聲,新一輪對話開始。乘客總會對推車上的商品討價還價,售貨員似乎也早已習慣,甚至享受這類“刁難”,穩立在車廂中央,喜怒不形于色。此般拉扯往往以售貨員的勝利結束,那些廉價且產地可疑的“地方特產”,將會被乘客帶回綠皮火車都無法抵達的地方,成為一段故事或傳奇的佐證。
汽笛轟鳴,順風可送出十幾里,火車減速,撞擊鋼軌的聲音變得沉悶。廣播嘈雜作響,片刻之后,列車長清清嗓子,緩緩播報前方到達的站點。車廂里的對話戛然而止,即將下車的旅客紛紛起身收拾行李,向車廂連接處移去。綠色的巨獸終于頹然不動,幾十張口齊開,乘客如流水一樣瀉下。來不及,也不必說再見。候車的人們瞬間涌入,推搡著走進火車的腹腔,填補瞬間的空白。留在車上的乘客像被抹去記憶一般:“怎么稱呼?”
不久前,一個年輕人在火車臥鋪的下鋪掛簾子,引發熱議。可見在高鐵時代,綠皮火車的喧嘩已讓人無法想象,且難以忍受。如今坐火車,降噪耳機、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肩頸靠枕等裝備齊全,架起隔絕社交的高墻。驕矜且脆弱的現代生活,拒絕了大范圍接觸陌生人的時刻。從此,綠皮火車也變得沉寂,“旅行”漸漸退化成“行程”。
在《火車大巴扎》中,保羅·索魯這樣寫道:“在火車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但他一定從未設想過,在未來的高速鐵路上,人能如貨物般齊整、寧靜、安適,演著獨角默劇。
(療 愈摘自《新周刊》2024年第14期,陳岱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