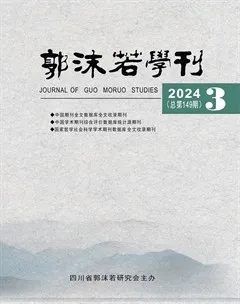主持人語
青年郭沫若在四川求學成長的歲月,正值中學與西學砥礪、舊學與新學斗妍的時代,知識的激增已遠超經史子集之范疇,其中不乏別開生面、石破天驚的論斷,這些見解乃數千年來所未有,即便是飽學之士、資深儒者也未曾涉獵。郭沫若在為廖平今文經學所吸引崇拜的同時,又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和探索的強烈欲望。在近代蜀學的滋養下,他對儒釋道三教和合的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領悟,興機觸發便可“醉眼欲窮天下勢,攬衣直上最高臺”,高臺之上更有“大叫狂生郭八來,但聽山壑呼長諾”壯志豪情,然而現實畢竟“烽火滿目,荊棘叢生,時局滄桑,一日千變”,日漸式微的儒家理想在“黑鐵主義”“武力強權”之下難以維持,但青年郭沫若在對新理論新思想新主義充滿渴望的同時,仍希望“同胞齊努力,愿漢家四百兆數之文明上族,演出這般事業來!”這便是有為青年在面對民族國家危機時矛盾迷茫而又奮發踔厲的精神姿態,從某種意義上說,后來郭沫若赴日留學、棄醫從文、投筆從戎、歸國抗戰等重大人生選擇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他青年時代精神追求的縮影。新文學家郭沫若對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與同情,但其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旨歸卻意在建設和發展新文化。正是源于此種長久的思考與探索,郭沫若于1925年寫出了《馬克思進文廟》這一戲謔游戲的歷史小說,讓馬克思和孔子這兩位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名人跨越遙遠的時空距離,在小說中相談甚歡,引為知己。郭沫若這種穿越戲謔的方式顯然不夠嚴肅,被認為“暴露出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a5M3qBXmL1SpgoKMb5J61w==膚淺和含混”,且在宿儒經師和古今儒家眼中也是對圣人的褻瀆。趙雨晴同學《戲謔外表下的嚴肅思考與現實選擇——淺析〈馬克思進文廟〉》一文,不僅看到了郭沫若游戲之作背后對中西古今之學對話交流的嚴肅思考,嘗試在現代儒學發展的脈絡中,呈現郭沫若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踐上的積極探索,也注意回到歷史現場,揭示郭沫若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對國共合作背后潛在話語矛盾的洞悉,以及希望通過“馬克思進文廟”的方式進行調和,夯實國民大革命理論合法性基礎的努力。同樣是在1925年,面對不斷喧囂的“祖傳”“老例”“國粹”,魯迅再一次提出要發動“思想革命”,在擱筆一年后重啟《彷徨》的寫作,撰寫了第五篇《長明燈》及以后余下諸篇。宋驍航同學《“長明燈”:“思想革命”重啟中魯迅對傳統的新批判》認為,“長明燈實為魯迅對1920年代中期興起的國粹復古思潮的具象描摹”,是魯迅在這一時期對于傳統文化問題的更深入的思考和批判,并進一步呈現魯迅的傳統觀,既在內容組成上有“橫向”的“完全拒絕”與“某些成分有意義”之分,更有著在精神上“縱向”的“真義”與“僵化”之別。魯迅、郭沫若等新文學名家對民族文化批判性繼承和創造性轉化的態度無疑具有示范作用。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以沙鷗為代表的青年詩人聚集在一起成立“春草社”,展開“詩歌大眾化”試驗,在巴蜀之地掀起了一股以方言作詩的風潮,以期進行更為廣泛的群眾動員和文化傳承。鄭娟博士《“把詩還給人民”——論沙鷗〈農村的歌〉〈化雪夜〉的農村書寫與方言嘗試》一文,從刊行和傳播的角度考據沙鷗與“春草社”內在關聯的同時,以具體詩歌文本校讀,展現了沙鷗方言詩歌從《農村的歌》單薄、刻板的農村印象式書寫到《化雪夜》不斷臻于成熟的創作過程,以地方路徑為研究方法重新定位沙鷗在四十年代川渝地區的文化位置。本期“青年論壇”三篇論文并非單純的“郭沫若研究”,在文獻的使用、文本的細讀和歷史語境的還原等方面尚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然而,諸位青年學者秉承了“郭學長”嚴謹的學術風范,尤其是在對待現有研究成果的態度上,展現了他們對當前學術動態的深刻理解,以及勇于開展大膽學術對話的氣度。這種積極的學術態度,無疑是值得贊賞和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