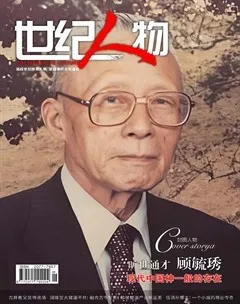把醫保變成“健康稅”,幫不了窮人
日前,國家醫保局會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印發《關于做好2024年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障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2024年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財政補助和個人繳費標準分別較上年增加30元和20元,即每人每年分別不低于670元和400元。雖然這是自2016年以來個人繳費新增標準首次低于財政補助新增標準,但是與20年前農村居民參加醫保每年僅需繳納10元相比,漲幅已然高達40倍。
在此背景下,北大教授李玲的一個視頻引起了廣泛關注。李玲在視頻中建議開征健康稅。她認為,這樣做更加合理更加科學,能夠惠及更多的人,尤其是因為有能力的人應該幫助沒有能力的弱者。

李玲所說的“健康稅”,指的主要是居民醫保個人繳費模式應改革為按個人收入水平來繳納費用,并且在此基礎上由自愿繳納改為強制繳納。李玲稱,現在中國大約十億人繳納居民醫保,在財政補助和個人繳費方面實行的是完全平均主義。平均主義不等同于公平,相比于高收入人群,這樣的繳費方式對低收入人群而言是不公平的。而醫療保障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公平。她說,未來無論城鎮、農村居民還是職工、非職工,可以完全按個人收入來征收一定比例的健康稅或健康費,這樣才是一個公平的制度,才能真正縮小所謂的醫保待遇城鄉差距。
這番表態贏得了很多掌聲。
那么,開征健康稅,真的對中低收入人群有利嗎?真的能夠帶來醫療保障上的公平嗎?
以公平名義,反而增加了中等收入群體負擔
眾所周知,中國當前的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大體上分為兩大板塊:職工醫保與居民醫保。前者覆蓋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及退休人員,而后者則主要面向城鄉居民,其中占多數的是農村居民。居民醫保參保人數遠遠超過職工醫保參保人數。根據國家醫保局發布的《2023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23年底,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133389萬人,其中職工醫保參保37095萬人,居民醫保參保人數為96294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參保人數與前一年相比減少了2055萬,而且這種下降趨勢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了。
李玲稱,這是居民醫保目前采取的完全平均主義的“個人繳納+財政補助”的不公平的籌資方式所致。因為不同區域的居民經濟收入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對于經濟條件不那么好的家庭,一年兩三千元的居民醫保繳費是一筆很大的支出,這會降低他們的繳費積極性。
但是,李玲自己在這里恰恰陷入了“平均主義”陷阱,她沒有考慮到任何一個家庭都是有結構的。居民醫保參保人數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逆向選擇的一個結果。
青少年和老年人更容易遭受傷病困擾,醫療費用支出相對較高,部分家庭出于經濟考慮,可能會決定只給沒有收入的小孩和老人購買醫保,而有一定收入的年輕人卻會選擇不參保。
為了便于說明,假設有這樣一個比較典型的收入不高的農村家庭,共有6口人:夫婦二人、他們的父母二人,再加上他們的子女二人。按照當前的居民醫保繳費標準,6人每年的參保費用為2400元左右。
如果按照李玲的建議,對有收入的父母開征健康稅,同時沒有收入的孩子和老人都不用繳費,又會怎么樣?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字,2023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691元。由于平均數會掩蓋很多問題,我們來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2023年這個數字為18748元,按此計算,這個有6名成員的農村家庭的收入大約為11萬元。由于前面假設這個家庭“收入不高”,不妨再打個5折,即假設該家庭年收入為5.5萬元。

這樣一來,這個家庭需要繳納的健康稅是多少呢?李玲的建議,“把居民醫保、職工醫保打通”,以健康稅形式統一收繳。當前職工醫保個人和單位的繳費比例分別為個人工資的 2%和10%,城鎮靈活就業人員的醫保繳費比例一般為8%至11%。
很容易計算,這個家庭需要繳納的健康稅應該在每年6000元左右,一般來說肯定不會少于5000元。
由此可見,開征健康稅會使這個家庭的醫保負擔比當前水平加重一倍以上。這個例子的假設也許不盡合理,計算過程也可能有不少漏洞,但是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啟示。
李玲在視頻中還說,現在即便是80歲以上的無收入老人,也必須繳費才能享受醫保待遇,這太不公平了!但是這個問題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已經基本得到解決了,因為各個地方政府都出臺了對困難群眾參加居民醫保個人繳費部分給予分類資助的政策,例如,以山東省而言,2023年,醫療救助共資助了188.8萬名困難群眾參加居民醫保。
其實,稍加分析可知,健康稅劍鋒所指,在很大程度上是兩億多“靈活就業人員”。
正式的職工,現在已經按工資比例交了(個人加單位10%左右),基本上不受影響,也無法籌集更多資金。而靈活就業人員,本來可以參加城鄉醫保,一個人每年只需交幾百元就可以了,但如果交“健康稅”,那么按收入一定比例,每個月至少要交幾百元(因為沒有單位給他交)。
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對這個群體磨刀霍霍,于心何忍?
講大道理容易,政策制定不能想當然

李玲稱,醫保制度的目標之一就是公平。而公平不應該是平均主義,而是有能力的人群幫助收入水平低的人群、健康的人群幫助生病的人群,年輕的人群幫助老年的人群。采取根據個人收入情況來繳費的模式,就跟征收稅收一樣,實現在收入方面相對公平,支出方面每人得到的醫保報銷比例一樣,這才是真正的均等化。
類似這樣的大道理,聽上去似乎很能說服人。
但是,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開征健康稅真的能縮小城鄉醫保待遇差距、促進公平嗎?
這里涉及醫保的逆向補貼問題。從根本上說,醫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種互助、共濟的制度安排。大部分人繳納的醫保其實是一時半會用不著的,但是可以通過這種途徑去幫助極少數患重大疾病的人。這種互助式保險天然很難避免逆向選擇和逆向補貼。逆向選擇很容易理解,即健康的人傾向于不投保,多病的人更愿意投保。
逆向補貼是指收入較低的人、獲得醫療服務較少的人,為收入較高、獲得醫療服務較多的人提供補貼。不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設一個窮人和一個富人得了同一種很嚴重的病,要一百萬才能治好,報銷比例為80%,那么這個窮人因為承擔不起需要自費的那二十萬,可能決定不去治病。這樣能夠享受醫保報銷好處的就只有那個富人了,而那個富人報銷到手的錢當中,有一部分正是這個窮人交的。
逆向補貼還會發生在地區之間。當規定醫保統籌區內部的所有地方都執行統一的報銷比例時,醫療資源豐富的地區能夠得到的實際報銷額和實際待遇水平、可能遠遠高于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而且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同時也是醫保基金收入較低的地區,從而出現醫保基金收入低、醫療資源少的地區為醫保基金收入高、醫療資源豐富的地區提供逆向補貼的情況。
從逆向補貼這個角度來看健康稅,就會發現它可能很難兌現減少城鄉醫保差距、促進公平的承諾。
上面的分析實際上已經表明,開征健康稅的實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以強制的方式,讓兩億多“靈活就業人員”多繳納一些醫保費用,從而一方面增加醫保基金收入,另一方面幫助地方政府卸下為醫保提供補貼的(至少一部分)財政負擔。更重要的是,給定當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的現實條件,在邊際上看,開征健康稅很可能會導致這樣一個后果:讓兩億多“靈活就業人員”出錢,提高城市收入較高的群體的醫保待遇,而農村的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醫保待遇在相對意義上反而可能eGU2zJNz0QM46aRT/wG5rQ==會下降,從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這里的機制不難理解:農村的老人,由于沒有什么收入、所在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再加上看病不便(如路途遙遠、“去城里連方向都轉不過來”等),接受醫療服務的機會比城里人(尤其是退休或離休的城里人)要少得多,因此他們實際能夠享受到的醫保待遇,相對來說也就比城里人少得多。
事實上這也就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從農村到城里“靈活就業”的年輕人所要繳納的健康稅,將會更多地用在城市人身上,而不是自己年老的父母身上。用上面舉的那個假想的家庭來說,就是夫婦二人多交的那些醫保費用,相對來說將更多地用于提高城里人(尤其是退休或離休的城里人)的醫保待遇,而不是用于提高自己的父母子女的醫保待遇。這似乎很難說促進了公平。
對此,雖然一時無法從現有的統計數據中找到直接的證據,但是間接的證據還是不難找到的。
《2023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3年職工參保人員待遇享受人次達25.3億人次,居民醫保參保人員享受待遇26.1億人次。
另外,住院率和住院費用的對比也提供了間接證據。2023年,職工醫保參保人員住院率21.86%,其中在職職工住院率為11.93%,退休人員住院率為49.02%。次均住院費用為12175元,次均住院床日9.8天。相比之下,居民醫保參保人員住院率為20.7%,次均住院費用7674元,次均住院床日8.8天。注意到居民醫保參保人數幾乎是職工醫保的3倍,同時居民醫保參保人員中農村居民占到了多數,上面這些數字無疑可以說明不少問題。
而且,這種實質不公平還可能因為醫保控費而進一步惡化。例如,醫保控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藥品、藥械的集中采購,而集中采購的一個后果是許多高效藥物不再進入醫保或者只在部分大城市的大醫院可以獲得,那么農村居民將可能會面臨更加不公平的處境。
最后順便再提兩點。
首先,將自愿繳納的醫保費用改為強制性的稅收,必須慎之又慎,因為這意味著個人選擇權的極大壓縮,而個人選擇權的縮小,不可能沒有其他后果。
其次,“健康稅”這個提法本身,也可能是不太恰當的。因為在經濟理論和公共政策領域,健康稅這個術語向來有其明確的含義,指的是適用于煙草、酒精和含糖飲料等有可能危害健康的產品的消費稅。
在討論要不要通過稅收途徑來籌集醫保基金時,直接用“醫保稅”可能都要比用“健康稅”合適得多。但是,也許健康稅更能吸引眼球吧。(來源:鳳凰網)
責任編輯/張元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