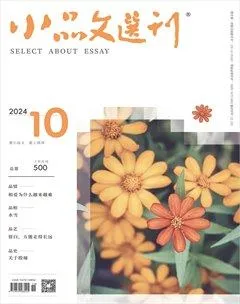你莫擔心
天氣如此之好。
陽光暖,春風軟,田地里這一處那一處,是忙著春耕的人。小孩子們在田埂上追逐,后面跟著小土狗,池塘邊傳來捶衣服的梆梆聲,還有沿著垸路“紅糖啊——藕啊——”的叫賣聲。
可是,我沒有精神去享受這些,頭昏昏沉沉,眼睛也疼,我知道我又一次感冒了。每到陽春季節,感冒如影隨形。氣溫忽高忽低,身體適應不過來。我去樓上睡了個午覺。母親在樓下叫我起來吃午飯時,我一起身,便知道感冒有所加重。我太熟悉自己的身體了,熬過白天,晚上只要睡一覺,第二天就沒事了。每次都是如此。
白米粥,包菜雞蛋炒面,腌制的蘿卜干。我吃飯時,沒讓母親看出我的不舒服。我也不想讓她知道我不舒服。土已經挑完了,地也掃干凈了,連午飯都做好了。我一點忙都沒幫上。其實沒有胃口,但還是強忍著吃完。母親看我一眼,問:“菜咸了?”我忙說沒有。從小到大,只要有一丁點不舒服,我就跟母親說。眼睛疼,頭好痛,腳崴了,脖子難受……總是想求得她的關注,而她每一次都好擔心地看顧我。可是現在,我不能再如此了。我已經這么大了,在外面闖蕩這么多年,事情都會自己處理好,不能再依賴別人,哪怕這人是母親。不能再讓她擔心了。但擔心是沒完沒了的,不是嗎?哪怕是在外地時打電話回家,我剛一開口,她都能立馬察覺出來:“你不舒服?”盡管我認為自己偽裝得夠好,但她還是能憑直覺感受到。
一下午怎么都不舒服。看不進去書,寫不成東西,坐著難受,又睡下;再次起來時,還是難受。到了下午三點,實在忍不住,蹲在屋門前嘔吐起來。母親忙跑過來,問怎么回事。我嘔得連眼淚都出來了。嘔吐完了,我說沒事。我知道沒事的,一般只要嘔吐完,人就會清爽很多;但是不舒服的感覺還在。母親說:“去衛生所看看吧。”我說沒事,只要晚上睡一覺就好了。母親轉身離開,過一會兒,拿一杯熱水和一塊冰糖給我。我接過來,讓她去忙。她又問:“真沒事?”我說:“真沒事,你快去忙。”那時,我其實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母親沒有走開,她坐在一邊守著我。我不愿意她看著我,起身往樓上去了。母親問:“我去給你買藥,要得啵?”我說:“普通感冒,莫擔心。”
母親沒有跟上來,我松了一口氣,在房間里坐著發呆,精神懨懨的,變得分外傷感。我感覺與這個世界所有的關系都斷掉了,那些讓人振奮的、開心的事情都索然無味,一股自艾自憐的情緒涌上來。為了不讓自己太過消沉,便到陽臺上走動。垸里生氣勃勃,四處都是人聲,而我隔絕在外。來來回回,走動了幾次,一轉身,母親站在門口。我想勉強笑笑,笑不出來。母親問:“是不是上午挖土,你出汗受寒凉,才感冒了?”我說沒有。過一會兒,母親又問:“是不是中午吃的菜太咸了?”我又說沒有。我知道母親在自責,她總覺得我的不舒服是她引起的。
這種自責,我太熟悉了。我說話大舌頭,她一直覺得是因為她沒有帶我去醫院好好治療。我小時候很瘦弱,她認為是她沒有讓我多多吃肉。我一邊耳朵因為患中耳炎聾了,她也自責得不行,因為那時候她跟父親在外種地……這一次,她又是這樣。我走到這邊,她跟著看到這邊;我走到那邊,她跟著看到那邊。我說:“我真沒得事,就是一個普通感冒而已。”她“嗯”了一聲,眼睛并沒有挪開。我甚至有點惱火起來,說:“我昨天就有點感冒了,跟你沒有關系。天氣原因,不是你的原因。”我不知道母親有沒有聽進去。
晚飯我沒有吃,一聞到飯菜味,就想嘔吐。父親從外面回來了,一聽說我病了,趕緊爬上樓,問我怎么樣。我說:“我不說話了哈,我沒有氣力說話的。”父親點頭,陪我坐了一會兒。母親又上樓,買了一盒桑菊感冒顆粒,讓我喝了一包。他們站在房間里,讓我深感壓抑。我沒奈何地再次強調:“我沒發燒,也不咳嗽,就是一個普通的感冒。你們莫擔心。”我連連催他們下樓,我要睡覺了。他們這才說好,慢慢起身往門外走。母親轉頭說:“你要么子,就喊我。”我說曉得。聽到他們下樓的聲音,我忽然有點哽咽起來。
晚上八點半,我就睡下了。一關燈,對面屋里亮著的燈光涌上來。這個時候睡覺,真算是早的了,連父母親都應該是在樓下看電視。到了九點多,房門開了,母親走進來,為了避免打擾我睡覺,她沒開燈。我沒有動彈,以免她又要問我。我聽到她走到桌邊拿起開水瓶的聲音,又聽到她關窗戶的聲音,然后是關上房門下樓的聲音。睡到凌晨三點半,我醒了過來,身體好多了,果然睡一覺就好是不會錯的。隔壁房屋的燈都滅了,人們都睡著了。到了四點半,房門又一次開了,還是母親。我依舊裝作睡著,她伸手碰碰我的額頭,又掖了掖被子,半晌沒有了動靜,我知道她在凝視我。我呼吸平穩,裝作睡得很沉的樣子。她轉身離開了,再次關上房門。我這才敢翻轉身,睜開眼,此時月光灑到床畔,窗外蛙聲陣陣。明天又會是一個好天氣。
選自《暫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