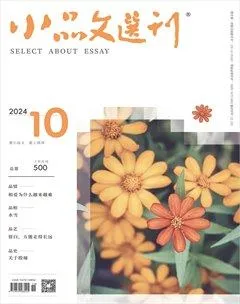文人與竹
竹子修長挺拔,四季常青,凌霜傲雪,與梅、蘭、菊并稱“花中四君子”,與松、梅并稱為“歲寒三友”。從古至今,竹子都是人們喜愛的植物,除了實用價值外,它也是文人墨客常常吟誦或揮毫潑墨的對象,還是高雅君子、剛直人士的偶像和象征。
在《詩經(jīng)·淇奧》中,記載了淇水邊的綠竹:“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在詩中我們不僅看到綠竹是多么修長茂盛,多么蔥蘢,全詩還以綠竹起興,極力贊美衛(wèi)國君王衛(wèi)武公頎長的身材、虛心有節(jié)的品行。《毛詩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在《詩經(jīng)·竹竿》中,許穆夫人的詩句“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也說明了人們使用竹子的悠久歷史。
古代文人墨客尤為愛竹。魏晉時期,世稱“竹林七賢”的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等人,迫于社會動蕩時的統(tǒng)治,崇尚老莊哲學的他們,遁隱清靜的竹林,尋求精神寄托,與竹為伴,寓情于竹,飲酒放歌,放飛自我,不同流俗,成為當時文人的代表,對后世文人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世說新語·任誕》曾記載,東晉時期名士、書圣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字子猷),暫時借住別人的空房,隨即叫家人種竹子。有人問:“暫住何煩爾?”王子猷指著竹子說:“何可一日無此君?”蘇東坡借此典故,在與友人游綠筠軒時,寫下了詩作:“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yī)。”富含哲理和情韻地寫出了物質與精神、美德與美食在比較中的價值。愛竹之情,溢于言表。
白居易不僅愛竹,還在散文《養(yǎng)竹記》中從四個方面概括了竹子的高尚品格:根穩(wěn)固,秉性直,心空虛,節(jié)堅定。進而以竹喻賢人,君子看見竹子穩(wěn)固的根,就要想到培植好堅定不移的品格;看見竹子秉性直,就要想到剛正不阿,淡泊明志;看見竹竿中空,就要想到謙虛,虛懷若谷,虛心接受一切有用的東西;看見竹子的節(jié),就要想到高風亮節(jié),意志堅強,面對任何困難都不屈服。他在《題李次云窗竹》中云:“不用裁為鳴鳳管,不須截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紛紛雪里看。”在這里,詩人看重的不是竹子的實用性,而是托竹寓意,從竹子身披皚皚白雪依然青翠的自然景象,引申出竹子昂揚絕俗、高潔孤傲、堅貞不屈的品格,從而表達了詩人對竹子的喜愛以及對竹子品格和精神的追求。
清代書畫家、文學家鄭板橋,更是對竹子情有獨鐘。據(jù)《清代學者像傳》記載,他的一生中,三分之二的歲月都在為竹傳神寫影。他在詩中寫道:“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他曾說:“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于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他通過對竹子長期細致入微的觀察,將自然實景的“眼中之竹”化為藝術構思的“胸中之竹”,然后再將“胸中之竹”畫于紙上,定型為創(chuàng)作完成的“手中之竹”,把自然現(xiàn)象與藝術想象有機地融為了一體,創(chuàng)作出了很有代表性、寓意深刻、流傳后世、令人嘆服的佳作。
在鄭板橋的竹子畫中,竹子不單單是自然的竹子,而是融入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灑脫豁達、高風亮節(jié)、堅貞正直的精神內涵。《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題畫詩云:“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板橋先生托物言志,由竹葉蕭蕭作響而聯(lián)想到民間的疾苦,拳拳愛民之情,令人贊嘆。當他“以為民請賑忤大吏而去官”時,畫了一枝瘦竹,并題《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詩一首,詩云:“烏紗擲去不為官,囊囊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竹漁竿。”借一枝瘦竹抒發(fā)了他剛正不阿、棄官為民、兩袖清風、淡泊名利及不與污濁的官場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在《竹石圖》中,幾株瘦勁的竹子,從山崖石縫中挺拔而立,迎風不倒,堅強不屈,題詩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充分表達了他勇敢面對現(xiàn)實,絕不屈服于任何艱難挫折的壯志豪情。在其他有關竹子的詩畫中,板橋先生也借竹抒發(fā)了自己豪邁曠達的胸臆。
選自《燕趙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