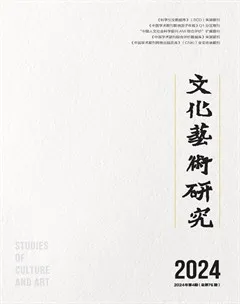戲劇如何成為事件
摘要:謝克納的環境戲劇實踐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探討并重置了戲劇的根基,把戲劇模仿論轉到他所說的戲劇交易論的方向上。他認為戲劇是如游戲、儀式、運動一樣的人類基本活動,它發生在表演者中間、觀眾成員之間、表演者與觀眾之間、演出的各個組成部分中間、演出組成部分與表演者之間、演出組成部分與觀看者之間、整個演出與舉行演出的空間之間,并以一套或明或隱的規則來規范這一活動的順利進行。謝克納進而認為作為現實活動的戲劇起到了在人類社會溝通真實的自然世界與情感、希望、幻覺、夢想等精神性沖動的作用,通過創造出一個“過渡客體”,它現實性地處理著人類社會中性與暴力等種種困境。
關鍵詞:環境戲劇;事件;博弈;過渡客體;謝克納
中圖分類號:J8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3180(2024)04-0033-09
從1967 年表演劇團成立到1980 年徹底離開表演劇團,謝克納導演了《狄奧尼索斯在69 年》《麥克白》《公社》《罪惡的牙齒》《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瑪麗蓮計劃》《俄底浦斯》《警察》《陽臺》等作品,進行著環境戲劇的試驗。除劇場導演外,謝克納還是一個戲劇理論家。對他來說,實踐與理論總是緊密相連,理論指導著實踐,實踐發展并修正著理論。要對謝克納的環境戲劇實踐作深入的了解,就必須要理解其環境戲劇理論。
《環境戲劇的六項原則》是謝克納環境戲劇實踐的宣言,在此他提出了環境戲劇的六項原則:1. 戲劇活動是一整套相關聯的交易(transaction);2. 所有的空間既為表演者運用,也為觀眾運用;3. 戲劇事件可以發生在整體轉換的空間,也可以發生在“發現”的空間;4. 焦點靈活多變;5. 所有的元素都用自己的語言說話;6. 文本既不是創作的起點也不是創作的目標,甚至可以根本不需要文本。[1]157-180可以看到,第一項原則是根本性的,后面的這些原則可以說是它的進一步展開。
戲劇活動是一整套相關聯的交易的提出,意在打破藝術與生活的區隔,將戲劇演繹為現實發生的事件,這是對傳統戲劇理論的一個顛覆。謝克納不僅發出了這個革命性的宣言,還建構了其理論的基本框架。
謝克納的這一宣言受儀式表演和儀式理論啟發頗多。在《現實性》一文的開頭,謝克納敘述了澳洲北部的Tiwi 人對通奸者的懲罰儀式。在一個有較多人參加的集會中,老人全身涂白指控年輕的通奸者,并要求一場決斗。在眾人的見證下,決斗在一個眾人圍成的橢圓形場地中進行,老人站在一頭,年輕男子赤身裸體地站在另一頭。老人先是數落和辱罵年輕人的不忠,年輕人則一般保持沉默。然后老人將手中的梭鏢投擲向年輕的通奸者,年輕男子則只能跳閃躲避,不能回擊。在此過程中,年輕人不能完全躲避投來的梭鏢,最后一般都會全身沾血,但受傷不會太重,因為老人從這么遠的距離投來的梭鏢通常都是強弩之末。如果他回擊了老人的數落或者躲避了太多投來的梭鏢,旁觀的其他老人就會加入進來,共同對年輕人發起攻擊,甚至最后將他放逐出去。這個儀式是維持Tiwi 人社會以老年人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的一個表演。表演中年輕人的逆來順受表示他對這一規則的接受,旁觀者的參與則是這一規則有效性的見證。
我們可以從四個層面來解讀這個儀式:首先,作為當事人的老人和年輕人以及作為集體成員的其他人共同認可這一懲罰儀式的有效性,將一塊空地轉換成一個表演的空間,并且自愿扮演各自的角色;其次,這是一種現實性的活動,實實在在地發生著,老人、年輕人及其圍觀的觀眾都現實在場并且共同推動著事件的發生發展;再次,現實發生的這一事件遵循著一個約定俗成或按照契約規定的規則,這一規則規范著它的表達方式和能夠抵達的邊界,保證這一活動能夠順利進行。如果老人或年輕人有一方在這個活動中違反了規則,旁觀者就會介入并把活動導向正確的軌道;最后,這一儀式是對現實通奸事件中老人和年輕人沖突的自反性呈現,現實通奸事件被帶入到當下的情境,被整個群落反思和評判,它對整個群落的生存起到了調節作用。
因此,在Tiwi 人的這個儀式中,有兩重辯證關系在交織著:事件與規則、事件與調節。而當事人、參與者對這一交易的共同認可則確保了事件的有效性。謝克納的戲劇理論正是從這兩重的辯證關系中開辟著自己的方向。
一、作為事件的戲劇
西方戲劇史上關于戲劇的本性有著種種的說法:布倫退爾的“自覺意志”說、阿契爾的“危機”說、貝克的“動作”“感情”說及“情境”說等,但正如顧仲彝在討論了種種觀點之后所說:“‘沒有沖突就沒有戲’這句中外一致的口頭語,確是表現戲劇特性或基本規律的顛撲不破的普遍真理。”[2]對戲劇與沖突的這種天然關聯,謝克納也同樣認同,他說:“戲中沒有沖突,就沒有眼淚。戲劇是從沖突的觀點理解生活的一種方式。”[3]107
但是,謝克納對戲劇與沖突密切相關的認同與西方傳統戲劇理論有著根本性的區別。西方傳統戲劇理論中的沖突論以戲劇文學為中心,認為戲劇必須構設一個圍繞沖突展開的完整行為,然后通過演員的忠實表演將這一完整行為連貫地呈現出來。這種以戲劇文學為中心的沖突論又進一步與模仿論關聯著,認為這一完整行為是對現實生活的模仿。謝克納的環境戲劇要顛覆的就是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模仿論及以戲劇文學為中心的西方戲劇理論傳統。我們知道,柏拉圖認為藝術是對現實世界中事物的模仿,而現實世界中事物則是對先驗世界的模仿,因此它是影子的影子,與真理有著兩重隔膜。亞里士多德改造了柏拉圖的模仿論,認為藝術是對現實生活的模仿,但同時它具有自身存在的獨立性和完整性,這是對柏拉圖貶斥藝術觀念的一個翻轉。謝克納認為這一翻轉并沒有走出模仿的邊界,因為模仿就必然意味著藝術來自于生活,它總是在生活之后因而低于生活,同時它也把藝術與生活分裂了開來。他認為戲劇與人類社會的其他活動如游戲、儀式、運動一樣,都是人類活動的基本形式,不存在誰先誰后誰主誰次的問題。
戲劇是現實發生的事件,這是謝克納對20 世紀以來包括先鋒戲劇在內的先鋒藝術理論和實踐的接續。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格洛托夫斯基提出了質樸戲劇的理念,認為表演者與觀眾的互動才是戲劇的核心,而在這兩者中表演者又是重中之重。在他的領導下,波蘭表演藝術研究所實際上成為了演員身心訓練的實驗場。格洛托夫斯基對謝克納的影響很大,謝克納的很多演員訓練方法取法于他,不僅如此,謝克納也由此認識到了工作坊- 排練的關鍵性,在這里,表演者得以專注地進行身心訓練并通過集體的努力創作出作品。工作坊- 排練不再像傳統的戲劇排練那樣只是將劇本具身化,而是獲得了與演出一樣的地位,成為了戲劇存在的理由之一。也就是說,戲劇不僅僅是為觀眾而存在,同時也是為表演者而存在,是表演者個體或集體身心的修煉所。
在將演出轉化成事件上,謝克納則受到約翰·凱奇、卡普羅等人的行為藝術的啟發。約翰·凱奇是美國的作曲家,同時還是先鋒派復興的鼓吹者、美食烹飪師、社會評論家、菌類專家。早在20世紀50 年代,其作品《事件》《塊、件》便推動了音樂行為表演藝術,致力于將藝術與生活關聯起來。1965 年謝克納在《戲劇評論》上開辟了“機遇劇”專號,其中有他與柯爾比對凱奇做的一個訪談。當謝克納問及戲劇結構方面的問題時,凱奇說:“我們應該考慮的結構是觀眾席中每一個人的結構。換句話說,他的意識正在結構著體驗,這種體驗與觀眾席中其他人都不一樣。如果我們結構的戲劇性場合越少,那么非結構的日常生活就越多,對于觀眾席中每一個人的結構能力的刺激也將越大。如果我們什么也不做,那么他將什么都可以做。”[4]凱奇創作的著名樂曲《4 分33 秒》可謂這一段話的注腳。樂曲的演奏過程是:鋼琴家坐到鋼琴前,打開琴蓋,默坐4 分33 秒,然后起身,向觀眾鞠躬致意。鋼琴家沒有演奏任何意義上的傳統樂曲,目的卻是要讓觀眾去注意和發現周邊的各種各樣的聲音并結構著屬于自己的聲音世界。凱奇的藝術理念受禪宗和老莊思想影響很深,其上述主張和樂曲《4 分33秒》會讓我們自然而然地聯系到老子的“大音希聲”“五音令人耳聾”等警示以及禪宗公案的作用方式。“如果我們什么也不做,那么他將什么都可以做”不就是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一個回聲嗎?為踐行這種“無為”,凱奇在作曲上還經常采用一種隨機操作的方式。比如在大型音樂作品《音樂的變化》中,他通過擲硬幣的方式隨機獲得《易經》的卦象,然后用這些數字來決定音高、時長、力度變化和其他方面的音符特點,其目的是創作不受個人偏好和品位影響的音樂。這種將作曲的焦點轉移到以觀眾為中心的特點以及隨機操作的創作方式影響了謝克納,他說:“從理論上我接受它,但這還不夠——總之,作為一個‘戲劇人’,我不希望‘什么也不做’。卡普羅對于凱奇觀念的運用和改造更接近于我的需要。”[3]74 顯然,謝克納接受了凱奇對表演中觀眾地位的探索,但并不太熱衷于“無”或者說自在自為的觀眾存在方式,他傾向于有所為,只不過這種有所為與傳統戲劇所為的方式差別甚大,其觀念受卡普羅的機遇劇影響極大。
卡普羅在20 世紀50 年代開始探索突破傳統繪畫邊框的限制,將繪畫蔓延到周遭的環境中,并逐漸發展出了機遇劇的表演形態。卡普羅在新社會研究院曾師從約翰·凱奇,并把精心制作的《分為六個部分的18 個偶發事件》(18 Happenings in Six Parts)搬上舞臺。卡普羅的這一作品受到了凱奇的影響,但與其師不同的是,卡普羅堅持讓觀眾在特定的時間按照特定的方式表現自己。觀眾在畫廊里看到的是用木條和半透明的塑料薄膜所分割成的三個小房間和一條走廊,在每個房間中都有顏色各異、明暗不等的照明光源和各類招貼,還有椅子供觀眾休息。因為每個房間被分為兩部分,而每個部分又安排了三次活動,所以加起來稱作“6 個部分中的18 個偶發事件”。卡普羅把每次將要發生的事情寫在卡片上,分發給觀眾,指導他們在一定的時間內依次參與不同房間的不同活動。這是卡普羅劇場形態的機遇劇,觀眾的參與過程只限于簡單的互動。卡普羅還創作過“活動型態”[5]的機遇劇,這里沒有觀眾/ 演員的區分,而是由一群參與者共同執行某個計劃。比如1967 年10 月在洛杉磯上演的作品《流體》,在洛杉磯的十五個地方同時興建用冰塊砌成的墻體,每個地方的工作由十到十五個人完成,整個活動歷時三天。
在汲取這些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謝克納描述了戲劇作為一項現實性活動的基本形態:“1. 過程性的,此時此刻一些事情當場發生了;2. 重要的、無可補救的、不可挽回的行為、交換或者情狀;3. 對賽,對表演者甚至常常包括觀看者來說一些事情瀕于險境;4. 加入,參與者地位的改變;5. 具體和有機的空間利用。”[6]46 也就是說,戲劇應當成為具體、有機空間中現實進行著的活動,參與者特別是其中的表演者圍繞著某些事情進行著真實的博弈,產生現實的后果。因此,這種現實性的活動賦予了沖突以新的表現形態和呈現方式,它真實地發生在所有參與者之間,或者說所有參與者之間的現實性沖突構成了戲劇的基本內容,而不是如正統戲劇那樣只是發生在一個模擬性的封閉的舞臺空間中。
二、在事件與規則辯證關系中的博弈
戲劇是在所有參與者之間發生的現實性沖突,就如任何現實事件一樣,這些沖突也都是在一定的規則之下進行的。借助于戈夫曼、艾瑞克·伯恩等人的博弈理論,謝克納明確了作為現實性活動的戲劇與規則之間的辯證關系。
在《環境戲劇的六項原則》中,謝克納將戲劇與日常交流關聯在了一起。他說:“戲劇事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交織物,一個期望與職責的網絡。刺激的交流——不管是感覺上的抑或是認識上的,還是兩方面都有的,都是戲劇的根基。把戲劇從更普通的交流——比如說一次簡單的談話或一個聚會脫離開,從形式上是很難做到的。”[1]158 他所謂的“期望與職責的網絡”以及將戲劇與一次簡單的談話或一個聚會聯結,顯然是在援引社會學家戈夫曼的理論。“期望與職責的網絡”的表述出自戈夫曼的《日常接觸》:“就像社會生活的其他分子一樣,日常接觸組成部分都展現了由履行了的責任和實現了的期望而產生的,得到認可的秩序。”[7]謝克納在《環境戲劇的六項原則》中引用了上述這段話并認為它“直抵戲劇事件的核心”。戈夫曼以研究微觀互動而著稱,他借用戲劇中的表演、角色、劇班等概念來描述和分析日常互動,認為當個體出現在他人面前時,往往會有許多動機,試圖控制他人對當下情境的印象,而其他人也會通過自己的回應來有效地影響這種情境定義,于是會出現運作一致、臨時妥協或破裂等種種情形。為避免出現因為情境混亂而帶來的窘迫,人們就會采取種種防衛措施、保護措施。就像人類學家格爾茨所說的,戈夫曼眼中的社會生活就是一場博弈,“或許是當今美國最受推崇,當然也是最有天分的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著作,幾乎完全建基于博弈類比之上。……將它們全體關聯起來的是這樣的觀點:人類較少地為強力所驅使,而是更多地依循規則而行,這些規則如此這般地提示了戰略,這些戰略又如此這般地推進了行動,而這些行動又如此這般地自我滿足:不為別的,只是為了運動。……將社會視為一個種種賽局的集成,意味著將之視為眾多既定習俗與適當程序的一個巨大而多元的總匯,一個緊密的、毫無罅隙的行動與反應的世界,易言之,生活就如一套規則”[8]。生活就是一套規則或秩序之下的行動和反應,這意味著行動有預期,反應可以預測,從而形成“期望與職責的網絡”。這種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是謝克納在環境戲劇正式演出中引導觀眾參與的理論依據。
在戈夫曼式的日常交際博弈之外,謝克納通過援引溝通分析精神治療的開創者——艾瑞克·伯恩的理論,將現實性沖突擴展到了無意識的層面。伯恩將人的內在經驗與涵蓋了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互動的人際行為聯系起來,從博弈的角度進行分析并建立種種模型。與數學博弈分析不一樣,溝通分析處理的是理性之外甚至非理性的活動,伯恩把博弈界定為:“游戲(game)是一系列朝著一個明確而可預測的結局進行的互補式隱蔽溝通。可以將游戲描述為一套重復發生的溝通系列,表面合理,但潛藏了內在動機;若更通俗一點地說,游戲就是一系列暗藏陷阱或‘機關’的溝通步驟。……每一個游戲基本上都是不誠實的,其結局也頗具戲劇性而不僅僅是令人激動。”[9]伯恩關注的是不知情的個體在無法完全覺察的情況下進行溝通所玩的無意識博弈,如夫妻關系中的“要不是因為你”博弈等。這類博弈是每個人的無意識生活計劃或腳本的動力性組成部分,是個體生命在死亡或圣誕老人到來之前填補時間的過程,幾乎別無選擇。博弈式的人生景象是慘淡和悲哀的,伯恩試圖要做的就是讓身在其中的人看清楚自己生活中的一場場難以自拔的博弈,超越種種形式的博弈,幸運地進入到一種自主狀態,即能夠覺察、自發和親密。伯恩的理論是謝克納環境戲劇工作坊- 排練過程中表演者自我修煉的重要理論資源。
不管是戈夫曼式的日常交流中的博弈,還是伯恩式的親密關系中無意識的博弈,它們都是在一套隱含著的規則下進行的。對于這種規則的作用方法,謝克納在1966 年的《理論/ 批評的方法》一文中進行了討論。依據規則作用的方式,他把游戲、戲劇、博弈、運動、儀式這五個類別的活動劃分為三組:游戲;戲劇、博弈、運動;儀式。游戲aed5cf4506f0ebc36bed382b4d89be6dda04f49b08156c09783eb01f7852f148由參與者自己制定規則,遵循快樂的原則,類似于弗洛伊德所說的本我;儀式遵從給定的規則,遵循現實的原則,類似于弗洛伊德所說的“超我”;戲劇與博弈、運動可歸為一類,處于游戲和儀式之間。因此,在戲劇活動中,規則以框架的形式存在,它告訴了人們哪些是可以做的,而哪些又是不能做的,但同時,參與戲劇活動的各方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這些條條框框,創造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新規則,由此戲劇中的博弈呈現出了動態的特點。
在環境戲劇的實踐中,謝克納將博弈運用到戲劇制作的方方面面,“時間、空間、活動、具體事物之間具有一整套復雜的關系。協商發生在每個層級上、每一次的交際中。層級之間以及層級之內各個子項之間的交換不但是可能的,而且還是不可或缺的。協商是藝術的真正原料,否則它就會成為對過去的固化”[1]198。他把環境戲劇中的博弈規定為組成戲劇事件的三個主要的相互作用和四個次要的相互作用,三個主要的相互作用發生在表演者中間、觀眾成員之間、表演者與觀眾之間,四個次要的相互作用發生在演出的各個組成部分中間、演出組成部分與表演者之間、演出組成部分與觀看者之間、整個演出與舉行演出的空間之間。因此,不管是在工作坊- 排練還是在面對觀眾的演出中,表演都成為了各種博弈交織的充滿能量的場域,這種博弈既有戈夫曼意義上的日常博弈,也有精神分析意義上的潛意識博弈,最終表現為遵守規則與打破規則相連續的動態過程。由此,謝克納的環境戲劇在演出中呈現出了從正統戲劇到公眾事件的連續統一體,各種形式融合在了一起。
“不純的”,生活 “純的”,藝術公眾事件,示威活動 混合媒體表演,機遇劇 環境戲劇 正統戲劇
行動、反應以及規則的規范與打破使得戲劇工作坊- 排練和正式演出演變成了一個大的社會實驗,成為了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社會變革的象征性行為。
三、作為戲劇主題的性與暴力
戲劇是現實發生的事件,是一場博弈,謝克納由此突破了西方傳統戲劇理論的窠臼,站在了一個新的理論基點上。
作為一種現實發生的活動,謝克納認為戲劇的主題是關于性和暴力的。他說:“戲劇是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因為它普遍地排它地全神貫注于性與暴力的主題。……戲劇處處并且總是趨向于爆發性、血和性。而盡管對戲劇的本性明顯有些偏袒,但人們卻不認為它是不完整的。”[3]107 謝克納還援引人類學家對部落社會狩獵- 生殖、成年禮儀、薩滿儀式等的研究來佐證其觀點。成年儀式在各種文化中普遍存在,人類學家對此做了很多的田野調查,有著豐富的文獻資料。著名的民俗學家范熱內普在其《過渡禮儀》中專辟一章討論成人禮儀,介紹了很多的成年禮儀,比如里基布韋人成人禮儀的進程如下:建起一座神圣茅屋;孩子被系捆在一塊木板上,在整個儀式過程中,他猶如失去了全部個性;參與者盛裝、涂色等;列隊進入茅屋;酋長—巫師—神父將所有參與者殺死,再使他們一個個再生;列隊、屠殺和再生是在儀式的每一重要階段之后;孩子的父親在男女支持者陪伴下將孩子獻給酋長,然后與同伴跳舞。此儀式延至中午。下午,祭臺祭品擺在茅屋中央。上面是一塊布蓋著樹枝,參與者繞行一圈、兩圈、五圈,直至每人用嘴將涂色貝殼放在祭品上,并將布蓋住。之后,大家再繞行,一個個將貝殼拾起。這樣的貝殼便具有神圣性,可做有效力的“藥”。每人再擊打圣鼓,唱首祈禱歌,男人們都抽煙(一種儀禮行為)。傍晚,酋長和神父接受孩子父親贈送的禮物,并回贈“藥”和咒符等。孩子的祖父當眾祈求“神靈(Kitschimanitou)之恩典”;所有人一起吃玉米粥,包括孩子們。在此儀式過程中,受禮的孩子得到一個新名。謝克納認為成年儀式是“某些最為殘酷最為夸張的青春期想象的扮演活動。男孩被綁架、肢體懲罰、挨餓、活埋、辱罵、傷害、全面折磨。儀式的高潮常常是割除包皮或剖腹術或其它疼痛的留下永恒疤痕的人體標記。然后男孩們穿戴起武士裝飾,完全成熟的男人服飾,聚集在整個公社包括婦女前面,開始跳舞。狠褻的鬧劇跟嚴肅的儀式緊密聯在一起”[3]109-110。也就是說,成年禮儀是青春期想象的再現實化。
在將性與暴力當作戲劇主題上,環境戲劇與傳統西方戲劇并沒有什么不同,差別在于傳統西方戲劇主要在故事層面對這些主題進行處理,而環境戲劇則將它直接引入到工作坊- 排練以及演出中,在現實活動中直面性與暴力。
在基本的身體練習之外,謝克納的工作坊- 排練有大量關于性與暴力的博弈。謝克納在《環境戲劇》一書中專列一章談裸體,其中敘述了“展露”“動物”“選擇1”“選擇2”“組合”“迷舞”“真實接觸練習”“衣服”等關于裸體的練習,這些練習的目的是:“幫助人們了解他們具有關于他們自身人體的想象力;他們能夠想象出他們自身的人體以及作為客體的其他人的人體。對于這些態度是沒有‘療法’的,它們是人的狀態的一部分。”[3]103 在這些直接處理與身體相關的專門練習之外,工作坊中的練習更多的是處理性的幻覺、想象。謝克納在紐約的第一個工作坊就做了一個被稱作“撫慰”的練習:一男一女搭檔,一個站著不動,另一個則邊撫摸邊嗅著對方的身體,然后輪換。表演劇團成員之一的山姆·謝潑德選擇了瓊·麥金托什這個第一眼就吸引他的女人作為搭檔。在做這個選擇時,他就隱約感到這個女人與謝克納有著不一般的關系。工作坊演出結束后這一直覺或者說擔心得到了證實,瓊·麥金托什正是謝克納的女友。多年之后,謝潑德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分析了那時自己與謝克納、瓊·麥金托什的這種三角聯系,謝克納被投射成了父親的角色,而瓊·麥金托什則被投射成了母親和情人的合體。這種幻覺、想象在工作坊過程中會被展示出來甚至被結合到其演出總譜中去。在整個工作坊- 訓練中,這種包含有性幻覺、想象的練習比比皆是。謝克納認為青春期想象是戲劇的原型之一,因此工作坊的很多練習與此相關也就不足為奇。
謝克納工作坊- 排練的一個目的是表演者之間學會信任、分享并最終建立共同體,而信任、分享有它侵犯和暴力的一面,把侵犯和暴力展示出來是達到信任、分享的必然內容,一些練習如“滾動”等處理的就是這類問題。除此之外,直接與暴力主題相關的是激發侵犯的練習。在一次探索空間的練習中,謝潑德找到了一架沉重的梯子,并把它拖回去建造“城市”,途中特里上前來搶奪,這本來是練習所允許的一個游戲環節,謝潑德卻有些過于較真,用梯子敲擊了特里,這一意外打斷了整個練習并引發了劇團的討論。這一事件之后,謝克納發展了“儀式格斗”“對視控制”等練習來激發并處理暴力的主題。
在工作坊- 排練過程中,一段劇情或一個腳本會被引入,以發展出一個完整的演出總譜。我們看到,謝克納所引入的劇情或腳本及其發展出來的演出總譜集中于性和暴力的主題。
《狄奧尼索斯在69 年》a 根據歐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侶》(The Bacchae)改編而來,從歐里庇得斯的1300 行臺詞中選了600 行,此外還引用了《安提戈涅》和《希波呂托斯》中的一些臺詞。全劇圍繞狄奧尼索斯與彭透斯的沖突來進行,彭透斯是特拜城的國王,代表著權威,狄奧尼索斯則是神,代表著對權威的威脅。特拜城是狄奧尼索斯的出生地,但其神性在此遭到否定。于是,他來到特拜城擴展他的影響,引得該地的婦女們甚至國王的祖父都對他崇拜得發狂。彭透斯非常厭惡狄奧尼索斯追隨者們的這種狂熱并明令禁止。為了根除這種崇拜,他甚至逮捕了狄奧尼索斯,但是卻沒法把他控制住。受狄奧尼索斯的誘惑,他化裝成一個女人,進入男人禁地去查看女人們瘋狂的慶祝儀式。女人們發現了他,并在他母親的帶領下在極度興奮中殺死了他,還以為是殺死了一頭野獸。之后她們舉著他的頭作為戰利品返回特拜城,直到瘋狂退去之后才發現了自己的所作所為。整個特拜城被羞恥所籠罩,狄奧尼索斯則完成了其復仇。這是一個復仇的故事,充滿了大量的暴力,特別是瘋狂的女人們撕裂彭透斯的那場戲展示了對身體的施暴。整個演出總譜被呈現為一個獻祭儀式:“《69 年的狄俄尼索斯》暗示了獻祭儀式,在獻祭儀式中,共同體只通過獻祭一只替罪羊,通過對一個個體的暴力行為而產生。……這里共同完成的行為完全是R·吉拉德(R. Girard)強調的所有的人對準一個東西(獻祭品)而發的‘凈化的’暴力所特有的。在‘撕羔羊肉行為’中,對準的是羔羊——最傳統的獻祭物和耶穌犧牲的象征。在《69 年的狄俄尼索斯》中,共同體以‘仿佛’一形式作為象征的暴力來發生影響——把彭提烏斯從一個共同體中排除出去,而這個彭提烏斯本想要控制和奴役這個共同體。”[10]在暴力主題之外,該劇也以對裸體和性的大膽呈現而著稱。演出總譜中狄奧尼索斯從四個女人胯下慢慢擠出來的“生的儀式”、迷舞、總體撫慰等段落展示著性和生殖的主題。扮演狄奧尼索斯的芬利與扮演彭透斯的謝潑德還將兩個主要人物之間的關系涂抹上了同性戀的色彩,在原有的競賽之外增加了誘惑與抗拒的曖昧色彩。《麥克白》根據莎士比亞的同名劇作改編而成,其主要的情節和主題都是在工作坊中逐步發展出來的,意在探討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問題。改編本中考特爵士、馬爾康、麥克德夫和班柯成了國王鄧肯的兒子,每個人都意圖謀害他們的父親。麥克白是外來者,但他做到了鄧肯的兒子們所沒有做到的事情——攫取了皇冠。鄧肯的兒子們聯合起來把他打敗,緊接著禍起蕭墻,一樁樁謀殺相繼發生。改編本主要由9 個段落組成:1. 鄧肯一個人獨攬大權;2. 考特爵士反叛他的父親鄧肯;3. 鄧肯、麥克白夫人同幽靈的交易;4. 麥克白、麥克德夫、馬爾康、班柯受幽靈誘惑;5. 謀殺鄧肯;6. 謀殺班柯;7.謀殺麥克白;8. 謀殺麥克德夫;9. 馬爾康實施統治。謝克納的其他作品如《公社》《政府的無政府狀態》《條子》等都對暴力、權力等主題進行了探索。
公開演出中,在演出總譜規范下,性和暴力的主題以現實發生事件的方式呈現出來,在大多數時候,其呈現為規則之下的自由游戲。規則的存在保證了界限的分明,以性的呈現為例,正如謝克納自己所說:“人體解放,嚴肅藝術和性表演之間的不同在于它們的程度。它們每一個都集中在人體:第一個是慶典,第二個是象征或隱喻的‘與客觀相關聯的東西’,第三個是商品。”[3]126 所謂的“象征或隱喻的‘與客觀相關聯的東西’”,指表演者演出中的裸體并非客觀的赤裸裸的身體,而是在與觀眾的面對中通過觀眾的反應而引發的表演者對自己身體的幻覺及其沖動的展示,類似于精神分析中的照鏡子游戲。但是,由于新人——觀眾的來到,表演者之間形成的默契面臨著新的博弈,越界時常發生,有時甚至打破原有規則制造出新的事件。
《狄奧尼索斯在69 年》有一場發生在狄奧尼索斯與彭透斯之間的競賽。在第二次會面時,扮演彭透斯的演員要到觀眾中尋找一位女人請求魚水之歡,如果這位女人答應了,這場競賽就以彭透斯的勝利而告終,演出也就結束。在公開彩排時,謝潑德扮演的彭透斯既興奮又害怕地在女性觀眾中尋找目標并提出請求,如其所愿,這個請求一一被冷淡地拒絕了,只有一位二三十歲的女性接受了他的親吻和擁抱,但當他繼續有意要粗魯地撫摸她的乳房時,她拒絕了,并一言不發地回到了觀眾席。謝潑德事后知道這個女人叫麗塔·艾麗薩,是一份激進報紙的撰稿人。麗塔后來發表了一個評論,以表達憤怒。她說:“彩排之后我的心情被理查德·謝克納弄糟了,他還有些高興地問我當時有多憤怒。憤怒?因為我不喜歡在一個房子中間接納某個男孩,還不給錢。憤怒?因為大家都明白他們知道接下來要做什么,而我卻不知道?哦,好,這個戲是要來證明些什么?是觀眾不想要那吊在線上的干癟無味的骨頭,線的另一端還被導演牢牢控制著?還是觀眾應該害羞地做出演出所要求的尷尬反應?”[11]從觀眾的角度講,麗塔的憤怒完全可以理解,而謝克納的高興則說明了他對這一效果持認可的態度。麗塔所抱怨的觀眾與表演者、導演信息不對等,也確實如此。但相對于正統戲劇,謝克納所實踐的環境戲劇對表演者甚至對導演來說,都存在著很多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在上面所說的這一演出環節中,表演者謝潑德在面對觀眾時同樣感到害怕,他也不知道究竟會發生什么。當然,表演總譜的存在可以讓表演者在面對不確定時迅速退回到安全地帶,而觀眾為規避風險也大可選擇無動于衷甚至冷面相對。然而如果雙方都這么做的CZp0WGDyCKPfs+mnYBF1cQ==話,那環境戲劇的演出就回歸到了傳統戲劇的窠臼,這也就意味著導演的失敗。《狄奧尼索斯在69 年》演出中有一個“撫慰”的場面:在狄奧尼索斯與彭透斯進入地窖之后,其他表演者就慢慢移向觀眾并隨意挑選出一些觀眾,然后與他們碰觸,逐漸過渡到深度的擁抱、撫摸,最后發展成動物式的抓撓。這個演出進行一段時間之后,表演劇團的女演員受不了了,因為常有不懷好意的觀眾趁機非禮,后來這一場面就改成了表演劇團分兩隊面向觀眾跳舞,其中一隊仍然邀請觀眾參加。相比于“撫慰”場面,后一處理顯然可控性更高,雖然謝克納本人更青睞前一種。
四、戲劇對個體或群體生態的調節
直面性與暴力并將它們展示出來,這就是環境戲劇的主要內容,謝克納認為它起到了調節人類基本交往活動的功能,“就其最深層的意義而言,劇場所‘涉及’的乃是框定和駕馭的能力、把生的轉化為熟的能力以及處理最疑難的(暴力的、危險的、性的、禁忌的)人際交往活動的能力”[6]191。借鑒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的過渡客體理論,謝克納闡述了這一調節的作用方式。
溫尼科特是一位著名的英國精神分析學家,也是一位兒科醫生。他發現嬰兒在出生幾個月后會迷戀上一些事物,比如一塊柔軟的毛毯、一塊舊的衣服、一個玩具、一塊尿布或熟悉的聲音等。父母親也知道這些事物的重要性。媽媽會允許它很臟,甚至有氣味了也不去洗它,因為她知道這樣做會損毀這個物品對嬰兒的意義。溫尼科特把這些事物稱作為“過渡性客體”,認為它是母親乳房的替代物,是嬰兒的第一個“非我”所有物,嬰兒會認為這個事物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并能夠控制它。溫尼科特認為“過渡性客體”既非完全的客觀現實,也非完全的主觀現實,而是兩者之間的一個中間區域,既是客觀現實,也是主觀創造。在“過渡客體”的基礎上,溫尼科特提出了“過渡性現象”的概念。“過渡性現象”標示出嬰兒從主觀性到客觀性,從與母親融合到與母親的分離的成長階段,是一個幻想的中間階段,即部分是主觀、部分是現實的狀態。溫尼科特說:“過渡性客體和過渡性現象都屬于基于早期經驗的幻覺的領域。這種早期狀態的形成有賴于母親對嬰兒的需要提供無條件的接納,因此使嬰兒產生了創造現實存在的幻覺。這個經驗的中間區域,就它屬于內部還是外部(共享的)的現實而言,并未引起爭議。它是嬰兒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強烈的體驗保留終生,并在藝術、信仰、生活幻想和創造性科學工作中表現出來。”[12]可以看到,溫尼科特將過渡性體驗擴展到了成人生活和整個文化領域。他認為在純主觀性的自戀和純客觀性的與世推移之間的中間領域、過渡空間是人類的游戲生活和創造性所在。如同“過渡客體”一樣,這個過渡空間既是客觀現實,也是主觀創造的。
謝克納對溫尼考特的這一理論非常感興趣,他說:“溫尼考特把戲發生的空間——一個‘轉化的空間’當作‘母親和嬰孩之間的潛在空間’。那是‘文化體驗被安置的地方’。這個地方是一個反映的地方,一個所有參與者把他們所得到的反饋回來的情境,非技巧化的,而是微妙的變化與變形。溫尼考特的觀念被諸如雷·布德惠斯特爾等人的研究所證實,布氏證實了‘對于其他人的存在和行為,人在不斷地進行自我調整’。”[3]79 也就是說,戲劇通過一種類似哈哈鏡的作用機制處理個人或群體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是創造而不是模仿。
因此,在謝克納看來,戲劇是溝通真實的自然世界與情感、希望、幻覺、夢想等精神性沖動的一項活動,通過創造出一個“過渡客體”,它現實性地處理著人類存在中的種種困境。而這也是戲劇存在的必然性所在,即戲劇是“人們以數不清的方式‘主動地’把他們的情感、希望、幻覺和夢想與自然世界的真實結合起來的一種典范。我不以一種單一的戲劇觀點,一把萬能的鑰匙為最終目的。相反我想追尋無論什么時候人們聚集時必然會產生戲劇的推動力的根源。我相信戲劇與人的狀態共同存在,而且是這種狀態的基本要素”[3]221。
總之,謝克納的環境戲劇將戲劇的根基從傳統的模仿論轉換到了交易論,將戲劇的空間打造成在一定的結構規則下各種預先準備的活動與即興活動的交集之地,因而在20 世紀先鋒戲劇理論中獨樹一幟。不僅如此,環境戲劇的理論和實踐還是謝克納走向表演詩學的先聲。在將戲劇轉換為現實發生的事件,成為與儀式、游戲、博弈、運動等相并列的人類活動之后,他繼續向前推進,去探索這些活動的共同性,從而成為表演研究的創立者之一。
參考文獻:
[1]Richard, Schechner. Public Domain: Essays on the Theatre[M].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9.
[2]顧仲彝. 編劇理論與技巧[M].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87.
[3]理查德·謝克納. 環境戲劇[M]. 曹路生,譯.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
[4]Mariellen R. Sandford, ed. Happenings and Other Acts[M]. London: Routledge,1995.46.
[5]簡立庭. 從完全藝術到活動:卡布羅的偶發藝術實踐[J]. 美術學刊,2010(1).
[6]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Theory[M]. London: Routledge,2003.
[7]Erving, Goffman.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M].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1. 18-19.
[8]格爾茨. 地方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M]. 楊德睿,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30-32.
[9]伯恩(Berne, E.). 人間游戲:人際關系心理學[M]. 劉玎,譯. 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14:49.
[10]費舍爾- 李希特. 行為表演美學:關于演出的理論[M]. 余匡復,譯.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77-78.
[11]William Hunter Shephard. The Dionysus Group[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1991.118.
[12]溫尼科特. 游戲與現實[M]. 盧林,唐海鵬,譯. 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6:18.
(責任編輯:相曉燕)
基金項目:本文系韓山師范學院校級課題“謝克納表演詩學研究”(項目編號:E21146)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