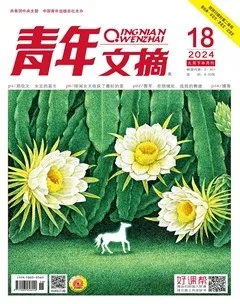每個逃離的人身后都有一雙手的支撐

每個離開家鄉的人都由兩個自己組成。在他們離開家鄉的那一天,便把過去的自己留下了。異鄉的他們又會在新的土地上長出一個全新的自己。
曾有朋友對我說:“真羨慕你,離開家那么久,父母也沒有給你壓力,任你在外面看世界。”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愣住了——我似乎從未站在父母的角度思考過這個問題。難道不是因為自己足夠堅定,足夠堅忍,才能在大城市生存下來的嗎?我也沒有想過,如果父母不在背后支持我,我是否能這么多年心安理得地待在大城市。
一
我30歲之前那些年,當一起北漂的伙伴陸續選擇回家鄉時,我不止一次問過自己到底要不要堅持下去。父母從未對我提過任何要求,也沒有任何催促。他們不問我究竟能掙到多少錢,也沒問過我未來的計劃,他們問我最多的就是:“還行吧?”我說:“還行。”他們就說:“還行就行。”
他們好像從一開始就做好了支持我遠行的準備。大學畢業時,很多同學選擇了回家鄉,我對我媽說:“我不想回郴州工作了,想留在長沙。”她說:“你喜歡就好,反正長沙離家也不遠。”
又過了一年,我跟她說:“我打算去北京工作,北京很遠,有可能我們一年只能見一兩次了。”她還是對我說:“你喜歡就好,你回不來湖南,我們就去北京看你。”
事實上,他們從未提出來北京看我,他們知道我和幾個朋友擠在一間小房子里,知道我買了一張二手的床墊睡在地上,知道我每天的生活只有兩點一線——公司和家里,也知道我每天都會加很長時間的班,他們對我唯一的交代就是:注意身體。
邊回憶邊想,哪位父母不希望能與孩子生活在一起呢?當時逃離家鄉只覺得和父母共同生活的18年太壓抑,卻不曾想到,一旦大學畢業選擇了漂泊他鄉,這輩子與父母相見的次數就開始所剩無幾了。
我曾以為自己選擇北漂是一場勝利的人生逃亡,后來才意識到,這是肩膀上與父母見一次便多落一層的霜。
二
我曾以為自己對人生的每一次選擇都快速堅定,富有主見。可頂著風往前走,光有主見是不夠的,還需要背后有足夠有力的手推著我往前。
那雙手來自我媽。
因為從小成長在醫院里,周遭的人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應該學醫,不然我爸那些醫書、那些積累無人繼承。更何況,同齡人多數都找到了各自的專長,只有我沒有任何突出的地方,只是憑著高三的最后一腔熱血和好運考了一個不錯的分數。
雖然我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但我很清楚自己討厭與醫院有關的一切。半夜家里響起急診電話鈴聲,手術臺的無影燈能照出一切膽怯,閉上眼,我的世界至今都彌漫著84消毒液的味道。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半夜驚醒,發現只剩自己一個人在家,于是跑去住院部找爸媽,路上經過有病人家屬低聲哭泣的太平間,我用力推開住院部的雙扇門,看到走廊兩邊躺滿了因為瓦斯爆炸而重度燒傷的礦工,所有醫生、護士都全副武裝,只露出雙眼在為傷者抹燒傷膏。我在驚恐中一步一步往前挪,終于看見一雙熟悉的眼睛,便走過去蹲在她的身邊,一聲不吭。
我媽看我一眼,瞬間就哭了。
我媽是個矛盾的人。她不敢殺任何家禽,卻對醫院的急救輕車熟路。她有時順從我爸,有時又固執己見。比如,明知道我爸反對我學除醫學之外的任何學科,卻帶我在最后一天坐火車趕上了中文系的報名。學費不菲,她從貼身的衣物里掏出了厚厚一沓現金,說:“火車上小偷多得很,你千萬小心。”報完名,我長舒一口氣,問她:“我爸那邊怎么辦?”她說:“沒事,我去說。”
后來我在北京工作了兩年,她問:“如果你不打算回來,我想干脆給你交個首付買個小房子,你自己還月供,這樣你也能稍微有點安全感。”我爸不同意,覺得家里所有的積蓄都給我,他們就沒法安心養老了。但我媽又背著他把錢都給我交了首付。我問她:“我爸那邊怎么辦?”她還是說:“沒事,我去說。”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寫:“28歲那年,我硬著頭皮跟我媽聊了自己對未來人生所有的規劃,這種決定對傳統父母來說一定是忤逆的。但我媽花了半小時消化完我的想法,依然對我說你好,我們就好,你爸那邊我去說。”
小時候,她帶著我回位于江西大吉山鎢礦的外婆外公家。乘綠皮火車需要兩天一夜,如果外公沒有及時收到我們發去的電報,沒有人半夜來鎮上接我們,我媽只能凌晨在街頭隨便找一家小旅館過夜。因為害怕半夜有人撬門而入,她把我哄睡之后,自己背靠著門睡一整夜。
平時看起來最柔弱的她,卻是家里最敢拿主意、最敢給大家兜底的人。
三
我爸工作很忙,我和他的關系在長大中逐漸疏離。中學的我從未給他爭過氣,高考后我選擇了他不允許學的中文,我們的父子關系降到了冰點。
我曾對我爸說:“如果你不讓我讀中文系,我們就斷絕父子關系。”這句話說起來是那么輕而易舉。我沒有做過父親,不知道做父親要經過怎樣的磨礪,也記不清楚父親對小時候的我投入過多少凝視,我所有的怒氣只緣于他想控制我的生活。此后我和我爸長達兩年零交流,大學放假回家,即使兩個人坐在同一張沙發上,也誰都不說話。
我當著全家人的面拒絕了他的建議,一意孤行選擇了另一條路時,他父親的形象就被一個18歲的孩子砸得粉碎。
30歲那年,我參加一個訪談節目,主持人突然請出了我的父母。那一天,我重新認識了我爸。
起因是主持人問了我爸一個問題:“你覺得當初逼兒子學醫是不是一種錯誤?你覺得自己被誤解了嗎?委屈嗎?”
這個問題讓我爸突然哭了出來,豆大的淚珠撲簌直落。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見我爸哭。我媽一邊拍著爸爸的肩膀安慰他,一邊解釋,其實我爸想讓我學醫的出發點很簡單,因為那時我各方面表現都不盡如人意,他覺得只要我學醫,無論我干得好不好,他都能保護我。但如果我選擇讀別的專業,去往異鄉,萬一受了挫敗,被人欺負,他都不知道該如何保護我。
他所有的出發點都來自——他該怎么保護我。而我的所有的出發點都來自——為什么他要管控我的人生。
我媽接著說,我剛到北京頭兩年,半夜會因為空氣過于干燥而流鼻血,總是凌晨打電話給我爸問如何止血最有效。我爸告訴我方法后,掛了電話就立刻穿上衣服去醫院幫我抓藥熬藥。
我也想起來,每次第二天醒來,總會收到爸爸給我發的一條信息:“中藥給你熬好了,剛寄出去了,真空包裝,每天一袋,開水溫熱睡前喝,連喝兩周,看看效果。”
我媽說那是我爸覺得他還能幫助我的唯一方式,他在盡他的全力保護我。
之后,我把這一段故事寫在了散文集《你的孤獨,雖敗猶榮》中,然后把書寄給了他。我不知道他看了沒,也從來沒問過他的感受。但我心里想的是:看!說了不要擔心我學中文找不到工作!我還能把你的故事寫進書里,這下你總該放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