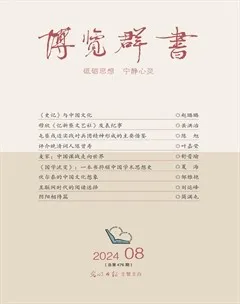張祜的行跡與詩風
唐代詩人眾多,人生情況互異。對于那些客走天涯的詩人來說,其行跡就成為理解詩風的一大關鍵。張祜就是如此,他的詩風就是在漫長的客游中形成的,不了解他的行跡,也就不理解他的詩風。廣泛的客游能幫助詩人拓寬視野,豐富閱歷,觸發靈感,獲取題材,提高技能,從客游角度顯然更能理解其創作。
張祜其人及其行跡
張祜是中晚唐之間的著名詩人,一生為了科舉之業而四處奔波,最后卻厄于時運,身事無成,客死異鄉,詩名與經歷嚴重不符。其生平事跡,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周祖譔《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有詳考。綜合諸家所考可知,其人名祜,字承吉。因祜、祐形近,古書多誤作張祐。貞元中踏入求名路途。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節度使陸長源被亂軍殺害,張祜即有《哭汴州陸大夫》詩哀悼,稱“利劍太堅操,何妨拔一毛。寃深陸機霧,憤積伍員濤”,表明其文學活動始于貞元后期。此后多次赴京舉進士。《唐摭言》卷十一謂其“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詞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此事還可找到旁證,杜牧《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自注就說:“令狐相公曾表薦處士。”表明并非虛構。文中關鍵一句是“元江夏偃仰內庭”,如果是指元稹充翰林學士,則與令狐楚鎮天平年月不合。據元稹《承旨學士院記》:元稹長慶元年二月,自祠部郎中充翰林學士。十月,拜工部侍郎,出院。二年二月,拜工部侍郎平章事。而據《舊唐書·文宗紀》,令狐楚為天平軍節度使,在大和三年十二月至六年二月,這段時間內元稹都不在翰林學士院,而在同州、浙東,可見即使元稹阻抑張祜也不在其任翰林學士時。學界有人將令狐楚薦張祜定在元和十五年到長慶元年,其說亦不確。《全唐詩》卷五一二張祜《寓懷寄蘇州劉郎中》:
一聞周召佐明時,西望都門強策羸。
天子好文才自薄,諸侯力薦命猶奇。
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唯是勝游行未遍,欲離京國尚遲遲。
詩題下自注:“時以天平公薦罷歸。”詩題中的蘇州劉郎中指自禮部郎中出任蘇州刺史的劉禹錫,天平公指在鄆州天平軍擔任節度使的重臣令狐楚。劉禹錫大和五年冬至八年秋,任蘇州刺史。張祜作此詩時,因令狐楚之薦未見成效而罷舉南歸,可見令狐楚薦張祜,的確在大和三年十二月至六年二月,只是阻抑張祜的人不能確定。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序》:“或薦之于天子,書奏不下。亦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表明真正原因是公卿推薦不力,執政未予重視,而不是某位大臣在皇帝面前說了壞話。加以他本人還很有個性,姿態傲岸,喜嘲公卿,出入歌樓酒館,如其《到廣陵》詩所說:
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曉上樓。
嗜酒幾曾群眾小,為文多是諷諸侯。
此被當政者認為士行輕薄,因此未能錄用。
據《唐才子傳》,造成他長期不第的另一原因是“不業程文”,即不認同、不修習進士科必考的詩、賦、判文三種文體,所以盡管在京城、外地混跡多年,“凡知己者悉當時英杰”(《唐才子傳》卷六《張祜傳》),卻幫不上他。“遍識青霄路上人,相逢只是語逡巡。”(張祜《偶作》)交游雖廣,相交卻甚淺。
張祜的干謁始于元和年間,終于大中時。與他關系較深的令狐楚、杜牧均牛黨成員,所以他就受到李黨的排抑,表明大臣黨爭也是其求仕失敗的原因。他跟李商隱和杜牧一樣,生平和文學都受黨爭影響。張祜這些活動,目的是“求解元”,即求得州府“首薦”,因為“首送無不捷者”(《唐摭言》卷二)。但唐代舉進士的名額都分配到各州,每州可薦的舉子人數有限。《唐摭言》卷一《會昌五年舉格節文》明載,國子監、宗正寺每年薦送進士應舉30人、20人。鳳翔、山南東道、山南西道、荊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歙、商鄧、涇原、邠寧、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陜虢所送進士不過15人,河東、陳許、汴州、徐泗、易定、成德、魏博、澤潞、幽州、懷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每年不得過10人。金州、汝州、鹽豐、福建、黔中、桂林、嶺南、安南、邕管、容管等道,所送進士每年不得過7人。為了爭得這些名額,各州每年都要舉行選拔考試,由刺史出題,中試者方能薦舉進士。名額極少而求名者眾,這就在進士中造成激烈競爭,像張祜這類無強援而有性情的文人注定失敗。為了得到這個名額,張祜到處求人。長慶三年,乘舟至杭州,拜謁刺史白居易,希望求得該州“首薦”。時文士徐凝亦自富春來,與張祜爭解元。主試的刺史白居易試《長劍倚天外賦》《余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為首,祜遂不勝而歸,憤激之至,終身不隨鄉試,事載《云溪友議》卷中、《唐摭言》卷二。后杜牧守池州,與張祜結為詩酒之交,對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懷有很大不平,于是為詩三首以高之,一曰《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
百感中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
…… ……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二曰《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
…… ……
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
三曰《贈張祜》:
詩韻一逢君,平生稱所聞。
粉毫唯畫月,瓊尺只裁云。
黥陣人人懾,秋星歷歷分。
數篇留別我,羞殺李將軍。
杜牧的一再稱揚擴大了張祜的影響。
張祜早年還得到過著名詩人李涉的賞識,見李涉《岳陽別張祐》:
十年蹭蹬為逐臣,鬢毛白盡巴江春。
…… ……
霸橋昔與張生別,萬變桑田何處說。
龍蛇縱在沒泥涂,長衢卻為駑駘設。
愛君氣堅風骨峭,文章真把江淹笑。
洛下諸生懼刺先,烏鳶不得齊鷹鷂。
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
新釘張生一首詩,自余吟著皆無味。
策馬前途須努力,莫學龍鐘虛嘆息。
此詩作于元和六、七年李涉貶峽州司倉時,提到二人相識于京城,曾在長安城東灞橋分別,中間指出張詩“氣堅骨峭”,多為題壁,寓有譏刺,詩味雋永,對其多加肯定,寄以希望。
據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序》,張祜早在元和中,就感于時代風氣,開始“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當時輕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諫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以曲阿地古澹,有南朝之遺風,遂筑室種樹而家焉……從知南海……余汨沒者,不足哀承吉之道,邀襲美同作,庶乎承吉之孤,倚其傳而有憐者”,表明他晚年還出任過南海縣令,這在《廣東通志》中也可得到印證。
由于長期不能得第,張祜被迫投靠地方藩鎮謀生,方鎮成為朝廷之外另一能夠決定其命運之地。行跡遍及長城以南,鳳翔以東、嶺南以北廣大區域,陜西、寧夏、甘肅、內蒙、山西、河北、河南、四川、安徽、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廣東等省。在揚州、潤州寓居最久,潤州丹陽還是其晚年隱居終老之地,留下的詩也最多最好。基本的運動軌跡是以揚、潤二州為中心,以京師長安為目的地,在長安至潤州之間做往復循環。應舉求名期間,曾經出游邊地,西北至于鳳翔、涇、原,靈、夏、豐、勝,北至魏博、幽州,南至江西、荊鄂、湘中、嶺南,在唐代詩人中算是游歷范圍最廣、時間最久的一位。李群玉《寄張祜》:
越水吳山任興行,五湖云月掛高情。
不游都邑稱平子,只向江東作步兵。
昔歲芳聲到童稚,老來佳句遍公卿。
知君氣力波瀾地,留取陰何沈范名。
此指出了游歷和創作的依存關系。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
勝華通子共悲辛,荒徑今為舊宅鄰。
一代交游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
魂應絕地為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
聞道平生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
此則是對其不幸命運寄寓同情,對其才情深表贊許,可以視為其生平與文學的精煉概括。
但張祜的主要活動地域還是淮南、浙東、浙西,其次是江西、宣歙、鄭滑。《鑒誡錄》卷七《釣巨鰲》云,會昌四年,李紳節鎮淮南,張祜與崔涯同寄府下。祜以觸物善對,與李紳結為詩酒之知。《劇談錄》卷下載,張祜嘗在徐州王智興使院會飲,從容賦詩,得到王的竭力稱揚,云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不易得。留駐數月,贈絹千匹。從孫望《全唐詩補逸》所輯詩可知,其《閑居作五首》《江南雜題三十首》《寓居臨平山下三首》是杭州詩,《題河陽新鼓角樓》為河陽詩,《到廣陵》為揚州詩,《投滑州盧尚書》為滑州詩,《偶登蘇州重玄閣》《投蘇州盧中丞》《投蘇州盧郎中》為蘇州詩,《奉和池州杜員外南亭惜春》為池州詩。詩中涉及的有京兆府、河南府及并、魏、徐、宋、陳、許、楚、宣、潤、湖、荊、壽、池、岳、潭、衡、洪、江、濠、宿、泗、信、越等二十余州,作詩地點不是郡城、驛站就是道路、僧房。晚年境況凄涼。客居曲阿,大中時卒于丹陽隱舍。《金華子雜編》卷下:
張祜詩名聞于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托詞自敘也。崇遠猶憶往歲赴恩門,請承乏丹陽,因得追尋往跡。而祜之故居,垝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
《甫里集》卷二十顏萱《過張祜丹陽故居序》:
萱與故張處士祜世家通舊。尚憶孩稚之歲,與伯氏嘗承處士撫抱之仁……光陰徂謝,二紀于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處士有四男一女……琴書圖籍,盡屬他人。
所以,張祜成為繼孟浩然之后另一終身為處士的名家,留下巨大遺憾。
盡管如此,他的文才還是曾得到了多位名人的欣賞,有二十多部唐宋筆記、詩話、總集提到他。《唐摭言》《唐才子傳》載令狐楚薦張祜表稱:“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蚤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指出其詩的過人之處。宋人對其尤多肯定,所論十分精當。魏野《送王專王衢之許下自維揚謁孫學士王舍人》:“薛能詩在僧樓上,張祐名題酒肆中。”林逋《孤山寺》:“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祐詩牌妙入神。”表明張詩早在北宋就被當地人刻為詩牌,高懸于酒樓、寺觀,供人觀賞。晁說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更明確提出:“前乎韓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后,有李商隱、杜牧、張祐,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認為其詩出于杜甫,其實不然,杜甫對其影響并不明顯。畢仲游《楓橋寺讀張祐詩碑》引張祜詩:“長洲苑外草蕭蕭,卻憶相從歲月遙。惟有別時應不忘,暮煙疏雨過楓橋。”并有和作:“茂苑春歸花信空,黃梅漸熟麥揺風。今朝門外分攜處,還是楓橋煙雨中。”王安石有《崑山惠聚寺次張祜韻》,孫覿有《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唐人張維、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游,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于天下。”宋李昭玘《樂靜集》卷五《錄張祜詩》:“勝因禪院,有王智興詩刻凡十余篇,最后處士張祜酬智興詩。”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三《記昆山登覽》:“紹興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昆山縣,挈家同邑宰程沂詠之游山,寺寺名慧聚……張祐嘗題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以上所舉僅為著者,但足以顯示出張詩的過人之處。其文學史地位正是憑借著多位唐宋名賢的稱許才得到確定。
張祜詩的諸多勝處
在唐代,張祜的文譽低于李商隱、杜牧、溫庭筠,屬于中等層次的名家。一生經歷德、順、憲、穆、敬、文、武、宣宗八朝。文學史上以宮詞得名,以題詠著名。其《宮詞二首》其一“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是唐代最著名的宮詞,譽滿天下,傳誦極廣。鄭谷《云臺編》卷中《高蟾先輩以詩筆相示抒成寄酬》:“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其下自注:“杜牧舍人《贈張祜處士》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云溪友議》卷中載杜牧此詩作“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表明此詩寫成不久就被樂工制為樂曲,宮女傳唱。題材則大中三年得自進士高璩,涉及武宗愛姬孟才人的故事。詩意得自大歷詩人耿湋《渭上逢李藏器移家東郡》:“求名須有援,學稼又無田。故國三千里,新春五十年。”宋王觀國《學林》卷八:
唐張祜有詩,名《宮詞》,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當時人頗稱賞此詩,然后人讀之,多不曉其句意。唐人小說云:宣宗時孟才人者,本東南人。入宮二十年,以善歌得寵。宣宗不豫,才人侍帝使歌,才人歌《何滿子》一聲而泣下,故祜《宮詞》專為此發。當時人知其事者,無不以為切當也。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三:
景祐四年……陳堯佐為宰相,韓億為樞密院副使。既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為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眾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謄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為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涕下。上憐之,數日,遂為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張祜詩,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魏泰《東軒筆錄》卷一五所載略同。此詩存傳的資料之多,足證是張祜最具影響的代表作,完全可納入一流唐詩范圍。《華清宮四首》《連昌宮》亦為名篇。后者云:“龍虎旌旗雨露飄,玉樓歌斷碧山遙。玄宗上馬太真去,紅樹滿園香自銷。”宋何汶《竹莊詩話》卷十三選張祜此詩,后按:“張祐素以詩名,而《華清宮詩》尤為世所稱。”雖然誤記詩題,但其眼光還是獨到的。
張祜還是中晚唐之間題壁詩的重要作者,如李涉《岳陽別張祜》所說,“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詩題中帶題字的多達85首,比白居易還多。部分詩是題寫上墻的題壁詩。由于多寫當地風物,故而還被視為地域書寫的代表作。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張祜喜游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嵓、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準確指出其詩歌創作融題寺、詠景于一體的藝術特色。張祜《送李長史歸涪州》:“好為題新什,知君思不常。”《旅次上饒溪》:“更想曾題壁,凋零可嘆嗟。”把他喜愛題壁的創作特點概括出來。題材范圍遍及邊塞、山水、寺廟、古跡、驛館、音樂、物象,體裁為五律、五絕、七絕,極少有古體。“題”的后面,常有寺、廟、堂、院等字眼,如《題潤州金山寺》《題杭州孤山寺》《題余杭縣龍泉觀》《題惠山寺》,均為五律,表明已經題寫上壁。少數詩如《禪智寺》無題字,也是題壁詩。另一些詩則帶投、贈、獻等字眼,為干謁詩。還有60多首詠物詩、20多首感懷詩,這些題材,都代表中晚唐詩的一種風氣。《文苑英華》選其詩60余首,題材據《英華》目錄,依次為詠物、樂府、觀妓、山川、行邁、寺觀、隱逸、寄贈、酬和、送行、軍旅、悲悼、居處、花木、禽獸。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卷五將張祜推許為“長慶、寶歷間詩人之翹楚”,立論的基礎就是張祜在多個題材領域的顯著成就。也正是著眼于此,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卷四三才選錄張祜七絕86首,另于卷一六選其五絕26首,名篇佳作,盡在選中。
由于到過的地方多,所以在宋元明清歷代地理總志、方志中出現頻率也高,今存地志中可以查到360余次,僅宋代文學地理總志《方輿勝覽》就出現20次。最著名的莫過于潤州、揚州佛寺題詩,都是題詠地方風物之什。唐人李益、王建、張祜、杜牧、盧仝、崔涯、章孝標、李嶸、王播,都在揚州留過詩。但相比之下,張祜之詩尤其著名。《太平寰宇記》卷八九,潤州丹徒縣甘露寺,“詩人多留題,唯……張祜云‘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澤心寺……詩人多留題。張祜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十國春秋·孫魴傳》:“有《題金山寺詩》,與張祐詩前后并稱,一時以為絕唱。”宋陳舜俞《廬山記》卷三紫霄峰條載張祜詩:“紫霄峰下草堂仙,千載空遺石磬懸。”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卷二《孤山三提勝跡》載張祜詩“斷橋荒蘚合”,孤山條載唐張祜詩“樓臺聳碧岑”,凡此諸作,均堪不朽。《容齋隨筆》卷九《唐揚州之盛》:“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云溪友議》《唐摭言》所載張祜與徐凝爭解元中張祜自舉的代表作,正是《甘露寺詩》的“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的“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其他五絕亦往往超卓。如《江南逢故人》:
河洛多塵事,江山半舊游。
春風故人夜,又醉白蘋洲。
如《松江懷古》:
碧樹吳洲遠,青山震澤深。
無人蹤范蠡,煙水暮沉沉。
如《書憤》:
三十未封侯,顛狂遍九州島。
平生鏌鎁劍,不報小人讎。
此幾首莫不興象超妙,寄托遙深。
張祜的題詠風物詩受到歷代選家的重視,在詩歌總集中入選的作品較多。韋縠《才調集》卷七選張詩六首,含《觀杭州柘枝》等觀妓詩四首,《病宮人》等宮詞二首。王安石《唐百家詩選》選張宮苑、詠古詩七首。宋扈仲榮等《成都文類》選其成都風物詩二首。方回《瀛奎律髓》選其詩七首,皆為名篇。卷一錄其名篇《金山寺》,下按:
此詩金山絕唱,孫魴者努力繼之……大歷十才子以前,詩格壯麗悲感。元和以后,漸尚細潤,愈出愈新。而至晚唐,以老杜為祖,而又參此細潤者,時出用之,則詩之法盡矣。
入選理由,正是此詩取景構境上的“工巧”之長。同卷錄王安石《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下按:
介甫有金山寺五言律詩,未為極致……張祜詩無可議矣。荊公此詩,恐亦未能壓倒張處士也。
此表明張詩高處,宋人難及。
張祜樂府詩的成就較高,短曲長歌,各成格調;韻味風情,不減王建。郭茂倩《樂府詩集》選其樂府詩四十五首,其中屬相和歌系列的《長門怨》,清商曲系列的《丁督護歌》《讀曲歌》《玉樹后宮花》《烏夜啼》《莫愁樂》《襄陽樂》《拔蒲歌》,琴曲歌系列的《思歸引》《昭君怨》,雜曲歌系列的《車遙遙》《愛妾換馬》《樹中草》都屬泛詠前代,不同處在于摹擬味較淡而略具民歌色彩,少數詩中人物非古非今,難以辨別。《入關》為橫吹曲,作者卻將前代樂府的邊關之事置換為唐代鄉貢進士入關一暏京城形勝,大寫秦中帝王州的山河壯麗,新意十足。《白鼻騧》為李白同題詩的擬作。近代曲辭系列的《上巳樂》《大酺樂》《千秋樂》《熱戲樂》《春鶯囀》《雨霖鈴》《折柳枝》中心人物都是女性,時代都在盛唐。一些短詩具有“比興體制”,前半以比興起勢,后半以實寫證之。后人對此亦有論焉。《容齋三筆》卷一六《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后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祜、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
所論即古樂府的比興引喻之體,張祜運用得十分嫻熟。《蘇小小歌三首》《昭君怨二首》屬于詠古,后者得之于京城西北邊地客游期間,寫邊地景色,也未重復古辭。
張祜還有出色的觀獵詩。五律《觀魏博何相公獵》,內容是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出城圍獵的精彩場面,約作于文宗大和三年何進滔擔任魏博節度使以后的十余年間:
曉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
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
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
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此詩八句均為動作描寫,塑造馬上英雄的矯健的身手,不凡的武藝,取材精確,線條明快,極有氣勢,在杭州期間,還得到了白居易的肯定,認為是繼王維《觀獵》之后的又一觀獵題材的名作。白居易對他是抱有成見的,唯獨此詩十分欣賞,可見其品格確實不凡。
張祜還有四首塑造遷客形象的送別、寄贈、傷悼詩,十分成功,印象深刻。《送沈下賢謫尉南康》:
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
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
山高云緒斷,浦逈日波頹。
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
此詩作于京城長安,送別其好友沈亞之貶虔州南康縣尉。
《送徐彥夫南遷》:
萬里客南遷,孤城漲海邊。
瘴云秋不斷,陰火夜長然。
月上行虛市,風回望舶船。
知君還自潔,更為酌貪泉。
此詩是送其友徐彥夫貶嶺南,想象其南遷途中經歷、景色。
《傷遷客歿南中》:
故人何處歿,謫宦極南天。
遠地身狼狽,窮途事果然。
白鬚才過海,丹旐卻歸船。
腸斷相逢路,新來客又遷。
此是寫唐代長安至嶺南驛路上新的遷客南征,而身歿于嶺南的遷客靈柩則北返,生者死者相遇于道,令人不能無感。
《寄遷客》:
萬里南遷客,辛勤嶺路遙。
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魈。
瘴海須求藥,貪泉莫舉瓢。
但能堅志義,白日甚昭昭。
此詩以想象之筆描摹遷客南行情狀,概括性強。《瀛奎律髓》卷四三遷謫類選錄此首,舉為唐人遷謫詩之典范。
此四首詩都有很濃的悲悼意味,讀后深感陷入遷謫的唐文人“處人倫之不幸”,體會到唐代遷謫制度對文人的傷害之深。
張祜詩風的代表性
張祜詩風的特點是短章居多,長于律絕,題材廣泛,取材精當,精于描摹。宮怨、懷古詩比興寄托,寄意深曲,耐人尋味。詩風介于白居易、劉禹錫、杜牧之間。白居易詩重視寫實,多有諷諭,取材貼近日常生活,在反映世態人情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廣度。所到之處,常有題詩,加以形象鮮明,摹寫傳神,其詩遂廣為流傳。這些特點張祜都有。劉禹錫是中晚唐懷古詠史詩派的開創者,經他奠基,杜牧、李商隱、許渾等繼起,遂成為晚唐五代普遍的詩壇風尚,張祜則是中晚唐之間懷古詩的重要作者,寫過的古跡從長安到揚州、浙東、荊州,大小數十處。杜牧為人頗似劉禹錫,詩風也近似,都喜歡詠史懷古,感慨深沉。張祜長期在揚、潤、宣州停留,跟杜牧交往甚密,常有酬唱,因此杜牧的這種詩風張祜也有。杜牧詩風神俊爽,長于絕句,張祜詩亦然,風神俊爽不及,簡練傳神則過之。《能改齋漫錄》卷一五:“唐之詩人,最以摸寫風物自喜,如盧仝、杜牧、張祜之徒。”將張祜、杜牧并舉,表明二人在詩歌創作上的關聯度和相似性。張祜雖感于時代風氣,有懷古題材,但并非簡單模仿,而是注入自己個性,將詠古、寫景結合,融入很深感慨,這樣就不浮泛。
概括來說,張祜詩體現出三種中晚唐詩的創作風氣。
首先是“善狀詠風態物色”,用陸龜蒙的話說,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并認為只有這樣才是“才子之最”。《唐詩品》曰:“(張)處士詩長于模寫,不離本色,古覽物品游,往往超絕,可謂五言之匠也。”準確指出其創作特長。靠著這種超凡本領,張詩得到廣泛認可,交游日廣,詩歌也氣象日新。《舊唐書·元稹傳》:“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摹寫風物是中晚唐詩的寫作趨向,元稹、白居易、令狐楚都有這一特點,元白還以此聞名。張祜也是元和長慶間成名的,其詩也有這一特點,在模寫事物形體狀態方面功夫很深,構思命意精巧,然而又不刻意雕琢,所以高于晚唐眾作。
張祜的風物詩,多以題寺的方式發表,題寺和風物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可截然分開。《瀛奎律髓》卷四七釋梵類選張詩三首,每首都有評騭,可見對張甚為留意。《孤山寺》: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
不雨山常潤,無云水自陰。
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
猶憶西牕夜,鐘聲出北林。
后按:“此詩可謂細潤,然太工,太偶合。”
《惠山寺》:
舊宅人何在,空門客自過。
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
小洞穿斜竹,重階夾細莎。
殷勤望城市,云外暮鐘和。
下按:“此詩同前,三四尤工,五六則工而窘于冗矣。以前聯不可廢也,故取之。”
《題虎丘東寺》:
云樹擁崔嵬,深行異俗埃。
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
俯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
傷心萬年意,金玉葬寒灰。
后按:
(祜)僧寺詩二十四首,金山寺詩第一,亦當為集中第一。孤山寺、惠山寺詩次之。此詩非親到虎丘寺,不知第四句之工。高堂之后,俯視石澗,兩壁相去數尺,而深乃數十丈。其長蜿蜒曼衍,而坼裂到底,泉滴滴然,真是奇觀。故其詩曰石壁地中開,非虛也。故選此詩,以廣見聞……《題道光上人院》亦佳。至如“上坡松徑澀,深坐石池清”之類,則非人可到矣。
《野客叢書》卷二三《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祜詩為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
此說明成功的詩篇可為地方景物存照、傳名。
其次是詠古,所詠多為關中古跡,多達數十處。《集靈臺二首》:
日光斜照集靈臺,紅樹花迎曉露開。
昨夜上皇新授箓,太真含笑入簾來。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
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馬嵬坡》:
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
塵土已殘香粉艷,荔枝猶到馬嵬坡。
《馬嵬歸》:
云愁鳥恨驛坡前,孑孑龍旗指望賢。
無復一生重語事,柘黃衫袖掩潸然。
《太真香囊子》:
蹙金妃子小花囊,銷耗胸前結舊香。
誰為君王重解得?一生遺恨系心腸。
《雨霖鈴》:
雨霖鈴夜卻歸,秦猶見張徽一曲新。
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
《邊上逢歌者》:
垂老秋歌出塞庭,遏云相付舊秦青。
少年翻擲新聲盡,卻向人前側耳聽。
除最末一首外,都是歌詠楊李愛情的。南宋學者洪邁對此尤為注意,其《容齋隨筆》卷九《張祜詩》云: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于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系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傳之樂府也。
《野客叢書》卷二四《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而寧、邠二王尚存、是以張祜目擊其事,系之樂章……蓋紀其實也。
同卷《張祜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祜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祜詩云云。一述明皇時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是祜經涉十一朝也,計死時且百二十歲。
此誤后人追述為作者親睹。由于對歷史的無知,而招致清代學者譏諷。王士禛《香祖筆記》(卷十一)就說:“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者……亦多矣,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四庫全書·野客叢書提要》:“張祐寧王之詩,自屬追詠,而(王)楙以為目擊。又以與祐詩年代不符,則造為祐身歷十一朝,年一百二十余歲之說。然則李商隱有《九成宮詩》,壽更永矣。”但王楙的這一誤解至少表明張祜經歷之豐富,影響之深遠。
張祜這些詩,寫女性的普遍比較感性,寫時政的則語帶感諷,含有理思。《容齋續筆》卷二《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劉克莊《后村詩話》卷三:
王贊《序方干詩》云: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祐尤為杜牧所稱,林逋亦有“張祐詩牌妙入神”之句,牧、逋非輕許可者。
卷一二選錄其寺觀、宮詞十三首,皆名篇。
第三是愛情題材、艷麗詩風,多為絕句,多達30余首,“多道天寶宮中事,入錄者較王建工麗稍遜,而寬裕勝之。其外數篇,聲調亦高。”(《詩源辨體》卷二九)即使同一個人,也傾向于朝著情愛方向處理,傾注了很深的同情和憐惜,而不是從社會政治角度做辛辣的嘲諷批評,風格普遍柔婉。詩中多有精彩的女子動作神態外貌描寫,十分引人注目。所寫的人物普遍命運悲慘,顯然是經過挑選的具有代表性的題材類型。部分詩用樂府古題,虛擬古代人事,并無現實指向。另一部分則取材現實,書寫宮女。《孟才人嘆序》記載的是晚唐樂曲《何滿子》傳唱的故事,主人公武宗孟才人,即此曲的主唱者。武宗駕崩,隨駕而去,事情悲慘。序曰:
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懇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及帝崩,柩重不可舉。議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嗟夫!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進士高璩登第年宴,傳于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話于余,聊為興嘆。
詩曰:
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吊舊才人。
第二句表明張祜作此詩時,此曲已經流傳12年。
又有《病宮人》:
佳人臥病動經秋,簾幕繿縿不掛鉤。
四體強扶藤夾膝,雙鬟慵插玉搔頭。
花顏有幸君王問,藥餌無征待詔愁。
惆悵近來消瘦盡,淚珠時傍枕函流。
此是寫一位兩京行宮中生病將死的宮女,題材當獲取于入京應舉期間。
《退宮人二首》寫一位因故遭棄的宮女:
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
歌喉漸退出宮闈,泣話伶官上許歸。
猶說入時歡圣壽,內人初著五方衣。
《宮詞二首》其二:
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憐。
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這是寫一位先皇時因善歌得寵的宮女,新君即位之后失寵,下場悲慘。《贈內人》贈給他遇到的一位歌女: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唯看宿燕窠。
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焰救飛蛾。
詩題中的宮人是晚唐宜春院妓女,出身樂籍,以年輕貌美且有技能而充選入院。五言排律《華清宮和杜舍人》:
渭水波揺綠,秦山草半黃。
馬頭開夜照,鷹眼利星芒。
下箭朱弓滿,鳴鞭皓腕攘
…… ……
月鎖千門靜,天高一笛涼。
細音揺翠佩,輕步宛霓裳。
禍亂根潛結,升平意遽忘。
衣冠逃犬虜,鼙鼓動漁陽。
外戚心殊迫,中途事可量。
雪埋妃子貌,刃斷祿兒腸。
近侍煙塵隔,前蹤輦路荒。
益知迷寵佞,惟恨喪忠良。
北闕尊明主,南宮遜上皇。
禁清余鳳吹,池冷映龍光。
祝壽山猶在,流年水共傷。
杜鵑魂厭蜀,蝴蝶夢悲莊。
雀卵遺雕栱,蟲絲罥畫梁。
紫苔侵壁潤,紅樹閉門芳。
守吏齊鴛瓦,耕民得翠珰。
此詩從玄宗天寶中渭水射獵、行宮寵幸寫到至德后車駕回京,幽禁大內,失去自由。所言禁中遺聞軼事,不僅后人不知,時人也難曉,甚至多不見于《長恨歌》《連昌宮詞》《津陽門詩》等寫安史之亂及楊李愛情的著名歌行體長詩。由于內容有獨到處,故而具有不容忽視的史料價值,不失為研究玄宗朝政治與文學的第一手資料;加上藝術表現也能夠“到人所未到”,故有特殊的文學意義。
(作者系中國唐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湖南科技大學古代文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