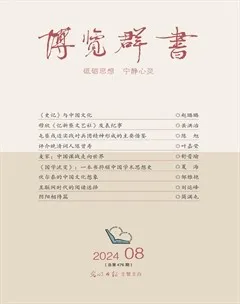張祜研究辨疑三題
張祜,中唐時期的著名詩人,起著承續中晚唐詩歌傳統的重要作用。但其命運多舛,身前不得入仕,身后多年受到冷遇,正史無傳不說,長期以來,即在野史中亦無較完整的述說,直到元代,方在辛文房的《唐才子傳》中有較為完整的呈現,垂至近現代,在一些文學史和唐詩研究的專史之中,也往往只是一閃而過的配角。
20世紀80年代以降,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張祜研究已成為唐詩研究的一個關注點。《中國大百科全書》收入孫望師所撰的詞條,論斷審慎,言簡意賅;2014年譯出的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先生的《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中,為張祜安排了篇幅甚長的專節,讓我們見到了在西方詩學視野中的這位詩人;2020年,《張承吉文集》(宋刻十卷本),整理為《張祜詩集校注》出版,集前整理者尹古華先生《張祜及其詩(代前言)》,為全面介紹和評價張氏的專文,此外還有相當數量論述張祜及詩的文章。
先師時賢有關張祜的輪作中,諸說紛呈。既有一些共識,也有不少分歧很大的地方。這是緣于持論者治學方法有所殊異,史料鑒別取舍有所不同而成的,所好的是,張祜現存的詩作多達517首,與其交接的友人以及筆記、詩話中也留存較多的記載,筆者不揣谫陋,從分歧較大的論點中擇其要者,就張祜研究當下所能占有的材料,本著精思細審,謹斟慎酌的理念和方法,陳疑辨疑,臚陳己見。
本文擬辨析的疑點有三:一為身世之謎,一為不遇之因,一為成就評估失衡之故。茲分述于后。
辨疑之一:身世之謎
張祜身世,包括其名字、生卒年、籍貫等,皆有不同說法。
先說其名,張祜的名字常被弄錯。唐代和其后的典籍中,不少將“祜”誤寫為“祐”,如《唐人選唐詩》中的《又玄集》。即使是最早為張氏立傳的元人辛文房也弄錯了,傳文的首句是“張祐(祜),字承吉”。
“祜”“祐”字形相近,字義又互訓,從其字“承吉”來推詳兩字均可。據說張祜自己對此事也很苦惱,于是給兒子取個小名叫“冬瓜”。他人覺得這件事難以理解,“或以譏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祜審矣。”(【明】胡應麟:《詩藪》),張祜利用“祜”“瓠”諧音和俗諺,幫他人辨正了自己的名字。
不過此事也有異說,謂張祜晚年“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冬瓜”是河堰名,并非其子的小名。此說出自唐人筆記《桂苑叢談》),揆諸情理,一位有名望的士子,為了別人不會把自己的名字弄錯,竟給愛子起個不倫不類的小名。故似以后說為是。
其二,說其生卒年。先說生年,孫望師說,“(張祜)生卒年不祥,約生于德宗貞元初”。貞元建元為785年,“初”當為二或三年,即786或787年。另說則謂張祜生于憲宗貞元八年(792),卒于宣宗大中七年(853),享年62歲。此說為現代學者聞一多在《唐詩大系》中提出的,但聞氏并未交代其來源,因而有的學人,如宇文所安,在這兩個年代前均加個“約”字。尹古華先生對聞說加以考訂。據張祜詩《題青龍寺》云及“二十年沉江海間”(《題青龍寺》),青龍寺在長安新昌坊,說明他20歲那年曾游京師。另據李涉《岳陽別張祜》云:“十年蹭蹬為逐臣,鬢毛白盡把江春”,李涉任試太子通事中書舍人。因言事被貶,時在唐憲宗元和六年(811),據這些材料倒推過去,張祜的生年則為792年。孫說與聞說相教,張祜生年推遲了六七年,則其游長安時只有十三四歲,與張詩作所言“二十年沉江海間”,即20歲時初游長安說不合。尹氏就問說考訂,有材料支撐,不過在詩中記年,往往用約數,不能全依照數學式計算,似以加一“約”字為宜。
其卒年,諸說均據《新唐書·藝文志四》,謂其“大中中卒”,尹古華先生考訂,大中是唐宣宗的年號,前后十三年,“中”當理解為六七年。另據陸龜蒙《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詩并序》:“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陸詩序寫于懿宗咸通十年(869),咸通十年距大中十年為十七年,符合陸龜蒙所言死未二十年的說法。不過如前對其生年說所言,似乎也得加一個“約”字。
其三,張祜的籍貫,有標定為清河(今屬河北)人,有謂南陽(今屬河南)人,尹古華先生,據宋代學者張瞬民《畫墁集》卷七記載見到的碑刻:“刺史杜牧、建安張祜書石”,推定石刻所書“當是可靠的,清河、南陽都是張姓郡望”。其本籍當為建安(今為河南許昌市建安區)(《張祜系年考》)。張祜喜書碑勒名,筆記上多有記載,張舜民所言可信。
辨疑之二:不遇之因
張祜,20歲左右,首游長安之際,已名動公卿,據陸龜蒙追憶:“(張祜)元和中宮體小詩,辭曲艷發,當時輕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譽。”(《和過張祜處士故居并序》)甚至還有一則近于神奇的傳說,武宗病篤時,宮人請為之歌舞《宮詞〈故國三千里〉》,歌舞畢,宮人氣絕而亡。
然而,張祜縱有著盛名,卻連入仕也不可得。有關張祜研究和記述的文字,幾乎一致認為,是由于元稹和白居易從中作梗,名之為“與元白交惡”,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個公案。小有不同的是孫望師的論斷,謂其不得見用的原因,為“當時或病其‘辭曲艷發’。流于輕薄;據說元稹且以為張祜雕蟲小技,有傷風教”,而將白居易置而不論。或許這是認為此事有玷白公請譽,而元稹人品歷史上素有非議,他因妒才而生毀議,則不難理解。
好在有比較多的材料在,不難推詳出令人信服的論斷來。張祜自稱處士,但他并不能像許由、務光那樣超然物外。遁跡山林,而是和一般士子一樣,胸懷濟世之志,期盼進入仕途,得以建功立業。不過他與一般士子有所不同,既不屑刻意揣摩應試詩賦寫作的程式規范,一次次去參加科舉考試,又不想去投靠某個封疆大臣,任幕職官而得到長官推薦,他想如李白一樣,為重臣薦舉,一下子就能立身朝廷。
張祜半生浪跡天涯,大半是為了尋找到賞識和樂于薦舉自己的貴人。為此,他幾乎走遍了大唐疆域,“南窮海徼北天涯”(《所居即事》),他西北到達東受降城(時屬靈州,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境內),東南到達南海(時屬廣州,今為佛山市南海區)。
耗費了幾乎半生精力,投獻了大量的詩章,張祜終于找到兩位賞識自己的重臣,有了兩次被薦舉的機會。
第一次,憲宗元和十五年(820),時張祜年約二十八,是由北郡留守、河東節度使裴度舉薦的。表文連同張祜手錄的新舊詩作三百篇一同獻上。表文雖不可見,但從張祜對裴度的感情投資來看,推想薦詞當是相當懇切的。張祜為了得到推薦,做足了功課。于其晉謁投獻所寫的《獻太原裴度相公二十韻》,對裴公揄揚備至,從大背景“萬古元和史”說起,標定裴度在平定淮西三州中的功業,“一鏡辭西闕,雙旌鎮北都。輪轅歸大丘,劍戟盡洪爐”,堪與韓愈的《平淮西碑》相提并論,裴度自然也會投桃報李。裴度是朝廷中舉足輕重的大臣,詩文又享有盛名,在張祜看來,此次定能進入仕途。在長安待了一年多,等待君王召見,結果是無功而返。
第二次,文宗大和五年(831)秋,時張祜年約三十八,是由太平軍節度使令狐楚舉薦的。令狐楚亦為唐代重臣,有名的詩人。薦表中對張氏至為推重,謂其詩云:“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文宗就此事聽取臣下意見。元稹對答,說:“張生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致。”文宗接受了這個意見,張祜求仕的努力又一次受挫(事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尹古華先生考證,元和三年,元稹罷浙東觀察使,回京任尚書左丞,四年正月即出京任武昌郡節度使,不可能于大和五年時在文宗面前言事。但另有人考證,《唐摭言》可能是把時間弄錯了,元稹進讒言是發生于穆宗當朝,張祜第一次被舉薦之際。
為了等待君王召見,張祜,在長安待了三年,“三年虛度帝城春”(《長安感懷》),他終于心灰意懶,不再謀求官職了。
在沒有得到薦舉機會時,張祜埋怨“唯恨世間無賀老,謫仙長在沒人知”(《偶題》),慨嘆自己沒有得到有力者如賀知章者的援引,如今遇到比賀老分量不知重多少的權貴和文壇領袖的薦舉,依然改變不了身份,回到江南以后,在《傷懷寄蘇州劉郎中》中,慨嘆“天子好文才自薄,諸侯力薦命尤奇。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劉郎中,就是由禮部郎中出任蘇州刺史的劉禹錫。劉氏在元貞革新失敗后,被貶謫到邊州多年,宦海沉浮,命運多舛,張祜想從這位同命運的前輩詩人那里得到慰藉
在第一次薦舉碰壁以后,張祜對謀求貴人舉薦事有所動搖,決定去參加科舉考試。
穆宗安慶三年(823),張祜年約三十一。這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仲春,牡丹花開時,他從蘇州出發,到杭州去參加鄉試。
唐代鄉試,就是參加朝廷組織的進士考試前的資格考試,不過那時并不像明清鄉試那樣,確定考期,選定考場,擬定考題,統一考試,而是由州郡長官考察后擇定。州府的推薦名額非常有限,每個州府只有數名,競爭異常激烈。
張祜去杭州參加鄉試,是仰慕白公的詩名和清望,相信自己一定會被賞識。其時,與張祜同來應試的,還另有一位也是頗有名望的詩人徐凝。白刺史覺得一個個地面試太費時間,于是別開生面,決定讓張、徐二人各自吟出其詩,以定去取。
這場面試,有類于今天電視流行節目——才藝大比拼,不過評分定奪,唯有白公一人。這個故事,唐人范攄的筆記《云溪友議》中有生動而詳細的述說。一開頭,張祜信心滿滿,說解首非我莫屬。比拼開始,張、徐兩位詩人各吟出得意的詩句,從范著所記看,幾個回合下來,徐凝并沒有什么勝出張祜的佳句良什。就在勝負難決之際,白使君出手了,認為“以(張祜)宮詞皆數對,何足奇乎?不如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決定徐凝勝出,張祜落第。
白公的評判的公正性,很引起一些質疑,有人認為白氏是妒才,也有人認為他是要舉“行實”之士,而徐凝為人“椎魯”,就是質樸老實,而張祜是以“輕薄”出名的。從徐凝次年應進士試落第后寫的詩看,“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原來徐凝早與白居易、元稹有舊,鄉試得以勝出就不難理解了。
百年而后,這件事仍常被人提起,北宋詩人蘇軾將徐凝與李白同寫廬山瀑布的詩作比較,予以評論: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
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東坡志林·記游廬山》)
徐凝這一聯詩,未必為“惡詩”,但也只是實狀描摹而已,遠不如張生《題金山寺》中的“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遺貌取神,將水流之狹窄,讓人們于想象中得之,“中流”與“兩岸”對仗也相當工巧。
尹古華先生認為,張祜不遇,除了他因——元抑白阻之外,還要看到自因——個人品格上的缺點。尹先生將其品格上的缺點歸結為三:一是嗜酒,二是疏狂,三是狎妓(《論張祜及其詩》),并作出分析,認為這些毛病,士大夫雖都在所難免,不過張祜走得太遠了,不能為世所容。其實,更恰切地說,他表露得太早,不能節制而已。試看張祜最為人詬病的詩: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
(《從游淮南》)
再看杜牧的名作:
娉娉嫋嫋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
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贈別》)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遣懷》)
幾相比較,從精神內涵上看,同樣輕薄帶有色情味,不過杜牧寫詩時,已貴為員外郎、中書舍人。
張祜之不遇,論者(也包括詩人自己)多歸咎于個人恩怨及品格,但是放開視界,從更深更廣處看,則是時非盛唐,君非玄宗,想再有李白那樣的不次之擢,已是夢想。
張祜生活的年代,大唐已經不是如日中天的開元時代,君王也不能像玄宗那樣乾綱獨斷。
文宗特別愛好詩歌,他曾給彌留之際的重臣、詩人裴度——也是薦舉張祜的恩主——送去自己的一首絕句和短札,希望能得到裴度的和詩。札中說:“朕詩集中欲得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御札尚未送到,裴公已經身亡。開成三年(838),文宗提出在翰林院設置72位詩學士,讓朝臣舉薦,可是不久就有臣下提出反對意見。曾任宰相的李玨在表文中說:
置詩學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輕薄之士,昧于說理、今翰林學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有疑,問學士可也。
就是說,詩學士名既不正,詩人的品質大多不純,再說有了翰林學士就夠了,沒有設置這個職位的必要。又數說憲宗之失,由于君王獎掖詩歌創作,弄得一班“輕薄之徒,……譏諷世事,而后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為嘲詠之詞,屬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事”。(【宋】王讜:《唐語林》)將置詩學士一事和政權穩定與否聯系到一起,使得文宗不得不打退堂鼓。在某些朝臣看來,張祜之流不過是以嘲詠為業的輕薄小人,舉薦之途決不能開。正如宇文所安先生所言,張祜應該屬于另一種詩人,即“將詩歌本身視為一種職業,而不只是作為一種社交技能或附屬于以報救國家為終極目標的生活”(《晚唐詩·文宗與詩歌》),也就是職業詩人、游士。
職業詩人,與有著官員身份的詩人相較,似乎沒有著很大的差異。職業詩人中的絕大多數,甚至全體,都非想以寫詩終老,在詩鄉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而是想以寫詩為跳板進入仕途,實現自己的濟世之志,只是暫時未能如愿而已。
開成之世,值甘露之變后,國事日非,朝外,軍閥割據,藩鎮勢力日益膨大,朝內,宦官專權,黨爭愈加激烈,文宗不可能像玄宗那樣,選拔一位“聲名狼藉”的游士(職業詩人),使之廁身朝廷。
一代才子詩人張祜終身不遇,不能不說是一場悲劇,然而不是命運悲劇抑或性格悲劇,而是歷史悲劇。
辨疑之三:評估失衡之故
張祜詩中最為人們注意的,是陸龜蒙所說的宮體小詩,即宮詞。影響至久、流傳最廣的唐詩選本——清人孫洙的《唐詩三百首》,共選入他的五首詩,除了《題金陵渡》一首以外,其余都是宮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唐詩選》,選入其詩作三首,除一首七律《觀徐州李司空獵》外,另兩首均為絕句,都是張祜早年的作品。在詩選前的導讀中,于批評張為《主客圖》將張祜使為白居易弟子的不當之后,認為“張祜毋寧是另一宮詞高手王建的‘入室’”。宇文所安先生則視之為絕句,特別是七言絕句的高手。在《晚唐》一書中,將其置于《七言詩人》一章之內,認為張祜是個“模仿者”,缺少自己的風格,是個“淺易的詩人”,沒有很高的思想追求。他雖也見到1979年重印的宋版張祜詩集(《張承吉文集》十卷本),但認為其中只“保留有少量的七言律詩,幾乎沒有更長的詩”。從上面列舉的諸著看來,這些學人近于一致的觀點是,張祜只是一位迎合公眾娛樂需要,并沒有多少思想追求,以小詩見長的詩人,并不能卓然自樹,難以視為一代名家。
能為張祜作出全面的合乎歷史實際評價的,首推孫望師。他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張祜詞條中,論其不僅有“為世傳誦”的宮詞和山水懷古詩,“同時也有關懷時政的如《喜聞收復河隴》《元和直言詩》等,評論詩文的如《敘詩》《讀〈韓文公文集〉十韻》等,其中有不少長篇”。還進而就杜牧、李涉過甚其辭的評價:“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作出分析,肯定了陸龜蒙對張氏詩歌風格嬗變的論斷:“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其晚年詩作深得‘諫諷怨譎’之意”。尹古華先生的《論張祜及其詩》全面評價了張氏各種題材和樣式的詩作,尋繹其創作道路,歸結其創作特色,謂“張祜這些詩不如杜甫傳神,也不似賈島的怪癖,但在一個方面上卻超過了杜甫和賈島,那就是‘巧’。”所謂“巧”,即對仗精巧。進而論定“我們很難將張祜歸入韓孟或元白任何一派,他的詩具有獨特的風格、獨到的造詣。無論就數量、質量還是對后世的影響而言,也取得相當的成功,成就與地位,應不在賈島、珧合、溫庭筠之下。”斯論切中肯綮。
張祜的宮詞和山水懷古詩及其早期詩歌創作,諸家看法基本一致,就不做討論,只擬就其詩體取向和詩歌風格的嬗變兩個問題,做一番辨析。
先說張祜的詩體取向。
唐代詩人不少都是諸體賅備,但也大都有所偏好,就是著意去寫某種樣式的詩,以某類詩見長。就張祜而言,他是著意去經營五言詩、律詩,特別是排律(長律),在其后期尤甚。
綜觀張氏詩作,先從五、七言詩體的占比看:其一,他的現存詩作,除了2首雜言詩外,五言有309首,七言有208首,五言詩超出七言詩101首;其二,關注得較多的是律詩創作。律詩中,五律88首、七律89首、五言排律(長律)65首,而古風樂府僅有9首。依據上面兩點,不難看出張祜不只是一位以寫小詩見長者,也善于寫長詩;他對于近體詩的寫作愛好,勝于古體詩。
再從其創作理念看,張氏留有完整的闡釋其詩歌創作觀的詩章——《敘詩》。細讀該詩,不難看出其詩歌創作的關注點,是五言詩。《敘詩》從中國詩歌的源頭——《詩經》說起,“二雅泄詩源,滂滂接漣漪”,再話及五言詩的萌生,“五言起李陵,其什傷遠離”,又歷數了五言詩發展歷程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曹植、劉楨、王粲、阮籍、左思、陸機、番岳、顏延之、沈約、謝靈運、謝眺、江淹、鮑照、陶淵明、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王昌齡、李白、杜甫、張九齡,直到韋應物。張祜一一標出這些詩人的風格特點。還透露了自己的創作追求,“伶倫管尚在,此律誰能吹?”大有繼承詩歌傳統舍我其誰的氣概。從《敘詩》可以看出:一是奉五言詩為正宗,傾力而作的是五言詩;一是廣采博攬,并不獨尊建安風骨,《敘詩》對程子昂認為的“興寄都絕”的六朝宮體詩,仍表現出某種肯定,“陳隋后諸子,往往沙可披”,這些詩人的作品還是有可借鑒之處,可以披沙揀金。一是嚴守格律,以發展和完善律體詩味己任。
張祜的詩,除了少量遣興寫景、吟風弄月的以外,還有著相當數量的抒寫報國無門的抑郁情懷以及和觸及時事的詩章。這類詩,可概言為抒懷言志詩,多為律體,且多為五言排律。
這類抒懷言志的詩,有的是直接言事,如《元和直言詩》。元和,憲宗年號,詩是針對憲宗時朝政的:
陛下欲垂衣,一與夔契論。
成湯事不盡,勿更隨波翻。
直者舉其材,曲者尋其根。
直固不可遺,曲亦不可焚。
用材茍可審,帝道即羲軒。
陛下復上階,四方敢高垣?
陛下喜睢墻,四方必重藩。
畋獵豈無誤?湯泉豈無溫?
始知堯為心,清凈自成尊。
此詩是勸諫憲宗,一要任用賢臣,使得人盡其用;二是要崇尚節儉,減少民眾的勞役和賦稅。憲宗早年勵精圖治,頗有作為,被號為“元和中興”,后卻意志衰退,耽于安樂,疏遠賢臣而任用宦官,又好“羨馀”,肆意搜刮民財,張祜這兩個意見,都切中要害。有的是即事生議。如《憲宗皇帝挽歌詞》和《戊午寓興二十韻》,都是就突然發生的重大事件作出的反響。前者寫于元和十五年憲宗身后。詩作先肯定憲宗早年功業,“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然后就其死因——當時流傳的服食金丹而亡之說,批評其愚昧,“武皇虛好道,文帝未登封”。后者作于文宗開成三年時,是“甘露之變”不久之后。這年朝臣和宦官來了一場大攤牌,結果宦官得勝,不少參與政變的大臣被殺,史家認為此次事變是中晚唐的分界線。張祜在詩中為國家不可知的前途擔憂。“大道開王室,辛勤自賈生。”詩人以漢代政論家賈山自比,把自己的這首比作賈生的《至言》。詩中縱論了西漢興亡之道,最后表述自己的愿望:“殷勤在伊呂,為我致太平”,即希望能有伊尹、呂尚一類的賢臣出現,國家臻于太平之世。尹古華先生認為:“此詩意思隱晦,不易詮釋。唐甘露事變后,朝政為宦官所把持,正直之士動輒得咎,作者亦有顧忌邪?”(張祜詩集校注》)即使到其晚年,已經疾病纏身,行走不便,仍然不忘王事。在得知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歸降唐朝,便激動不已,《喜聞收復河隴》,盛贊天子功業,“共感垂衣匡濟力,華夷同見太平年”。
言志抒懷一類的詩章,直抒胸臆,有助我們認識張祜的另一個不太為人所認知的一面。蔑視禮法,離經叛道,只是表面的,張祜和禮法之士一樣,同樣有著一顆灼熱的心,期望能為生民立命,為后世開太平。
傾情于抒懷言志一類詩章的寫作,必然要擇定合適于這種取向的詩體。在張祜看來,排律,特別是五言排律,是最為合適的。
張祜于發展和完善排律詩歌以抒懷言志,提供了屬于自己的嘗試。其一,張祜的這類詩婉而多諷,怨而不怒也就是孫望師所說的“諫諷怨譎”,可謂復歸風雅;其二,在近體詩律化上,提供了借鑒。他的排律的密集用典,摛文鋪采,以及以文為詩,可謂把排律寫作推向極致。中唐時,五律、七律已經完備定型,也形成合乎詩體要求的美學原則。著意于排律寫作,特別是五言排律者,為數并不多,但張祜全力為之,一寫動輒就數十韻,最長的《戊午年感事書懷一百韻,謹寄獻裴令公(裴度)、淮南李相公(李德裕)、漢南李仆射(李程)、宣武李尚書(李紳)》,長達二百句,千字,可以與之相提并論的唯有白居易的《代書詩寄微之》也是一百韻。戊午年,為文宗開成三年(838),距離甘露事變后兩年,所寄獻的皆為王公大臣,所感之事事,關乎社稷安危。“滿堂金已散,一草命難全”,詩人把子民的命運和國家命運緊緊扣在一起,希望王公們能有一番作為,挽狂瀾于既倒。排律是律詩的一種,按照一般律詩的格式加以鋪排延長而成。它要嚴格遵守律詩的平仄、對仗、押韻等規則,一韻到底,自杜甫以后,方告成熟,體制漸長,聲律愈工。張祜在完善律體,為排律提供了難以企及的樣本。
張祜生活于中晚唐之交,他的詩起著承先啟后貫穿詩歌傳統的作用,胡應麟說:
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卷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形容景物,妙絕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所然,故知文章關汽運非人力。(《詩藪·內篇》)。
張祜身歷德、順、憲、穆、敬、文、宣七朝,這個不算太長的62年,跨過中唐,走向晚唐,詩風既有期望國家中興圖治的心靈掙扎,也有無可奈何的哀嘆。張祜終結了一個時代的詩風,又開啟了另一個時代的詩風。張祜詩歌的價值和意義,不全在與同時代的詩人一較高下,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其在中國詩歌長河中的作用,肯定其獨特的存在。
(作者系文化學者、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