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雪峰希望我能夠更前進(jìn)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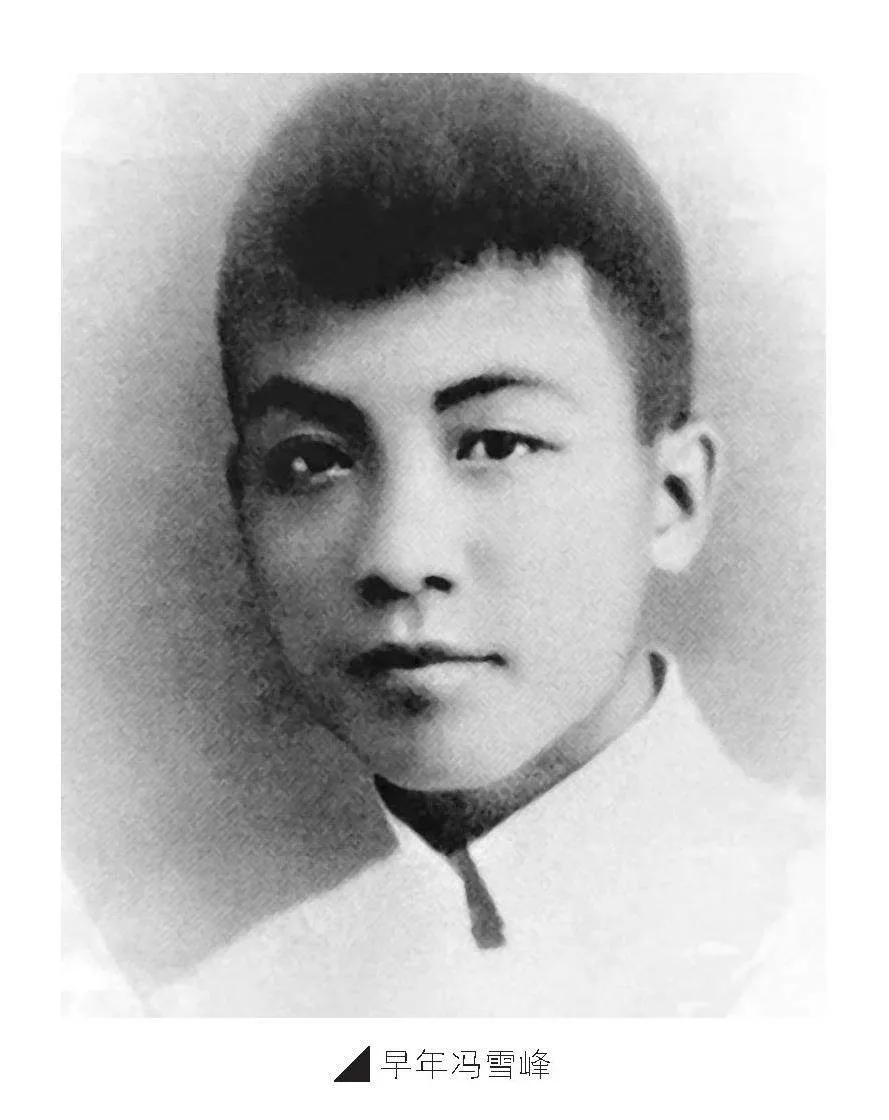


“人生有一知己足矣。” 丁玲與馮雪峰從相識(shí)相知至相偕相助至相思相念,半個(gè)多世紀(jì)的情感歷程與文學(xué)生涯,他倆是師生、同志、戰(zhàn)友、心上人和知己。這是一個(gè)傳奇,是文壇的佳話。今年是丁玲一百二十周年誕辰,亦是馮雪峰一百二十一周年誕辰,謹(jǐn)以此文緬懷這兩位中國(guó)文壇成就卓著的作家。
“一次偉大的羅曼司”
1927年冬,在北京北河沿的漢園公寓里,丁玲正在寫(xiě)她的第二篇小說(shuō)《莎菲女士的日記》。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了解她體會(huì)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zhǎng)久沉溺在失望的苦惱中,但除了自己,誰(shuí)能夠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這是莎菲的內(nèi)心獨(dú)白,亦是作者丁玲“夫子自言”。
丁玲隨和平安,溫文寡言,友人眼里的她不乏愛(ài)情。實(shí)際上,她的內(nèi)心痛苦不堪。與她剛建立起親密關(guān)系的胡也頻,無(wú)法慰藉她心靈的創(chuàng)傷。絕望中,馮雪峰走進(jìn)了她的生命世界。丁、馮相愛(ài),在沈從文看來(lái)是一次“感情的散步”,丁玲卻說(shuō)這是“一次偉大的羅曼司”。
和馮雪峰相識(shí),本意是請(qǐng)他教日語(yǔ)。出乎意料的是,師生關(guān)系僅維持了一天,兩人便暢懷地談起國(guó)事,談起文學(xué),自然也談起了愛(ài)情。
丁、馮可謂一見(jiàn)鐘情。八十歲那年,丁玲在與青年朋友漫談戀愛(ài)問(wèn)題時(shí),依然主張一見(jiàn)鐘情富有浪漫色彩的愛(ài)。她說(shuō):“我覺(jué)得這個(gè)‘一見(jiàn)鐘情’就是許多男女具有的一種特別的‘靈感’,也可稱為‘精神的閃光’,但不是‘沖動(dòng)’之類的東西。——他(她)之所以吸引你,那是因?yàn)槟愕膼?ài)好、喜歡的東西,早就儲(chǔ)存在那里,所以,一旦在人群中發(fā)現(xiàn)他(她),便會(huì)引起一種我不叫‘沖動(dòng)’,就叫‘靈感’吧。”
沖動(dòng)也好,靈感也罷,丁玲與馮雪峰初次見(jiàn)面就有似曾相識(shí)的感覺(jué)。后來(lái),她直言不諱地告訴斯諾夫人:“在我的整個(gè)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愛(ài)過(guò)的男人。”
丁玲與馮雪峰相愛(ài)雖屬“一見(jiàn)鐘情”,但也包含著一定的理性成分。丁玲注重并追求的是馮雪峰精神層面的東西。
馮雪峰是一個(gè)流浪他鄉(xiāng)的窮學(xué)生,從小在浙江義烏一戶農(nóng)民家里長(zhǎng)大,一身土氣。包括沈從文在內(nèi)的許多熟人都認(rèn)為馮雪峰木訥少言,狀如“鄉(xiāng)巴佬”。
在性格、氣質(zhì)上,除了馮雪峰對(duì)丁玲有強(qiáng)勁的震撼力外,兩人在性情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丁玲在待人擇友以及日后創(chuàng)作中的選擇題材、物色人物,有一個(gè)鮮明的審美特征:根據(jù)自己的性格、氣質(zhì)去衡量人,理解人,凡與自己性格、氣質(zhì)相近的人,就容易被她發(fā)現(xiàn)和理解。她喜歡像馮雪峰這樣負(fù)荷時(shí)代重壓、苦悶彷徨而又堅(jiān)忍奮斗、執(zhí)著追求的“倔強(qiáng)的人物”。
丁玲欽佩馮雪峰的文學(xué)才華,并將其引為“文章上的知己”。丁玲對(duì)自己的文學(xué)才情自視甚高,除魯迅、郭沫若、郁達(dá)夫、茅盾、瞿秋白等“五四”文學(xué)先驅(qū),同時(shí)代的年輕詩(shī)人作家極少會(huì)博得她的青睞。唯獨(dú)馮雪峰則不然,她認(rèn)為馮雪峰“特別有文學(xué)天才”。
此外,他們還有一種政治思想上的共鳴。丁玲在北京期間極端苦悶和孤獨(dú),當(dāng)發(fā)現(xiàn)日語(yǔ)老師竟是共產(chǎn)黨員,她喜出望外,大有“相見(jiàn)恨晚”之感。馮雪峰是在這年6月,在李大釗被害兩個(gè)月后,極端恐怖的政治氛圍里,由張?zhí)煲斫榻B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那時(shí)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些遠(yuǎn)離政治的作家,包括胡也頻在內(nèi)的朋友,都不能給丁玲思想上的滿足。于是,丁玲視馮雪峰為一個(gè)可以談心的老朋友。他們談?wù)摗皣?guó)事”頗多,其中包括她親身經(jīng)歷的三一八慘案和李大釗英勇就義。
自然,丁玲的外貌氣質(zhì)、思想品格,對(duì)馮雪峰也具有強(qiáng)烈的吸引力。同樣,使馮雪峰驚訝不已的是,一位“摩登女子”居然愛(ài)上了他這樣一個(gè)鄉(xiāng)巴佬。
丁玲坦誠(chéng)地告訴胡也頻:“我必須離開(kāi)你了。現(xiàn)在我已懂得愛(ài)意味著什么了,我現(xiàn)在同他相愛(ài)了!”她與胡也頻的同居,起先是出于對(duì)友人“冷待”與“揶揄”的“生氣和固執(zhí)”而有意為之,而后是“像姐弟一般”住在一起。對(duì)此,沈從文《記丁玲》中有所披露,他說(shuō),胡也頻曾告訴我,他與丁玲“兩人雖同居了數(shù)年,還如何在某種‘客氣’情形中過(guò)日子”。
丁、胡兩人無(wú)論在思想感情還是性格上都有著很大的區(qū)別。況且,胡也頻日常不愛(ài)多說(shuō)話,丁玲對(duì)其了解甚少,兩人一時(shí)無(wú)法達(dá)到心心相印的境界。直至馮雪峰介入后,兩人才有過(guò)一次長(zhǎng)談,丁玲對(duì)他開(kāi)始有了較多的了解,對(duì)他的感情增添了“更尊敬”“更同情”的成分。胡也頻犧牲后,丁玲承認(rèn):“以前我一點(diǎn)都不懂得他,現(xiàn)在我懂得了,他是一個(gè)很偉大的人……”但他實(shí)際上并沒(méi)有真正觸動(dòng)丁玲的感情,因此丁玲心中早有去意。
與丁玲初識(shí)期間,馮雪峰所處的生活環(huán)境相當(dāng)危險(xiǎn),反動(dòng)軍閥在查抄北新書(shū)局時(shí),發(fā)現(xiàn)他的一部譯稿的扉頁(yè)上有“這本譯書(shū)獻(xiàn)給為共產(chǎn)主義而犧牲的人們”的題詞,他因此而遭通緝。原計(jì)劃準(zhǔn)備離京南下,但見(jiàn)到丁玲后,他貿(mào)然改變初衷,決定留在北京,蟄居在未名社友人家。
1928年,丁玲、胡也頻、馮雪峰共同做了一個(gè)決定:三人一起去杭州生活。春暖花開(kāi)的杭州并沒(méi)有使丁、胡、馮三人感受到溫馨、清新,他們之間掀起了一場(chǎng)感情大風(fēng)暴。
到杭州一周后,胡也頻心力交瘁,落魄地跑回上海。他痛苦地告訴沈從文“他已準(zhǔn)備不再回轉(zhuǎn)杭州”。然而,胡也頻從沈從文處覓得“神丹妙藥”,迅速趕回杭州,終于迎來(lái)“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艷陽(yáng)天。丁玲曾承認(rèn),到杭州后才決定和胡也頻正式結(jié)為夫妻,斷絕了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
丁玲從憤怒的胡也頻身上明顯感受到那種“可怕的男性的熱愛(ài)”。更何況,胡也頻時(shí)刻準(zhǔn)備殉情。而這種足以震懾丁玲靈魂的熱情和勇氣,恰是馮雪峰所缺乏的。她在《不算情書(shū)》中責(zé)怪馮雪峰:“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頻那樣的人,你能夠更鼓動(dòng)我一點(diǎn),說(shuō)不定我也許走了。你為什么在那時(shí)不更愛(ài)我一點(diǎn),為什么不想獲得我?”她埋怨馮雪峰,把自己的無(wú)主見(jiàn)歸咎于馮雪峰的無(wú)勇氣。
激情過(guò)后,丁玲與胡也頻繼續(xù)逗留在西子湖畔,馮雪峰則負(fù)著心靈重創(chuàng)離開(kāi)了丁玲。
是年7月,馮雪峰回到義烏。他與中共浙江黨組織接上關(guān)系,回家鄉(xiāng)工作,任城區(qū)支部書(shū)記,公開(kāi)身份是縣立初級(jí)中學(xué)國(guó)文教員,任教期間很快與學(xué)生何愛(ài)玉建立了愛(ài)情關(guān)系。后因遭國(guó)民黨浙江省政府通緝,馮雪峰于11月悄然告別義烏,重返上海。第二年開(kāi)春,何愛(ài)玉離家來(lái)滬,3月與馮雪峰結(jié)為夫妻。
不愿用愛(ài)情去擾亂別人的工作
1930年3月,中國(guó)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成立。成立前夕,姚蓬子受組織委托,征求丁玲意見(jiàn),問(wèn)她是否愿意參加左聯(lián)。丁玲有些興奮,但得知馮雪峰是左聯(lián)發(fā)起人之一時(shí),她短暫默思后說(shuō):“蓬子,我不參加吧。”這個(gè)回答出乎姚蓬子意料,但他很快理解了,這是丁玲“一種感情的矛盾”的結(jié)果。
自從與馮雪峰分手后,丁玲始終生活在情理矛盾和煩亂不安的心緒中。她曾下決心寫(xiě)信給馮雪峰表示和他決絕,但她始終無(wú)法忘懷那段愛(ài)戀。此時(shí)她害怕加入左聯(lián)后兩人見(jiàn)面機(jī)會(huì)增多,會(huì)引起更大的不安和糾紛,因此壓抑了自己從事社會(huì)活動(dòng)的強(qiáng)烈愿望。
1930年2月,胡也頻去濟(jì)南省立高中任教。丁玲一面在給胡也頻寫(xiě)信訴說(shuō)“離情”之苦,一面在燈下?tīng)t旁向姚蓬子吐露自己內(nèi)心劇烈的隱痛。丁玲曾經(jīng)對(duì)馮雪峰表露真情:“我總以為你還是愛(ài)我的,我永遠(yuǎn)是愛(ài)著你,依靠著你,我想著你愛(ài)我,不斷的,你一定關(guān)心我得利害,我就更高興,更想向上,更感覺(jué)得不孤單,更感覺(jué)得充實(shí)而愿意好好做人下去。”后來(lái)又多次在信中向他表白:“可是我是真的這樣生活了幾年,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謊,我過(guò)去同他……講到我的幾年的隱忍在心頭的痛苦,講到你給我永生的不可磨滅的難堪。”
5月,丁玲與胡也頻參加了左聯(lián)。此時(shí),馮雪峰、王學(xué)文、姚蓬子等人正在籌備暑期社會(huì)科學(xué)補(bǔ)習(xí)班,馮雪峰來(lái)請(qǐng)胡也頻任課,講無(wú)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和馬列文藝思想。在補(bǔ)習(xí)班上,丁玲與馮雪峰見(jiàn)面多了,旁觀者姚蓬子看到的一景是:“誰(shuí)都沒(méi)有被先前那種不愉快的回憶所擾亂,各人都沉靜地處理著自己的事務(wù)。”
姚蓬子看到的是表面。表面上他們兩人僅是同志而已,實(shí)際上兩人的關(guān)系既復(fù)雜又微妙。有一次兩人在北四川路相遇,馮雪峰昂然從丁玲身后大踏步地跑到她的前面,不理她,完全把丁玲當(dāng)作路人。丁玲為馮雪峰的冷漠態(tài)度傷心,甚至恨他,常常氣憤地想:“哼,你以為我還在愛(ài)你嗎?”同時(shí)又寬容與體諒他內(nèi)心無(wú)法言說(shuō)的痛苦,她私下對(duì)馮雪峰說(shuō):“我永遠(yuǎn)不介意你所給我的不尊敬,我最會(huì)原諒你。”
丁玲無(wú)法用快刀斬?cái)嗨龑?duì)馮雪峰的感情,但她經(jīng)過(guò)一場(chǎng)暴風(fēng)驟雨后相對(duì)平靜多了。她學(xué)會(huì)用理智去克制情感,正視現(xiàn)實(shí):馮雪峰使君有婦,喜添千斤;自己也有身孕,胡也頻亦在左聯(lián)工作繁重。因此,丁玲不愿意因?yàn)樽约菏莻€(gè)女人,用愛(ài)情去擾亂別人的工作。
丁玲隱忍著痛苦,把自己“理還亂”的思緒轉(zhuǎn)移到新興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寫(xiě)作上去。她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講的仍是革命與戀愛(ài)的故事,但故事中流露出那種纏綿悱惻、一波三折的感情,實(shí)為丁玲當(dāng)時(shí)心態(tài)的折射。
苛求與希冀
1931年1月17日,“東方飯店案件”發(fā)生,胡也頻等三十多名共產(chǎn)黨人和左翼人士被捕。馮雪峰不顧個(gè)人安危,投入營(yíng)救的行列。左聯(lián)五烈士犧牲后,馮雪峰接任左聯(lián)黨團(tuán)書(shū)記。
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頻犧牲后,丁玲幾次三番執(zhí)意要去胡也頻所向往的紅色蘇區(qū)。潘漢年要她跟他去做他所從事的特科工作,她沒(méi)同意。后來(lái),經(jīng)馮雪峰的勸說(shuō),她才接受組織安排繼續(xù)留在上海,編輯《北斗》。
丁玲的人生方向業(yè)已確定,從此她走上了革命道路。她的感情由此起了巨變,表面上異常平靜,暗中心潮泛濫,常常被一種連自己也不明白的紛亂和矛盾蹂躪著。擔(dān)任《北斗》主編前,為了梳理情緒,丁玲托姚蓬子把馮雪峰找來(lái)作一次坦白的解釋。她希望通過(guò)解釋能忘記過(guò)去的一切隔閡、恩怨和成見(jiàn)。
這段時(shí)間,丁玲與馮雪峰接觸相當(dāng)頻繁,本已被理智壓抑下去的情感再次噴薄而出。丁玲按捺不住迷狂的心,拿起筆給馮雪峰寫(xiě)信:
我這兩天都心離不開(kāi)你,都想著你。我以為你今天會(huì)來(lái),又以為會(huì)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現(xiàn)在五點(diǎn)半鐘了。這證明了我的失望……
此信寫(xiě)于1931年8月11日,是《不算情書(shū)》(三封)之第一封,丁玲在信中恣意地向馮雪峰袒露她的真情實(shí)感。幾乎在同時(shí),她寫(xiě)了一首詩(shī)《給我愛(ài)的》。丁玲一生甚少寫(xiě)詩(shī),此詩(shī)是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愛(ài)情詩(shī)。這首詩(shī)也是寫(xiě)給馮雪峰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首公開(kāi)的情詩(shī),不日便發(fā)表在9月20日發(fā)行的《北斗》創(chuàng)刊號(hào)上。透過(guò)這首《給我愛(ài)的》,那個(gè)纏綿悱惻的丁玲不見(jiàn)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gè)壯志滿懷、激情亢奮的丁玲。
馮雪峰默默承受著這份感情,他不愿因此傷害妻子。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要避免卻也難。為了這件事,馮雪峰的妻子一直悶悶不樂(lè)。新中國(guó)成立后,丁、馮均在北京,但馮雪峰一般不單獨(dú)與丁玲見(jiàn)面,在家里也從不言她。
與丁玲不同,馮雪峰有他獨(dú)特的表達(dá)方式。丁玲參加一系列公開(kāi)的社會(huì)活動(dòng),均是左聯(lián)組織決定的,其中大多是馮雪峰擔(dān)任左聯(lián)黨團(tuán)書(shū)記期間親自點(diǎn)名安排的。1932年2月,丁玲加入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是年秋,她接替錢杏邨任左聯(lián)黨團(tuán)書(shū)記,至次年5月遭秘密逮捕。
編輯《北斗》期間,丁玲自己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同樣面臨著“兩難”抉擇之窘境。1928年春,和丁玲認(rèn)識(shí)僅數(shù)月后,馮雪峰在上海《小說(shuō)月報(bào)》上看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記》,當(dāng)即給還在北京的丁玲寫(xiě)了封長(zhǎng)信。他告訴丁玲他是不大容易哭的,但看了這篇小說(shuō)他哭了。他對(duì)她寄予很大希望,說(shuō)了許多鼓勵(lì)的話,要她繼續(xù)寫(xiě)小說(shuō)。信中,他又直率地指出:“你這個(gè)小說(shuō),是要不得的。”這封信是馮雪峰第一次評(píng)論丁玲的文章,引起丁玲思想的震動(dòng)是巨大的。當(dāng)時(shí),正處于讀者追蹤恭維包圍里的丁玲,接到此信,相當(dāng)不高興。眾人皆說(shuō)好,唯獨(dú)他說(shuō)不好;既然不好,為什么還要哭?為此,丁玲與馮雪峰有過(guò)爭(zhēng)論。
其實(shí),馮雪峰不僅在莎菲身上看到丁玲本人非常濃重的影子,而且深刻地理解丁玲苦悶的實(shí)質(zhì)。“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使馮雪峰在丁玲身上似乎也看到了自己,他為莎菲落淚,實(shí)際上亦為自己。因?yàn)樗穷w苦悶彷徨而執(zhí)著追求的心終于得到了理解。這便是馮雪峰“哭”的原因。但是,他還是站在左翼的政治立場(chǎng)上從世界觀方面向丁玲(包括其他知識(shí)分子作家)提出克服小資產(chǎn)階級(jí)意識(shí)“改移自己的立場(chǎng)”的要求。不過(guò),丁玲心里還是存留著一個(gè)疑惑:是不是《莎菲女士的日記》有不好的傾向?
1931年,一場(chǎng)泛濫于中國(guó)十六省的特大水災(zāi),喚醒了一盤散沙似的農(nóng)民百姓的群體意識(shí)和斗爭(zhēng)意識(shí),也激起左聯(lián)作家們的興奮與重視。錢杏邨后來(lái)回憶說(shuō):“1931年的中國(guó),最值得作家們抓取的主要題材,應(yīng)該是廣大的洪水的災(zāi)難。”丁玲的中篇小說(shuō)《水》發(fā)表在《北斗》第一卷前三期上,以全新的姿態(tài)和風(fēng)格——新的內(nèi)容、新的審美視角和新的藝術(shù)手法,震撼了中國(guó)文壇。
而站在左翼文學(xué)潮頭的馮雪峰,以其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文學(xué)批評(píng)家的藝術(shù)敏銳,關(guān)注著丁玲,并不失時(shí)機(jī)地在《北斗》發(fā)表重要論文,贊譽(yù)它是“新的小說(shuō)誕生”。馮雪峰還指出處于轉(zhuǎn)換期的“丁玲還不能即刻是簇新的作家”,她還需要“對(duì)于自己的一切舊傾向舊習(xí)氣的斗爭(zhēng),對(duì)于自己的脫胎換骨的努力”,認(rèn)為“《水》只能是新的小說(shuō)的一點(diǎn)萌芽,而不能有更高的評(píng)價(jià)”。而且,他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丁玲“轉(zhuǎn)換”前的早期創(chuàng)作成績(jī),甚至武斷地指責(zé)《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佳作表現(xiàn)了作家思想上“壞的傾向”。
胡也頻犧牲后,丁玲的情緒波動(dòng)相當(dāng)強(qiáng)烈,極度寂寞,極度亢奮。但是,無(wú)論是丁玲還是馮雪峰,在處理對(duì)方的感情時(shí),都顯得較為理智。特別是馮雪峰,采用相當(dāng)理智的克制態(tài)度,把自己對(duì)丁玲的感情轉(zhuǎn)移到對(duì)她的革命工作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關(guān)注上。他希冀中的丁玲,應(yīng)該是一個(gè)佼佼者,自始至終能夠和自己一道走在時(shí)代的前列。后來(lái),丁玲說(shuō):“他這是以高標(biāo)準(zhǔn)來(lái)要求我,好像從我們最初見(jiàn)面認(rèn)識(shí)起,他對(duì)我這個(gè)人,對(duì)我的文章總是表現(xiàn)出不滿足,使我覺(jué)得委屈,但我一直感到他總是關(guān)注著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夠更前進(jìn)一步。”
從1930年7月寫(xiě)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以后,到1931年夏《水》發(fā)表的一年間,丁玲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相對(duì)減少,似乎在完成了莎菲時(shí)代的第一個(gè)高峰之后,她正在積蓄力量以期迎接新的創(chuàng)作高潮的到來(lái)。
以特殊的形式,關(guān)注著丁玲
丁玲的創(chuàng)作蒸蒸日上,贏來(lái)了崇高的聲譽(yù),為此,她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jià)。
1933年5月14日“丁潘事件”發(fā)生,丁玲和潘梓年被國(guó)民黨逮捕。中國(guó)左翼作家聯(lián)盟發(fā)表了《反對(duì)白色恐怖宣言》,將國(guó)民黨反動(dòng)派用恐怖手段摧殘革命文化,屠殺革命文化工作者的罪惡消息暴露于全世界,強(qiáng)烈要求立即釋放丁、潘及一切階級(jí)斗爭(zhēng)的“罪犯”。由中國(guó)民權(quán)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領(lǐng)銜,聯(lián)合文藝界人士三十八人,聯(lián)名給南京政府發(fā)了營(yíng)救丁玲、潘梓年的電報(bào)。當(dāng)時(shí),新調(diào)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zhǎng)兼管文委工作的馮雪峰,指派宣傳干事樓適夷代表左聯(lián)參加中國(guó)民權(quán)保障同盟組織的“丁潘保障委員會(huì)”,向國(guó)民黨要人。當(dāng)時(shí)有關(guān)營(yíng)救事宜都是在李達(dá)、王會(huì)悟家商議的。營(yíng)救委員會(huì)曾設(shè)想把丁玲的母親從湖南接到上海,向法院正式起訴,但未能實(shí)現(xiàn)。營(yíng)救委員會(huì)還約請(qǐng)記者史沫特萊和伊羅生撰寫(xiě)報(bào)道,發(fā)消息給上海的西文報(bào)紙和國(guó)外進(jìn)步刊物,同時(shí)發(fā)動(dòng)上海進(jìn)步輿論界掀起抗議浪潮。文化界相繼組織“丁潘營(yíng)救會(huì)”并發(fā)表宣言,開(kāi)展為丁、潘家屬募捐的活動(dòng)。6月14日,我黨三名特工秘密擊斃策劃丁、潘案之主犯馬紹武,并給囂張一時(shí)的特務(wù)、叛徒以嚴(yán)厲的警告。
與此同時(shí),聲援工作也在出版界緊張地進(jìn)行著。由魯迅建議,經(jīng)趙家璧主持的上海良友圖書(shū)印刷公司以最快速度于6月27日出版丁玲長(zhǎng)篇小說(shuō)《母親》(未完成稿),次日在北四川路門市部先發(fā)售特制的作者簽名本一百冊(cè),第一版印四千冊(cè),一個(gè)月銷完,影響很大。接著,馮雪峰把丁玲事先寄存在王會(huì)悟處的收藏著她文稿、手跡、照片、信札的小箱取出,存放在較安全隱蔽的南市謝澹如家。為了擴(kuò)大對(duì)丁玲的宣傳,馮雪峰又把其中三篇《不算情書(shū)》和《莎菲日記第二部》《楊媽的日記》發(fā)表在《文學(xué)》(茅盾主編)和《良友畫(huà)報(bào)》上。茅盾還在《文學(xué)》上發(fā)表論文《丁玲的〈母親〉》,配合《母親》的出版,擴(kuò)大聲援丁玲的聲勢(shì)。
據(jù)樓適夷說(shuō),整個(gè)營(yíng)救工作由共產(chǎn)黨主持,中國(guó)民權(quán)保障同盟出面組織。上海黨組織領(lǐng)導(dǎo)人馮雪峰就是以這樣一系列特殊的形式,關(guān)注著丁玲和她的生命安危。
國(guó)民黨反動(dòng)派不敢輕舉妄動(dòng),把丁玲秘密轉(zhuǎn)移到南京。從1933年5月至1936年9月,丁玲在南京度過(guò)了她人生最黑暗也使她后半生最難堪的三年幽禁生活。
起初,國(guó)民黨特務(wù)對(duì)丁玲監(jiān)視森嚴(yán);一兩年后,才給了她些許自由,準(zhǔn)她在南京郊區(qū)“獨(dú)立居家”,準(zhǔn)許她進(jìn)城走動(dòng)。初夏一天,在夫子廟的一個(gè)小茶館,丁玲遇到正在喝茶的左聯(lián)盟員張?zhí)煲淼热耍s定第二天在雞鳴寺見(jiàn)面。張?zhí)煲韼?lái)的消息像一盆冷水澆在丁玲頭上。原來(lái),丁玲被捕后,上海白色恐怖嚴(yán)重,左聯(lián)盟員從九十多人減至十二三人。馮雪峰因身份暴露奉調(diào)赴瑞金中央蘇區(qū),周揚(yáng)、夏衍去了日本,錢杏邨不易找到,而張?zhí)煲硪灿泻镁貌蝗ド虾A恕?/p>
回南京一個(gè)多星期后,張?zhí)煲砗鋈粊?lái)看望丁玲,給她帶來(lái)一張字條。丁玲喜出望外,字條是馮雪峰親筆寫(xiě)的:“知你急于回來(lái),現(xiàn)派張?zhí)煲韥?lái)接你,可與他商量。”后來(lái)張?zhí)煲韼椭×峄b成貧苦人家的婦女,并由他侄女陪同到達(dá)上海。走出火車站,兩人叫了輛出租車,到泥城橋下了車,接著上了一輛早停在路旁的汽車,車上等待的是胡風(fēng)(張光人)。胡風(fēng)把丁玲安宿在北四川路儉德公寓。這個(gè)公寓有前后門,客房很多,旅客可在房?jī)?nèi)用飯,既隱蔽又安全。胡風(fēng)告訴丁玲,這一系列精密周到的計(jì)劃都是馮雪峰事前安排好的。關(guān)于丁玲“急于回來(lái)”的消息,是魯迅轉(zhuǎn)告給馮雪峰的。
第三天,馮雪峰來(lái)看丁玲。看到馮雪峰,丁玲第一個(gè)感覺(jué)是他變了。或許丁玲還不知道,馮雪峰到瑞金后,任中央蘇區(qū)黨校教務(wù)長(zhǎng),并參加了黨的六屆五中全會(huì),后又當(dāng)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guó)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huì)候補(bǔ)執(zhí)行委員,再后來(lái)跟隨中央紅軍經(jīng)過(guò)二萬(wàn)五千里長(zhǎng)征到達(dá)陜北。因?yàn)橹泄采虾5叵曼h組織與中共中央失去聯(lián)系,長(zhǎng)期處于孤軍作戰(zhàn)狀態(tài),中央為了弄清上海地下黨的情況,盡快重新建立聯(lián)系,于1936年4月25日特派馮雪峰秘密回上海工作。馮雪峰抵達(dá)上海還不到一個(gè)月,就迅捷地籌劃了這次丁玲來(lái)滬行動(dòng)。
三年來(lái),丁玲和馮雪峰各自經(jīng)歷了非同尋常的遭遇。此時(shí)此刻丁玲唯一希望的是能夠得到馮雪峰的同情與安慰。出乎丁玲意料的是,馮雪峰冷若冰霜,沒(méi)有安慰的話語(yǔ),更無(wú)深入詢問(wèn)的意思,丁玲滿腹委屈與埋怨。
馮雪峰長(zhǎng)期從事地下工作,已養(yǎng)成高度緊張、不茍言笑的職業(yè)習(xí)慣,并且在他看來(lái),個(gè)人受點(diǎn)苦難委屈算不了什么,唯此為大的是黨的事業(yè)不受任何損失。他興致勃勃地講長(zhǎng)征故事,講毛澤東,講遵義會(huì)議,講陜北,講瓦窯堡,講上海文壇,講魯迅……特別是他親身經(jīng)歷的二萬(wàn)五千里長(zhǎng)征和他崇敬的毛澤東,愈發(fā)堅(jiān)定了丁玲去陜北的決心。
兩個(gè)星期后,馮雪峰告訴丁玲去陜北蘇區(qū)因交通中斷無(wú)法實(shí)施,經(jīng)與潘漢年商量,要她先回南京,設(shè)法爭(zhēng)取公開(kāi)到上海來(lái)做救亡工作。丁玲沮喪透了,忍不住失聲痛哭,憤憤然對(duì)馮雪峰說(shuō):“你只知道長(zhǎng)征的艱難。可你們是一支隊(duì)伍,有無(wú)數(shù)的好同志在一起,你們是在大太陽(yáng)底下與敵人斗爭(zhēng)。你沒(méi)法體會(huì)到我獨(dú)自一個(gè)在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一秒、一點(diǎn)一滴地忍受著煎熬!”但丁玲只能接受馮雪峰的意見(jiàn),無(wú)可奈何地回南京去了。
不日,心急如焚的丁玲寫(xiě)信給馮雪峰,告訴他自己公開(kāi)出來(lái)已無(wú)希望,要求來(lái)上海到她向往的地方去。馮雪峰迅速回信寄到方令孺家,同意丁玲要求,并約定時(shí)間派周文愛(ài)人鄭育之到火車站接她,當(dāng)晚安宿在西藏路一品香旅館。第二天,馮雪峰同周文來(lái)看丁玲,告訴她中央已回電同意她去陜北,置辦行裝等具體事宜和周文接頭。
1936年9月,馮雪峰安排聶紺弩與丁玲假扮成夫妻同去西安,再由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負(fù)責(zé)護(hù)送她到黨中央所在地保安。離滬前,丁玲把近期作品匯編成集,即同年11月由上海良友圖書(shū)印刷公司出版的《意外集》。丁玲把1933年9月發(fā)表在《文學(xué)》上的《不算情書(shū)》編入此書(shū),稿費(fèi)后由周文匯到湖南給丁母作為家用。馮雪峰為丁玲送行,并受宋慶齡委托給丁玲送來(lái)三百五十元。丁玲感激的淚水奪眶而出。這一回,馮雪峰破例地沒(méi)有阻止她。
“我知道他當(dāng)時(shí)不痛快,他也知道我的艱難”
1937年1月,馮雪峰到中央新駐地延安向黨中央?yún)R報(bào)上海的工作,正在前線的丁玲奉任弼時(shí)之命陪同史沫特萊回延安。在延安,馮雪峰特地到窯洞來(lái)看望丁玲,兩人有過(guò)兩次暢懷的談話。 2月,馮雪峰即返回上海。之后,兩人南北遙望,“千里共嬋娟”。
同年8月,丁玲在率領(lǐng)第十八集團(tuán)軍西北戰(zhàn)地服務(wù)團(tuán)開(kāi)赴山西抗戰(zhàn)前線前,接受了斯諾夫人的采訪。在回答“你最懷念什么人?”時(shí),丁玲答:“我最紀(jì)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峰。”而此時(shí)的馮雪峰正在浙江家鄉(xiāng)進(jìn)行抗日斗爭(zhēng)和寫(xiě)作。
1941年皖南事變后,馮雪峰被國(guó)民黨逮捕,后被關(guān)進(jìn)上饒集中營(yíng)。在那里,被病魔纏身的馮雪峰心境變得非常壞。但強(qiáng)烈的生的欲望,使他竭力保持平靜。一天晚上,他夢(mèng)到了一雙女性的眼睛,他把這一幕寫(xiě)進(jìn)了詩(shī)中,并給詩(shī)取名為《哦,我夢(mèng)見(jiàn)的是怎樣的眼睛》:
哦,我夢(mèng)見(jiàn)的是怎樣的眼睛!
這樣和平,這樣智慧!
這準(zhǔn)是你的眼睛!這樣美麗,
這樣慈愛(ài)!襯托著那樣隱默的微笑;
那樣大,那樣深邃。那樣黑而長(zhǎng)的睫毛!
那樣美的黑圈!
與馮雪峰關(guān)押在一起的畫(huà)家賴少其,應(yīng)馮的請(qǐng)求,按照詩(shī)的描述畫(huà)了三四張眼睛的素描。馮雪峰在一張滿意的畫(huà)上,題了一首《霞光》。詩(shī)的開(kāi)頭是這樣寫(xiě)的:“是的,長(zhǎng)久以來(lái)我就懂得‘絕望’是怎么一回事了,朋友!——這樣的女人的眼光,豈不是在什么地方我都曾經(jīng)接觸過(guò)?”詩(shī)中的女主人公也是畫(huà)中那位有著一雙美麗眼睛的女性。她是一位失去了一切,“甚至連她乳頭上的孩子”也被剝奪的母親。苦難、戰(zhàn)爭(zhēng)、災(zāi)害,使她經(jīng)歷著各種磨難,那雙美麗的眼睛,從溫順變?yōu)閼嵟敝两^望、癡呆。馮雪峰在這幅畫(huà)里從母親絕望的眼睛中看到了“希望”:
啊啊,你怎樣地驚異看罷──
一道圣潔的,希望的宏闊的返光,
竟發(fā)自那癡呆的,石頭一樣的,
蒼白的臉上?
我的心由喜躍而沉下了!
新中國(guó)成立后,賴少其在北京第一次與丁玲相遇,驚訝不已,原來(lái)他當(dāng)年為馮雪峰所畫(huà)的竟然是丁玲的眼睛,他恍然大悟。“美麗的眼睛”的故事就這樣不脛而走。
馮雪峰后來(lái)解釋說(shuō),心靈極度寂寞而渴望得到美的享受的人,常常出現(xiàn)幻覺(jué),他在上饒集中營(yíng)就有過(guò)類似的幻覺(jué)。在生命垂危時(shí),這眼睛曾給他以溫暖,以甜美,以希望,以力量。在其神志恍惚之際,他思念著遠(yuǎn)方的丁玲。丁玲美麗的眼睛喚起了馮雪峰求生的強(qiáng)烈欲望,并且以她母親般的堅(jiān)韌不拔的毅力激勵(lì)著他與病魔與敵人斗爭(zhēng)的信念。
經(jīng)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營(yíng)救,馮雪峰以治病為名被保釋出獄,后于1943年6月奉周恩來(lái)之召到達(dá)重慶,并參加中華全國(guó)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huì)。
自1937年丁、馮延安話別以來(lái),兩人在各自的政治生涯中都先后遇到了麻煩。馮雪峰1937年離滬回家隱居之舉,幾乎把自己原先中共上海地區(qū)負(fù)責(zé)人和左翼文化領(lǐng)導(dǎo)人的舉足輕重的地位喪失殆盡,并且由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yùn)。丁玲于1942年因一篇《“三八節(jié)”有感》惹出一場(chǎng)不小的風(fēng)波,幸虧毛主席出面保護(hù),才涉險(xiǎn)過(guò)關(guān),但免去了她副刊主編職務(wù),調(diào)離解放日?qǐng)?bào)社。從此,她在延安文壇的顯要地位被取而代之,厄運(yùn)接二連三。盡管兩人都有非同一般的特殊經(jīng)歷,但他們都對(duì)革命事業(yè)充滿著樂(lè)觀主義理想,甚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丁玲說(shuō):“我知道他當(dāng)時(shí)不痛快,他也知道我的艱難。”
“我永遠(yuǎn)在注視著你的創(chuàng)作”
后來(lái),他們兩人陸續(xù)有些書(shū)信往來(lái)。馮雪峰信上告訴丁玲,“我永遠(yuǎn)在注視著你的創(chuàng)作”。日本投降后,丁玲離開(kāi)延安準(zhǔn)備去東北,因熱河被國(guó)民黨封鎖,便留在張家口工作。馮雪峰給丁玲寫(xiě)了一封信,把自己新出版的著作寄給她。后來(lái),丁玲把此書(shū)轉(zhuǎn)給了毛主席。
1947年10月,在上海做文化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馮雪峰為正在河北阜平抬頭灣村創(chuàng)作《太陽(yáng)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編選了一本《丁玲文集》,并為之寫(xiě)了一篇題為《從〈夢(mèng)珂〉到〈夜〉》的后記。與20世紀(jì)30年代寫(xiě)的那篇評(píng)《水》的文章不同,這次馮雪峰全面評(píng)價(jià)了丁玲所走過(guò)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道路,并如數(shù)珍寶般評(píng)述了丁玲到延安后的新作《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shí)候》《夜》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成就。
馮雪峰始終期待著丁玲不斷地有思想精湛與藝術(shù)上乘的佳作問(wèn)世。等到他下一次要為丁玲寫(xiě)一篇書(shū)評(píng)時(shí),中國(guó)的歷史已翻到了新的一頁(yè)。
久違十多年后,馮雪峰與丁玲再次相見(jiàn)是在1949年6月下旬丁玲從東北到北京參加第一次文代會(huì)時(shí)。沒(méi)有客套話,馮雪峰的第一句話便是稱贊丁玲的《太陽(yáng)照在桑干河上》寫(xiě)得好!
1952年3月15日,《太陽(yáng)照在桑干河上》獲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xué)獎(jiǎng)金二等獎(jiǎng)。馮雪峰受作協(xié)托付,寫(xiě)了長(zhǎng)篇評(píng)論文章《〈太陽(yáng)照在桑干河上〉在我們文學(xué)發(fā)展上的意義》。他高度贊揚(yáng)道:
這一部藝術(shù)上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當(dāng)輝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帶來(lái)了一定高度的真實(shí)性的、史詩(shī)似的作品;同時(shí),這是我們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最初的比較顯著的一個(gè)勝利,這就是它在我們文學(xué)發(fā)展上的意義!
雖說(shuō)這不算是最早評(píng)論《太陽(yáng)照在桑干河上》的文章,卻是迄今為止評(píng)論這部史詩(shī)性巨著最重要的一篇,也是收入《馮雪峰文集》中第三篇評(píng)論丁玲創(chuàng)作的文章。
丁玲的成功與失敗、成就與缺憾,與馮雪峰的理論導(dǎo)航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從20世紀(jì)30年代起,丁玲的文學(xué)道路基本是按照馮雪峰為她設(shè)計(jì)的出路走的,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shuō),丁玲的創(chuàng)作,成亦雪峰,敗亦雪峰。
馮雪峰對(duì)丁玲是如此的嚴(yán)厲與苛求。是揚(yáng)棄自我還是拓展自我?這是長(zhǎng)期困惑丁玲創(chuàng)作的重大難題。丁玲酷愛(ài)莎菲,這是她藝術(shù)獨(dú)創(chuàng)性之顯現(xiàn)。自莎菲問(wèn)世以來(lái),評(píng)論界對(duì)她褒貶不一,尤其是左翼批評(píng)家格外苛刻,批評(píng)她所謂的創(chuàng)作壞傾向,即使是她最敬佩的文藝?yán)碚摷荫T雪峰也不例外。丁玲執(zhí)著地探索與追求,其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依然在往后的創(chuàng)作中頑強(qiáng)地顯現(xiàn),以至有人驚呼“莎菲女士在延安”!20世紀(jì)40年代,曾經(jīng)嚴(yán)肅批評(píng)過(guò)《莎菲女士的日記》的馮雪峰反思自己,重新指出:“《水》,以藝術(shù)對(duì)現(xiàn)實(shí)對(duì)象的深度和藝術(shù)的精湛而論,反而大不及以前的《莎菲女士的日記》。”
遺憾的是,往后的二十多年非常的日子里,丁玲、馮雪峰先后跌入他們都沒(méi)有想到過(guò)的政治深淵,他們的創(chuàng)作與評(píng)論出現(xiàn)了漫長(zhǎng)的空白,丁玲無(wú)法寫(xiě)出她的佳作,馮雪峰也無(wú)法再寫(xiě)評(píng)論丁玲的文章。
“雪峰這家伙,為什么要死呢!”
1957年底,丁玲與馮雪峰雙雙被定為“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tuán)”的主要成員,劃為“極右派”,開(kāi)除黨籍,撤銷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wù),取消原級(jí)別,兩人均按右派分子第六類處理。
彼時(shí),丁玲與馮雪峰都在北京,馮雪峰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丁玲在作家協(xié)會(huì),“老死不相往來(lái)”。其實(shí),兩人都默默地、緊張地關(guān)心著對(duì)方的命運(yùn)。丁玲后來(lái)回憶道:“五六年底或五七年初,傳說(shuō)五五年給我戴的反黨帽子要摘掉,我的歷史問(wèn)題又作了結(jié)論的時(shí)候,我覺(jué)得沒(méi)有什么可以顧慮的了,不會(huì)太多地連累人家的時(shí)候,我同陳明兩個(gè)人去看了雪峰。我們感到他生活很寂寞,沒(méi)有娛樂(lè),只有工作。我們兩個(gè)人買了四張戲票,給他們兩張,我們兩張,他們?cè)跇窍虑芭牛覀儍蓚€(gè)在樓上,我們看了一次戲。”多么難得的一次見(jiàn)面,但已經(jīng)無(wú)法讓時(shí)間回到過(guò)去那段美妙的時(shí)光,雙方都攜帶著家人,而且處于高壓的異常氣氛之中,無(wú)法開(kāi)懷暢談。
不久,形勢(shì)急轉(zhuǎn)直下。丁玲說(shuō):“我每天看著他挨批,人家批他,他在那里檢討。他聽(tīng)著人家批我,我在那里檢討。我們大約成了完全不相知道的人了。我實(shí)在不知道他有那么多的‘罪惡’,他也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罪惡’。我們成了陌生人。從此我們沒(méi)有再見(jiàn)面。”
馮雪峰再也沒(méi)有為丁玲留下任何文字。在罷官閑居的日日夜夜里,他曾經(jīng)和家人談起過(guò)魯迅,談起過(guò)胡風(fēng)……卻至死緘口不言丁玲。
丁玲卻不這樣,在北大荒那段漫長(zhǎng)而寂寞的歲月里,她和陳明談得最多的友人便是馮雪峰。1976年1月31日,馮雪峰因患肺癌不幸與世長(zhǎng)辭。正在山西長(zhǎng)治鄉(xiāng)下“養(yǎng)老”的丁玲驚悉馮雪峰逝去的消息,墮入了深深的迷惘中,她感到無(wú)限的悲愴。
馮雪峰走了,留給丁玲的是刻骨銘心的長(zhǎng)相憶。
1978年丁玲回到闊別二十年的北京。一次,她去看望好友樓適夷,兩人自然談到了馮雪峰,丁玲忽然發(fā)問(wèn):“雪峰這家伙,為什么要死呢!”遺憾中無(wú)不寄寓著她對(duì)馮雪峰長(zhǎng)達(dá)半個(gè)多世紀(jì)的深情摯愛(ài)。
1979年11月17日,馮雪峰的追悼會(huì)在北京西苑飯店大禮堂舉行。丁玲和陳明敬送挽聯(lián):
生為人杰捍衛(wèi)黨的旗幟
死猶鬼雄筆掃塵世妖狐
這短短二十字,生動(dòng)概括了馮雪峰不平凡的一生和崇高的品格,同時(shí)也凝聚著丁玲對(duì)這位“最懷念的人”的摯愛(ài)。白發(fā)蒼蒼的丁玲看到馮雪峰的遺像和骨灰盒,百感交集,和在旁的李伯釗抱頭痛哭。
1983年5月至6月,第一屆馮雪峰研究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在浙江義烏舉行。已是八十歲高齡的丁玲從北京趕來(lái)參加。在會(huì)上,丁玲作了題為《我與雪峰的交往》的發(fā)言,向與會(huì)者介紹了他倆長(zhǎng)達(dá)半個(gè)多世紀(jì)的友誼。就在那次會(huì)上,會(huì)場(chǎng)后門悄然走進(jìn)一位身材魁偉的男子,坐在主席臺(tái)上的丁玲忽然從座位上站了起來(lái),望著那個(gè)男子,愣呆了好長(zhǎng)一會(huì)兒。進(jìn)場(chǎng)者非別人,乃馮雪峰的二公子夏森,由于他長(zhǎng)得酷像其父,丁玲錯(cuò)以為是馮雪峰來(lái)了……
1986年2月9日,大年初一清晨。街頭一陣密似一陣的鞭炮聲,不時(shí)從窗外傳來(lái)。病中醒來(lái)的丁玲,感嘆地說(shuō)了一句:“雪峰就是這個(gè)時(shí)候死的。”馮雪峰是農(nóng)歷除夕家家戶戶準(zhǔn)備年夜飯的時(shí)候,被送進(jìn)首都醫(yī)院搶救的。他一直處于昏迷狀態(tài),一夜震天價(jià)響的爆竹聲都無(wú)法把他從昏迷中喚醒,終于在1976年1月31日大年初一上午心臟停止了最后的跳動(dòng)。臨終前,他放不下三個(gè)未了的心愿:“我沒(méi)有能活著回到黨的隊(duì)伍里來(lái),我沒(méi)有能寫(xiě)一本新的關(guān)于魯迅的比較完整的書(shū),我也沒(méi)有能寫(xiě)完關(guān)于太平天國(guó)的長(zhǎng)篇……我心里難過(guò)!”臨終前的不到二十個(gè)小時(shí),他還平靜地伏首于案前工作。
距她感嘆不到一個(gè)月,3月4日,丁玲逝世,圓了她幾十年前在《不算情書(shū)》里幻想的那一幕:心遠(yuǎn)遠(yuǎn)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盡情地說(shuō)我們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無(wú)從消滅的我們的愛(ài)情吧。同時(shí),也實(shí)現(xiàn)了馮雪峰四十多年前在上饒集中營(yíng)所許下的心愿:兩個(gè)世界的明暗的相銜!
丁、馮之誼,點(diǎn)燃了丁玲人生與文學(xué)道路上新的希望,喚起她對(duì)生命的熱愛(ài)、對(duì)人生的執(zhí)著、對(duì)文學(xué)的鐘情。丁玲珍視并攜帶著這種激發(fā)她無(wú)窮力量的情誼,走完了她的人生歷程,留給后世以肅然起敬、遐想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