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用的志愿
一
18歲的小孩懂得什么呢?當人生最大的一次決定權突然握在自己手中時,那一瞬間,降臨的只有迷茫。
2004年的夏天,空氣潮熱,連風都懶得攪動起一些漣漪。彼時,張雪峰尚未橫空出世,高三生在結束了查分、經歷了狂喜或失落后,緊接著就要考慮如何在志愿表上落筆。
“小孩兒,她懂個屁。”這句話雖然沒從父母叔伯的口中說出,卻從他們的眼睛里涌了出來,混著若有若無的陰影,以及對這個小孩兒未來的擔憂。是啊,小孩兒復讀了一年,分數竟然和去年考的一模一樣,可是去年那試卷的難度堪稱地獄級,當時這個分數能上三本,今年難度一降,同樣的分數,就只能上個大專了。那個時代,志愿表還是一張紙,估分用的也是一張紙,估了幾遍后,這小孩兒死了心,又嘆了口氣,白復讀了。但是,接下來全中國密密麻麻的院系名單擺在眼前,即便是大專,也要選一選自己的路呢。
可是,到底哪條路,才是正確的路呢?
命運是否也如紙一般?
在人生第一個分叉路口,填報志愿時,有的人落筆之時,筆酣墨飽,胸有成竹;有的人卻是提筆四顧,只剩茫然。風起于曠野,太稚嫩的眼睛望不到邊界,也看不透命運會開出怎樣的玩笑。
小孩兒出身于普通人家,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忙于生意,對她的成長一向持放養態度,也無力管束;親戚的關心亦有限,雖然好為人師是叔伯輩慣做之事,但突然要擔負起一個女孩未來的人生軌跡,這棘手的任務放在誰身上,都要掂量掂量自己說出口的話。所以,在那張志愿表前,一家子長輩久經社會歷練的面孔,看透人情世故的雙眼,都露出一絲不確定。
在建筑類國企工作的姨父說:“要么報建筑相關的吧,以后考個建造證,看能不能把你安排到我們公司來做事。”
當過多年待業青年的叔叔說:“什么專業不重要,隨便報一個,畢業后立刻要考公務員,你看,要不是我后來考上了,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兒呢。”
姑姑說:“將來的事很難說,你看,我們這輩人經歷過下崗。你啊,別想著什么專業能吃一輩子了,要隨機應變。”
小姨說:“要么學計算機吧,這個以后賺錢。哎,你是文科還是理科?”
爸點燃一支煙,白色的煙霧在潮熱的夜里冉冉上升,煙圈逐漸擴大,擴散,那是無解的答題框,一個接一個,升到空氣中,解一解肺里的嘆息。
媽也著急,她連最喜歡的撲克也不打了,一張仍然秀麗的臉擰成一團,走進小孩兒的房間,坐在床沿上,推心置腹地說:“你說你要復讀,給你復讀了,還是考成這樣。你知不知道我整夜都睡不著,想你未來該怎么辦……”媽指望自己的話如千斤重錘,一舉將懵懂的小孩兒錘得神志清明,在人生道路上奮起直追。但是小孩兒就是小孩兒,小孩兒能怎么辦?
這個小孩兒,一方面模模糊糊意識到這次抉擇將直接改寫自己今后的人生軌跡;另一方面,又實在懶得也無力想出更好的解決方案,甚至還有一點兒肆意的自暴自棄:我就是理科很差,我能怎么辦?
是的,更糟糕的是,小孩兒是一個極度偏科的文科生,英語和數學不好,但語文的作文寫得興致來了,卷子的空間都不夠她發揮。這樣一個女生,從小就喜歡寫字,習慣了作文被當成范文,習慣了將青春期的心事全部寫入日記后上鎖,習慣了在面對面時訥言,在書寫時卻如魚歸大海,鳥上青霄。她習慣了被文字賦予力量,她深知這份自由和感知是一種甘美的天賦,因此便任由它引領自己一步步攀登至最舒適的領區域,這實在是一種驕傲的任性,當然,也是懶惰。
話說回來,這么一個人,學計算機這種熱門且能在不久的將來帶來經濟回報的理科專業,自然是沒資格的;建筑她一竅不通,毫無認知。比起那些線條和計算,她更熟悉的是《春江花月夜》的輪回與無限,《巴黎圣母院》的浪漫和悲情,《約翰·克里斯托夫》的英雄主義這些完全無用的東西。
對,雖然父母沒有說出口,但是在2004年,商業思維和價值變現普及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讀文學,有什么用?
爸忘記了,他在20歲出頭時也是個文學青年;媽也忘了,是她給上小學一年級的小孩兒買了第一本俄羅斯小說。只是,他們曾經對文學的愛在生活日復一日地打磨中失了光彩。“有什么用”的想法,是他們面對命運委婉的辯駁。
那是一個如此平凡的夏夜,但之于高考之后的每個畢業生,都蘊含著千鈞之力。如今,20年過去,我卻一點兒都想不起,爸媽到底對我的志愿說了些什么。
習慣放手的爸媽實在不敢為小孩兒的未來做主—萬一她將來懊悔怎么辦?她恨我們怎么辦?這反而成全了我的自由。最終,那份志愿報得既隨意又理所當然,我選擇了中文系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在一所不起眼的大專學校。
當不知道走什么路時,我選擇了最熟悉的路,既然那條路在童年和少年都予我以愉悅、暢快和成就感,在荒蕪的成長歲月里給我以理解和共鳴。朦朧中,我總有一絲感覺,走上這條路,即便迷路也迷不到哪里去。
爸說:“好啊,女孩子上師范,將來當老師,安穩。”他們還是為孩子惦記著一份安穩。他們選擇性忽略了中文系。
二
可是,畢業后,我沒順著既定的軌跡當語文老師。大學時光雖然只有三年,圖書館的書卻幫我打開了一扇又一扇通往廣闊精神世界的大門,文字仍然是我孤寂時最能依傍的伙伴。因為不再有升學壓力,原本孤僻訥言的我慢慢放開,開始參加語言類比賽,成為學生記者,組織活動,上電視,發表作品。喜歡的事物確實可以帶你去往你原本未曾想象卻在內心惦念過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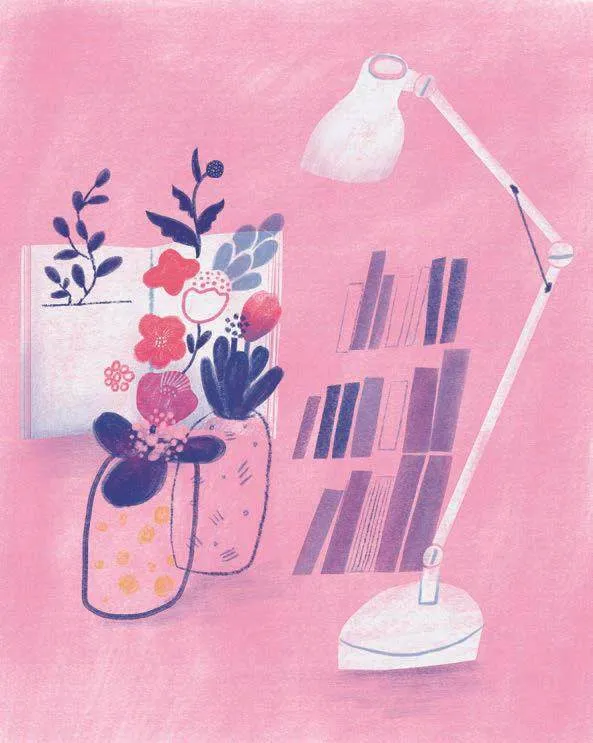
畢業后,學歷一般的我,自然不可避免地遭遇擇業瓶頸。一片混沌的擇業期長達半年,而半年后機緣巧合,還是因為文字上的表現,得到了前輩的賞識,我得以進入廣告行業,從此一路從文案成長為國際4A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和騰訊的創意專家,至今,依然在寫。
如今,距離那個潮熱的夏夜,已20年。這些年來,每過幾年,時代都刷新一次財富密碼,總有一批幸運兒洞悉時代先機,踩準變化。時代主音交錯更迭,文學,似乎越來越“沒用”了。
可是,為什么在繁花落盡,烈火烹油歸于沉寂之時,在一波又一波經濟浪潮風起云涌的間隙,總有人會懷念曾經人與文學的親密呢?那不是懷舊,而是懷念一種純粹,人們不恥于談論文學,每個人都能在文字中,找到迷茫時的落腳點,失落時的坐標系。錢能解決生活中80%的問題,但是“無用”的文字,能使那20%的精神空白得以填滿,而這20%,決定了人生不會在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中浪蕩、覆沒。
是這樣的。文字引領著我,陪伴著我,在進入社會之后,它是我立足世界的生存工具,我精神世界的導航燈,我穿行世界的一葉扁舟,雖小,但穩。
所以,那怎么能是一個無用的志愿呢?
在人生的第一個分叉路口,當決定權沉甸甸壓在手中,當夏天看似沒有盡頭,小孩兒終究還是循著內心一點點微弱的信號,撿起地上的一縷線頭,用漫長的20年捋出一條線索,牽著它,穿過了密不透風的叢林。
大人永遠無法想象,一個暑假就能成就一次蛻變,而蛻皮的裂口只能由孩子自己扯開。而“有用”和“無用”之間的溝壑到底該不該彌合,如何彌合,也永遠沒有定論。大人們用被現實錘煉出的眼光去判斷何為合適,但孩子內心的赤誠在那個夏天還是振蕩出一絲強音—去選擇你想選擇的那條路。
小孩兒,永遠不要對自己說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