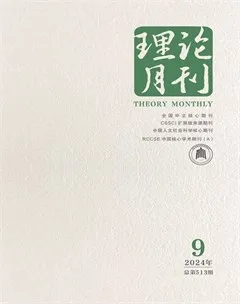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理解
[摘 要] 盡管政治義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概念,但是在對政治義務概念的理解上存在著分歧。不過,分歧并沒有消解政治義務概念,反而塑造了政治義務概念的理解空間。在這一空間中,我們主要以“我對誰負有政治義務?”“政治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嗎?”和“政治義務是一種獨立于內容的義務嗎?”三個問題為規范性導向,將國家認同納入政治義務概念的理解當中,進而把政治義務概念理解為公民出于國家認同的理由而服從國家的一種道德義務。當然,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或許存在不確定性,但卻值得嘗試,畢竟我們致力于在一種可能性政治的范疇內尋求對政治義務概念的理解。
[關鍵詞] 政治義務;道德義務;國家認同;概念聯姻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9.007
[中圖分類號] D6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09-0055-09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愛國主義義務研究”(22BZZ001)。
作者簡介:徐百軍(1983—),男,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政治義務不是一個新鮮的政治論題,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他的戲劇《安提戈涅》(Antigone)中就通過訴諸某種高于人定法或實證法的高級法來質疑政治義務1。而柏拉圖(Plato)的《克力同》(Crito)則對政治義務進行了更具原創性的探討,他為當代的同意理論、效用理論、公平游戲理論等諸多政治義務主張奠定了思想基調2。在彼得·斯科克(Peter Stirk)和大衛·韋戈爾(David Weigal)看來,“這些主張都能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口中發現,沒有一絲新意。有新意的是爭論使用的詞匯發生了轉移”3。顯然,這與懷特海(A.N.Whitehead)的下述評斷若合符節:“對構成歐洲哲學傳統最可靠的一般描述就是,它是對柏拉圖學說的一系列腳注。”4就此而言,托馬斯·格林(Thomas H.Green)在1879—1880年的牛津大學演講中將“政治義務”作為一個概念術語明確提出來也僅僅具有形式上的新意5。對格林來說,政治義務的概念要服務于“發現服從法律的真實基礎或正當理由”這一目的,在內涵上它包括對統治者的義務、公民對國家的義務以及由政治統治者強加的個體之間的相互義務1。從政治義務概念的內涵上來說,格林似乎把“義務是對誰而言的?”這一問題視為政治義務的中心論域。
盡管格林的政治義務概念引起了西蒙斯(A.John Simmons)的注意,但是西蒙斯并沒有為這一概念投入更多的關注。在西蒙斯看來,格林在他的政治義務概念中貫徹了一種新黑格爾主義政治理論,他基于對政治生活或政治概念的根本誤解而提出了一個唯心主義的政治義務概念。對西蒙斯來說,這一政治義務概念當然是錯誤的。因而,當西蒙斯認為格林的政治義務學說建基于一個錯誤的政治義務概念之上的時候,他對其失去重述或批判的興趣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2。為了探明政治義務的性質,西蒙斯提出了一個公式化的政治義務概念:政治義務就是公民對其所在國家的政治制度加以“支持和遵從”的一種義務3。那么,公民應該怎樣對其所在國家的政治制度加以“支持和遵從”呢?西蒙斯明確指出,他所使用的“支持和遵從”借自羅爾斯(John Rawls)的說法,那么,羅爾斯究竟對于“支持和遵從”持有一種什么樣的看法?
在談及自然義務時,羅爾斯給出了“支持和遵從”的兩種解釋:一是在“正義制度存在并適用于我們”的情境下,“支持和遵從”體現為我們對正義制度的服從并在其中盡我們的一份職責;二是在“正義制度不存在”的情境下,“支持和遵從”體現為我們在不需要付出高昂代價時幫助建立正義制度4。實際上,羅爾斯在對自然義務的“支持和遵從”進行描述時,預設了一個背景性條件:對正義制度的認同。所以,當西蒙斯說他是在羅爾斯意義上使用“支持和遵從”之時,就表明他一并接受了羅爾斯預設的這一背景性條件。稍有不同的是,西蒙斯將對正義制度的認同修改為對國家政治制度的認同,因為他要考察的是政治義務而不是自然義務。根據西蒙斯的表述可以推斷,公民認同他們自己的國家原本就是他們應該擔當的一項政治義務。當然,有人可能會質疑:國家認同能否被納入政治義務概念?將國家認同納入政治義務概念的理解,實現的究竟是政治義務概念的“去問題化”還是“再問題化”?政治義務是一個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5。為了獲得一個更清晰的政治義務概念,有必要對其進行一種以問題為導向的規范性考察。本文著重考察政治義務概念理解中的三個導向性問題:一是“我”對“誰”負有政治義務?二是政治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嗎?三是政治義務是一種獨立于內容的義務嗎?
一、“我”對“誰”負有政治義務?
在這個問題中,“我”是政治義務主體,“誰”是政治義務相對人,而政治義務呈現的則是兩者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如果我們不能精準地確認政治義務主體和政治義務相對人,那么政治義務概念只能被視為一種胡亂的囈語。通常,只有具備公民身份的“我”才有資格成為政治義務主體。正如西蒙斯所指出的那樣,“政治義務一直以來總是與公民觀念緊密聯系,也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在最低意義上成為‘好公民’的義務”6。在萊斯利·格林(Leslie Green)那里,我們也能找到與此相類似的表述:“政治義務是好公民的以要求為中心的方面,是一個以價值為基礎的概念。”7盡管人們普遍承認公民是政治義務主體,但是我們卻不能用“公民義務”來稱呼“政治義務”,畢竟它們之間存在著一條“道德間隙”。在日常生活中,公民義務主要指涉的是從屬于公民地位的職責,或者說,公民義務就是公民的崗位責任,而“職責的存在,從未(自動地)建立起道德要求”1。因而,我們從負有公民義務這樣一個與道德無涉的事實出發,并不能推導出政治義務的道德要求。換言之,公民義務的存在,不會對公民擔當政治義務的行為施加道德壓力。當我們在概念上混淆了公民義務與政治義務的時候,我們很可能已經忘卻了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警告:從“是”中不能推出“應該”2。在彼庫·帕雷科(Bhikhu Parekh)看來,政治義務要比公民義務具有更顯著的政治性,公民義務不能將政治義務全部覆蓋,而積極參與集體事務的義務與促進共同體及其同胞福祉的義務就是兩類典型的不同于公民義務的政治義務3。
對于政治義務主體的識別,人們鮮有分歧,而分歧更多體現在對于政治義務相對人的識別上。大體而言,人們在政治義務相對人是“誰”的問題上廣泛接受下述三種答案:統治者、政府和公民同胞4。統治者、政府和公民同胞完全可以被國家所統攝,因為它們都是國家的“所有物”。在《政治哲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一書中,喬納森·沃爾夫(Jonathan Wolff)指出,“說某人具有政治義務,至少等于說,他在正常情況下,有遵守國家法律的義務,包括繳納應付的稅款。其他義務可能也包括在內:如果需要的話為保衛國家而戰,或許還要表現得愛國,甚至找出并揭露國家的敵人”5。按照政治義務的狹義/廣義分類標準,沃爾夫歸屬于廣義政治義務觀的理論陣營,因為他倡議的政治義務不僅關心公民的回應性要素,還關心公民的積極性要素6。在沃爾夫的政治義務概念中,回應性要素體現為遵守國家法律的義務,而為保衛國家而戰的義務、愛國的義務以及找出并揭露國家的敵人的義務則屬于積極性要素。
不可否認,廣義政治義務觀向公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人可能會問:公民為何會覺得自己有義務去為保衛國家而戰、愛國以及找出并揭露國家的敵人?我們能說是源于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嗎?對于公民來說,只有得到他們認同的國家才值得他們去保衛、熱愛以及找出并揭露敵人,或者說,只有得到他們認同的國家才有資格向他們提出這些要求。沃爾夫讓我們相信,廣義政治義務觀完全可以將國家認同納入進來,且不會造成我們對政治義務概念的認知障礙。然而,當很多人認為意義和價值的中心存在于私人生活而非社會生活當中時,他們必然會贊同狹義政治義務觀而拒斥廣義政治義務觀,畢竟狹義政治義務觀要比廣義政治義務觀更符合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概念需要,廣義政治義務觀充其量只是一種值得稱贊的分外行為7。
客觀地講,狹義政治義務觀與廣義政治義務觀分別呈現了兩種不同的政治義務概念:前者對政治義務概念進行消極的理解,政治義務被稀薄化為一種守法義務8,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義務的防御能力,因為當守法義務遭到反駁之后政治義務也隨之被否定;后者對政治義務概念進行積極的理解,政治義務被厚重化為一種認同義務,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政治義務的防御能力,因為認同義務將守法義務涵攝為一個子項,當守法義務遭到反駁之后政治義務并不會隨之被否定。如果說狹義政治義務觀呈現的是一種弱政治義務概念,它引導人們更多關注政治義務的證成問題,那么廣義政治義務觀則呈現的是一種強政治義務概念,它引導人們更多關注政治義務的擔當問題。雖然我們并不否定弱政治義務概念,但是我們更肯定強政治義務概念,這鮮明地體現為我們在政治義務的概念理解當中引入了國家認同的考察進路。在強政治義務概念的引導下,我們可以暫時跳離麥克弗森(C.B.Macpherson)所謂的“占有性個人主義”1的思維框架來對國家、公民、認同、政治、義務等諸要素進行重組性思考。
理解政治義務的概念,不僅需要我們明晰何為政治義務主體與政治義務相對人,而且需要我們明晰政治義務主體與政治義務相對人之間的關系。那么,作為政治義務主體的公民與作為政治義務相對人的國家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呢?實際上,從“公民對國家負有政治義務”的話語表述中,我們自然可以推斷說公民與國家之間存在著一種服從關系。或者說,“服從”概念是我們進入政治義務概念的一條重要門徑。喬治·克洛斯科(George Klosko)就指出,在政治義務理論所要回答的一般問題和具體問題當中,“服從”都處于中心位置2。然而,“服從”并非一個簡單明了的概念,我們需要小心謹慎地將它與“順從”“屈從”等概念區分開來。相比于“順從”和“屈從”,“服從”具有更強烈的“自愿性”3。只有當公民基于自身判斷的獨立性而對國家所施加的政治義務自愿加以擔當時,我們才能將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稱為服從關系。當公民服從國家的要求而自愿擔當其施加的政治義務時,這種內在的、自覺的服從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在政治義務概念當中,國家(政治義務相對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公民(政治義務主體)的服從對象,是因為在公民眼中國家是一種權威,而“權威是以認同為前提的,一種權威的存在必須以獲得廣泛的認同為前提”4。由此而言,我們與其從公民與國家之間的服從關系去理解政治義務概念,不如從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認同關系去理解政治義務概念。
二、政治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嗎?
在這個問題中,政治義務是否具有道德性質成為爭議的焦點。根據相關的爭議性主張,我們可以清晰地辨識出兩種不同的政治義務概念:一種是道德的,一種是非道德的。就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而言,政治義務被視為道德要求而非制度要求。一方面,承認政治義務的道德義務屬性符合人們的直覺,因為“許多人都會感覺到自己以某種特殊方式與其政府存在的關聯,不僅僅只是‘感情的紐帶’,而且是道德的紐帶。盡管他們經常大聲抱怨(并非沒有道理)政府的種種缺點,不過他們感覺自己無論如何還是有義務支持本國的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政治機構,服從本國的法律”5。另一方面,承認政治義務的道德義務屬性也符合傳統思想家在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不同)領域中構想政治義務問題的本意6,“如果政治義務僅僅是法律要求我們做的東西,那么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對法律條文的解釋、注釋而達到目的,這同樣和政治哲學無關,很多人也會認為這屬于法理學尤其是部門法學(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等)的研究領域”7。當然,在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中并非不存在制度要求,只不過制度要求通常會經過道德化處理。正如理查德·達格(Richard Dagger)所說,法律制度能夠被我們賦予一種道德力量8。
實際上,在大部分學者那里,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都是自明的,這種自明性的預斷讓他們排斥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至于自明的原因,他們的解釋不是含糊其詞,就是充滿主觀臆斷。對此,我們有必要采納國家認同所提供的解釋策略。正是在國家認同的幫助下,我們從多種道德選項中選擇了政治義務的擔當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認同為政治義務的概念理解提供了一種價值的源泉。當我們在政治義務題域內采取一種國家認同時,我們意欲讓國家認同來構造我們的生活方式。用夸梅·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的話來說,一旦國家認同被我們所采取就變成了我們的認同,而我們的認同有其內在的模式,這種模式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思考我們的生活,而且能夠幫助我們創造團結的形式1。比如說,“我”認為自己是A國的公民,而另外一個人也認為自己是A國的公民,僅憑這個事實,“我”就傾向于與他一起擔當A國所施加的政治義務,或者為他而擔當A國所施加的政治義務。然而,國家認同的解釋策略并不能讓所有人都滿意,有些人就質疑:政治義務的道德價值對于國家認同來說難道不是內在的嗎?確實,政治義務的道德價值是那些擁有國家認同的人必須去考慮的價值,但它們卻并不符合那些不擁有國家認同的人的價值需要。作為國家認同的承擔者,“我”通常會把政治義務的擔當作為“我”的具體目標,而“在我的具體目標中一種認同概念的出現也許部分地解釋了為什么我會有那樣的目標”2。無論是從國家認同到政治義務的正向解釋,還是從政治義務到國家認同的反向解釋,都與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須臾不離。顯然,在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當中,“政治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嗎?”已經淪為一個偽問題。
盡管人們普遍接受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消除了所有的理論分歧。客觀地講,在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中人們通過爭論焦點的轉移而開辟了新的爭論空間,他們在失去了對政治義務是否具有道德性的爭論興趣后,將更多的理論精力放在了政治義務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道德性之上。在新的爭論空間當中,有的人認為政治義務是一種絕對的道德義務,而有的人則認為政治義務是一種相對的道德義務。對于前者而言,政治義務的道德約束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被推翻,人們必須無條件地擔當政治義務,我們可以將之稱為一種本質論的政治義務概念,它實質上更契合于共和主義的思想脈絡;對于后者而言,政治義務的道德約束力在特定情況下則允許被推翻,人們必須有條件地擔當政治義務,我們可以將之稱為一種工具論的政治義務概念,它實質上更契合于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如果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來考察,就能夠更為深刻地辨識出兩種道德版本的政治義務概念的優劣之處。當我們承認政治義務概念的道德絕對性時,我們所認同的國家便是一個能夠發號絕對道德命令的聯合體,而在無條件認同的基礎上承擔它向我們施加的政治義務能夠更好地保護我們自身,畢竟“國家乃是人民的事業”3。然而,獲得我們無條件認同的國家在向我們施加政治義務時有可能違背我們的道德自主性,我們極有可能會被推向極權主義的政治深淵。當我們承認政治義務概念的道德相對性時,我們所認同的國家便是一個發號相對道德命令的聚合體,而在有條件認同的基礎上承擔它向我們施加的政治義務,同樣能夠更好地保護我們自身,因為國家建基于人民的同意之上,而“當每個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個政府統轄的國家的時候,他使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每一成員負有服從大多數的決定和取決于大多數的義務”4。問題是,如果說獲得我們有條件認同的國家在向我們施加政治義務時必須首先接受我們的道德自主性審查,那么我們就可能將個人理由置于國家理由之上,甚至為國家帶來分裂主義5的隱患,而掉入無政府主義的政治陷阱極有可能是我們最終的宿命。究其實質,兩種道德版本的政治義務概念關聯著不同的“人”的概念,我們的取舍似乎難以遵循客觀標準。當然,我們也并非一定要在絕對/相對的兩分法之間糾纏,自由共和主義或者共和自由主義就為我們提供了第三種政治義務概念。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究竟是將政治義務視為一種絕對道德義務,還是將政治義務視為一種相對道德義務,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在實踐過程中,我們在進行選擇時就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其中至為關鍵的就是各個國家的國情,有的國家適用于道德絕對性版本的政治義務概念,而有的國家則適用于道德相對性版本的政治義務概念。即便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可能對兩種道德版本的政治義務概念有不同的選擇需求,而政治義務的道德絕對性和道德相對性可能會交替出現在人們認同國家的政治過程當中。
除了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之外,我們還能從少數學者那里找到一種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在托馬斯·麥克弗森(Thomas McPherson)看來,如果我們將政治義務與道德義務置于比較視野下加以考察的話,那么基于兩者的差異性,我們就應該否認政治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麥克弗森認為,政治義務與道德義務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道德義務的擔當具有自愿性,而政治義務的擔當則具有強制性1;二是道德義務的擔當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行為,而政治義務的擔當則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行為2。對此,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政治義務與道德義務確實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麥克弗森在理論上重構了政治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的差異性。對麥克弗森來說,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原本就是他在探究政治義務問題時所預設的一個概念前提,而重構政治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的差異性就顯得至為自然和順當。從邏輯學的角度來看,麥克弗森顯然在演繹推論形式上犯了“預期理由”的錯誤。然而,人們的批判注意力并非僅僅集中在麥克弗森的邏輯錯誤之上,約翰·霍頓(John Horton)就批判麥克弗森在重構政治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的差異性時存在“誤用”行為3。而西蒙斯則批判麥克弗森沒有提出一種明晰的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他說麥克弗森壓根就不甚了解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的作用或者特性,至少麥克弗森沒有像大多數人那樣去理解“義務”一詞的實際意義4。如果說麥克弗森提出了一種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那么我們也只能說這是一種否定意義上而非肯定意義上的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
有人可能會質疑:一種肯定意義上的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究竟是否存在?從瑪格麗特·吉爾伯特(Margaret Gilbert)的復數主體政治義務理論中,我們可以獲得一個肯定的答案。在吉爾伯特看來,社會群體是由其成員彼此之間通過共同承諾的方式構建出來的一種“復數主體”5,而共同承諾的約束力賦予“復數主體”規范性力量,畢竟“復數主體不是在累加某些去做A的個體承諾的基礎上形成的……而是通過每個個體所作出的、意在作為一個團體而共同行動的對稱且相互的承諾而形成的”6。對于吉爾伯特來說,國家只不過是一種超大型的社會群體,因而,作為“復數主體”的國家中的公民成員通過某種形式的共同承諾便負有了政治義務。在吉爾伯特那里,她的基于共同承諾的政治義務概念建基于日常生活和日常概念之上,這使得它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道德義務概念。吉爾伯特提出了一種肯定意義上的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因為它并不要求行動者具有作出大量復雜化的道德判斷的能力1,“只要人們是在共知的前提下作出了某種共同承諾,這種承諾就會使他們負有義務,并且,該義務是獨立于承諾的內容、背景和后果而存在的”2。按照吉爾伯特的論述,國家認同作為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同樣可以為她的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提供建構基礎,因為人們完全可以在“總群共知”3的情境下作出認同國家的共同承諾。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建基于共同承諾之上的以認同國家為核心內容的政治義務并不是一種道德義務,它實質上是一種“真正的義務”,也就是一種事實義務4。這種義務不僅為公民的擔當行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還預設了一個比道德性領域更為宏大的規范性領域5。吉爾伯特肯定意義上的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仍舊無法擺脫被批判的命運。例如,塔爾伯特·博厄(Talbot M.Brewer)就在區分外在主義承諾與內在主義承諾的基礎上指出,由于吉爾伯特沒有考慮到國家中公民成員所要擔當的政治義務與他們的動機、價值觀或者實質性確信之間的內在關聯,她無法提出一種完滿的非道德的政治義務概念6。不可否認,如果我們對國家中公民成員認同國家的動機、價值觀或者實質性確信詳加考察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發現不同的認同動機、價值觀或者實質性確信將映射出不同的政治義務的擔當格局。
三、政治義務是一種獨立于內容的義務嗎?
在這個問題中,核心爭論聚焦于政治義務的擔當理由究竟是源于公民對國家所要求的行動的道德價值的個體評價,還是國家所要求的行動這一事實本身。如果我們承認政治義務具有“內容獨立性”特征,那么我們就必須接受三個要件:(1)公民的主體性被預先排除在政治義務的擔當過程之外;(2)國家擁有發布權威性命令的道德資格;(3)公民認同他們的國家。就(1)而言,政治義務的擔當是一種與公民的個體意志無涉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義務是無條件的7。就(2)而言,國家所施加的政治義務只是它所發布的某種權威性命令,只有確信國家擁有發布權威性命令的道德資格,才能在道德上為公民提供政治義務擔當的正當性理由。相比于(1)和(2)的要求,(3)則要更加隱晦。不過,這并不意味著(3)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要件,因為僅有(1)和(2)并不足以讓我們將政治義務界定為一種獨立于內容的義務。盡管(1)和(2)能夠引導我們去關注國家所要求的行動這一事實本身,但是離開(3)它也只不過是一個外在于公民行動的事實而已。換句話說,只有在考慮(3)的情況下,(1)和(2)才能讓公民將國家所要求的行動這一事實本身內化為他們擔當政治義務的一個充足理由。由此可見,在內容獨立性的政治義務概念當中國家認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性要件。
在國家認同的情形下,國家的意圖理由對于公民的政治義務擔當具有重要作用。不過,從性質或者特征上來看,國家的意圖理由對于公民的政治義務擔當理由具有獨立性。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將國家的意圖理由簡單地等同于公民的政治義務擔當理由。那么,國家的意圖理由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理由呢?在這個問題上,哈特(H.L.A.Hart)或許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資參考的分析進路。根據哈特的論述,我們可以將施加政治義務的國家恰當地理解為一個命令者,而“命令者有關做某種行為的意志表達,意圖將聽者對做此種行為是否具有正反兩方面價值的任何獨立的慎思加以排除或者切斷。因此,命令者的意志表達并不打算在聽者的慎思之中充當一個行動理由,更不是作為最強烈的或支配性的理由,因為那將假定獨立的慎思會繼續下去,而這有違于命令者的原本意圖”1。哈特認為,“這精確地意味著命令是在‘要求’行動并稱命令是言說的一種‘專斷的’形式。事實上,‘專斷的’一詞的確意味著切斷慎思、討論或者爭辯,而包含這種含義的語詞是從羅馬法進入英語的。在羅馬法中,它被用來指稱特定的程序步驟。一旦實施了這些步驟,進一步的爭辯便被排除或者禁止。如果我們記住這一點,那么我們就能夠將命令者意圖他的聽者在行動時擁有的這些理由稱之為‘專斷性’理由”2。在哈特那里,“專斷性”理由是一種國家理由,它要求公民將國家的意志而非他們的個人意志作為擔當政治義務的行動指南。哈特明確表示,他對“專斷性”理由的分析更多地吸納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而非邊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成分。例如,在《利維坦》(Leviathan)的第二十五章中,霍布斯就曾指出,“當一個人說‘得如何如何’或‘不得如何如何’時,如果除了說話者的意志之外別無其他理由,便是命令”3。不過,哈特并沒有對“專斷性”理由作過多明確的解釋。自然地,人們就會追問:公民在擔當政治義務時為何只服從國家所提供的那種“專斷性”理由?當然,我們可以通過理論設想的方式來幫助哈特制定多種解釋方案,而在諸多解釋方案中基于國家認同的解釋則呈現出更大的解釋力。我們傾向于認為,公民認同國家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公民對國家進行“專斷性”賦權的過程。
對于內容獨立性的政治義務概念來說,運用“專斷性”理由表明,公民在擔當國家施加的政治義務時進行了實踐推理。在政治義務的實踐推理過程中,哈特告訴我們存在著兩種理由:一種是個人的慎思理由,另一種是國家的意圖理由。只有當后者對前者發揮專斷的“慎思排除”功能4時,我們才能將政治義務視為一種獨立于內容的義務。問題是,國家的“專斷性”理由是如何發揮“慎思排除”功能的呢?依照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的觀點,如果我們將兩種理由置于理由位階理論的理解框架下,那么問題便會迎刃而解。當公民在政治義務的實踐推理過程中僅僅考慮個人的慎思理由時,他們的政治義務擔當就是根據理由的平衡而做出的一種應然性選擇。所謂理由的平衡,指的是個人的所有慎思理由都具有公平的競爭性,都有機會來影響公民的政治義務擔當。在這個意義上,個人的所有慎思理由都是一種“一階理由”。正如萊斯利·格林所說,“一階理由是通常的行動理由,比如理想、欲望、利益或需要。這些理由之間的沖突是通過比較它們的相對重要性、權衡不同的考慮因素來解決的(如果能夠解決的話)。在這一層面上,一條理由只有在重要性上被同一層面的另一條理由壓倒時,才會被它推翻”5。由此而言,如果兩個理由處于不同層面,那么它們當然就不具有可比性。正因為哈特認定國家的“專斷性”理由與個人的“慎思性”理由并不處于同一可比層面上,所以他否定“專斷性”理由是一種最強烈的或者支配性的“慎思性”理由。由于理由的性質差異,國家的“專斷性”理由應該屬于拉茲所謂的一種“二階理由”。在拉茲看來,“當且僅當一個人因為他相信p是他做?的理由,從而做?的時候,他因理由p而做?。當且僅當他不是因理由p而做?的時候,他就會因p而不做?。換言之,如果一個人不做某個行動,或者不是因為某個理由而做這一行動,那么他就是因為這一理由而不行動。‘不行動’這里在廣義上使用,它不是說行動者因為這一理由而故意不做。二階理由是因為某個理由而行動或者因為某個理由而不行動的任何理由。排他性理由則是因為某個理由而不行動的二階理由”1。基于拉茲的論述我們自然可以推斷說,公民在進行政治義務的實踐推理時個人理由與國家理由之間的沖突實質上就是一階理由與二階的排他性理由之間的沖突,而沖突的解決總是遵循排他性理由優先的普遍原則。然而,普遍原則的遵循并非一帆風順,畢竟一個二階的排他性理由很可能與另一個二階的排他性理由發生沖突。比如,在具有少數族屬身份的公民那里,雖然族群理由與國家理由都是一種二階的排他性理由,但是在特定情境下族群理由可能會阻止他們根據國家理由而擔當政治義務。確切地說,族群理由要比國家理由更屬于一種“否定的二階理由”2。事實上,國家理由從未被像族群理由這樣的二階理由所擊敗過,在政治義務的實踐推理過程中國家理由就是一個不敗的理由,而只有不敗的理由才能成功地發揮“慎思排除”功能。因而,在綜合考慮一切事情之后,公民就應該按照國家理由這一不敗理由的要求去擔當政治義務。至于國家理由為何具有不敗性,那是因為公民認同他們的國家。換句話說,在政治義務的擔當過程中國家的不敗動力源自公民的認同力量。沒有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內容獨立性的政治義務概念也只不過是一種空中樓閣。
四、余論: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
我們以“我對誰負有政治義務?”“政治義務是一種道德義務嗎?”和“政治義務是一種獨立于內容的義務嗎?”三個問題為導向對政治義務概念進行了規范性考察。在具體的考察過程中,我們嘗試性地將國家認同納入政治義務概念的理解當中,并將政治義務的概念界定為公民出于國家認同的理由而服從國家的一種道德義務。問題是:通過國家認同來理解政治義務概念是廓清了還是模糊了政治義務概念呢?或者說,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是否存在失jq9/a3ujpweXrl5olZngGqzWh3OWgcjS6HlWRszsxY8=敗的風險呢?
客觀地講,不同于日常生活中聯姻關系的法律性,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具有顯著的政治性。從政治性的角度來說,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需要達成兩個理論目的:一是用政治義務的擔當來填充國家認同的內容,為國家認同提供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抓手”;二是用國家認同來規制政治義務的擔當,為政治義務提供一個規范性的擔當理由。不過,我們并不能確保上述兩個理論目的一定能夠達成,而且我們不能確定它們自身的正確性。因而,我們對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預留了必要的反思空間,或者說,我們將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界定為一種反思性關系。經過必要的反思,我們會發現:一方面,國家認同讓我們擺脫了政治義務概念理解中“老問題”的困擾;另一方面,國家認同又讓我們陷入了政治義務概念理解中“新問題”的旋渦。當然,反思不是否定,而是批判的肯定。經過反思,我們看到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是脆弱的,它需要人們投入更多的經營精力來維系。如果人們失去了維系的耐心,那么終結便是它的最終歸宿。
在此,需要申明兩點:第一,盡管通過國家認同與政治義務的概念聯姻來廓清政治義務概念存在失敗的風險,但是我們認為值得冒險一試。我們的態度是鮮明的,而非曖昧的。第二,我們對政治義務概念的廓清工作并沒有超出一種可能性政治的作業范疇,因為我們毫不吝惜對于想象的運用。正如艾麗斯·楊(Iris Young)所言,“每種社會現實都呈現了它自身未能實現的諸種可能性,通常被體驗為匱乏和欲望。規范和理念源于一種自由表達的渴望:這種方式并不是它的必然選擇,它還可以選擇其他方式。想象是將所是的經驗轉化為追求所能是的能力,這種能力實現了思想的解放,進而形成了理念和規范”3。
責任編輯 申 華
技術編輯 王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