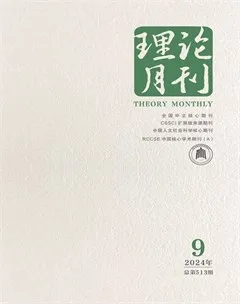身體與“無為”:無為—政治的治理術與自發秩序
[摘 要] 孔子所說的“無為而治”,不僅包含一種特殊的治理術,而且隱含著對于政治運轉中自發秩序的某種肯定。“無為而治”中的自發秩序,揭示了無為—政治得以自發運轉的深層機制和核心奧秘。不同于建構與演進之分下哈耶克式的自發秩序,無為—政治的自發運轉直抵身體的層面,整體奠基于一種獨特的由人的身體予以確證的自發秩序之上。其中的自發性依賴于身體能力的充分實現,人與人在身體之間的相互感通中形成緊密的身體性關聯。君主的修身牽動著自發秩序的運轉,修身能夠讓君主在具體的行事中彰顯出己身之“德”,取得一種針對人的身體層面起效的教化效果,實現“不令而行”的自發性。
[關鍵詞] 身體;“無為而治”;自發秩序;治理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9.008
[中圖分類號] D08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09-0064-12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來黨加強基層政治建設的實踐與經驗研究”(22ZDA033)。
作者簡介:李宸(1991—),男,博士,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博雅博士后。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對“無為而治”章的詮釋,歷來就是一處容易引發爭鳴的地方,其中所產生的分歧,事實上可被歸因于諸種觀點背后對“而”字的理解差異。這個“而”字在對“無為而治”的整體闡釋中極為重要,規定著整個“無為而治”章的內在邏輯。根據“而”的不同含義,可以將代表性的注疏劃分為在“無為而治”之外闡釋“無為而治”和在“無為而治”之內闡釋“無為而治”兩類。孔子所說的“無為而治”,隱含著對于政治運轉中自發秩序的某種肯定。“無為而治”中的自發秩序是奠基于人的身體之上的,身體本身已經具備了為無為—政治的自發運轉提供擔保的潛在能力。這種基于身體的自發秩序,似乎構成了孔子眼中政治運轉的深層機制。
一、孔子的“無為而治”是一種治理術嗎?
在孔子明確提出“無為而治”之后,歷代儒家學者等均對此有所闡發1,共同構成和限定了后世理解“無為而治”章的基本路徑,主要分為“選才說”和“德治說”兩類2。錢穆、楊伯峻、毛子水、李澤厚等后世學人的解釋,總體未超出前人的范疇1,都隱含著一種政治的視野。政治一直是孔子的核心關懷,在《論語》中,孔子對“問政”的直接回應就有九處,其中,“無為而治”章因在關涉政治時所觸及的深度、廣度與高度而頗為復雜,且易與老子的“無為”之說相混淆2,因而經常引發今人的爭論。揆諸歷代闡釋,雖然各家之間的觀點不同,但主旨普遍針對何以為“治”的問題3,這與當今流行的治理術范式存在某種交疊,敞開了重新討論該問題的入口。
“治理術”是一個舶來的概念。在福柯的原始語境中,治理術存在廣狹二義:狹義上的治理術,對應于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司法國家向行政國家的轉型,作為權力運行的特殊形式,治理術的“目標是人口,其主要知識形式是政治經濟學,其根本的技術工具是安全配置”4;廣義上的治理術,“不僅僅屬于政治理論”5,但并未特意關注龐大的國家機器及其制度框架,而是廣泛地容納著能夠引導人的行為的策略、技術、程序等種種內容,覆蓋了人與人之間關系中多重層次的引導方式,試圖在生命內部的自然狀態中為這種引導的實現尋找基礎。因此,“治理術”一詞,可以被泛化地理解為不依賴于強制,而是以合乎生命自然的方式去治理人的全部技藝。在關于治理術的寬泛意義上,孔子早在福柯之前就已對類似問題有所意識。盡管孔子曾贊許“三以天下讓”(《論語·泰伯》)這種原始風格的有限精英民主,但孔子關心和討論的主要問題,依然是以權力行使方式為中心的治理問題,而非以權力配置結構為中心的統治問題。同時,孔子的改進策略又始終攜帶著一種關懷人的生命的積極視野,反對將暴力的使用置于權力行使的核心環節。就此而言,后世在對“無為而治”以至于“子曰”的所有內容的理解中,時不時表現出某種與廣義的治理術范式之間的相似,就不必令人驚訝了。現在的問題是,“無為而治”章中,孔子所闡發的真的是一種治理術嗎?
這就需要重回“子曰”之中。乍看起來,“無為而治”章的重心落在“無為”上,“治”的狀態是作為背景而伴隨其中的。如果說在“無為而治”章的前半部分,孔子只是感嘆舜的“無為而治”,重心尚不明確,那么,在后半部分中,孔子就完全轉向了對“夫何為哉”的詳細展開,用“恭己正南面”去充實“無為”的內涵。在文本表達的整個結構中,“治”的狀態被視作已經確立的事實,以某種形式伴隨著舜的“無為”,孔子用一個“而”字描述了這種伴隨狀。但恰恰是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而”,決定了“無為”與“治”在孔子眼中是以何種形式關聯起來的,進而決定了“無為而治”章的整體性質。這個“而”字,構成了一條貫穿于“無為而治”章之中的隱性線索。
這里,“而”作為連詞的詞性是相對清晰的。但在整個《論語》中,孔子對連詞性的“而”的使用,依然是多元化的,“而”通常包含并列、因果、緊接、假設等不同的含義6,對具體的含義,需要回到具體的語境之中得到確定。“無為而治”中的“而”,起碼同時在兩種含義上都是成立的。
一是當“而”作并列解時,“無為”與“治”是以同時出現的時間形式相伴隨的,“無為而治”旨在表達孔子對舜的贊美。此時,“而”的伴隨狀是一種時間性的同時而非邏輯性的因果,“無為而治”即“無為”且“治”,“無為”對于“治”的實現作用是否存在,在這種非邏輯的共時性中尚不清晰。孔子對“其舜也與”的感嘆,只是為了贊美舜的非凡之處,即君主不需辛勞卻能實現理想的“治”。孔子通過對“夫何為哉”的反問和“而已矣”的語氣,又一次強調了作為“恭己正南面”的“無為”,這進一步強化了對舜的贊美,“恭己正南面”是舜的“無為”的具體情狀。這種解釋具有合理的依據,因為舜對于孔子而言似乎極為特殊。孔子曾在與武王時的樂曲《舞》的比較中,用對舜之時的樂曲《韶》的評價,來隱喻舜的“盡美”又“盡善”(《論語·八佾》)。“舜以文德受堯之禪,武王以兵力革商之命,故孔子謂舜樂盡美又盡善。”1在這種闡釋進路中,“無為而治”章的主旨,就是把舜樹立為一個值得仿效的典范,但并不能從“無為”之中推導出何以為“治”的原因,“無為而治”因而并不能直接被視為一種治理術。
二是當“而”作因果解時,“無為而治”直接就是一種孔子所倡導的治理術。“而”對“無為”與“治”的聯結,不只存在于形式層面,更重要的是,在這種聯系之中加入了具有實質意義的因果邏輯。這時,“無為而治”就帶有一種“因為”與“所以”的含義,即舜因為“無為”,所以能實現“治”的狀態。在“夫何為哉”的反問中,“恭己正南面”不僅是對何謂“無為”的解釋,而且給出了何以為“治”的原因。“而已矣”的語氣反襯出“無為而治”之中的因果聯系是不可思議但卻極為真實的。因此,若“而”為因果義,“無為而治”章的主旨就超出了對舜的贊美,包含著一種以“無為”為內容的治理技藝,即一種特殊的治理術。
當前,按照“無為而治”章中既定的內容,不足以讓人確定“而”的具體含義,因而難以完全界定“無為而治”章的表達方向,但不妨結合《論語》之中的“子曰”加以推測。在對“無為而治”的兩類解法中,孔子都表達了對舜的贊美,都把舜視作“無為而治”的典范,這是兩類解法的一處共識。在提及像舜這樣的“圣人”時,孔子的言說中同時涉及兩類視角:一個是孔子面對“圣人”的立場,另一個是孔子面對聽眾的立場。就前者而言,盡管人們能夠在己身上去接近和體認“圣人”,但這極為難得,因而對“圣人”的準確言說就成為一個不易完成的任務。譬如,對于堯的概括,孔子就認為人們能見其“有成功”“有文章”,卻“無能名焉”,不得不依賴于“巍巍乎”“蕩蕩乎”“煥乎”之類比擬堯的外在形象的話語去籠統地言說(《論語·泰伯》),人們幾乎不可能站在“圣人”的立場上去言說“圣人”。就后者而言,孔子強調“言必有中”(《論語·先進》)。孔子去言說舜和舜的“無為而治”,根本上是為了以舜為世人的典范,通過這個典范給人們,尤其是君主帶來有效的啟發,指引人們去克服眼前的困境。在孔子看來,當下最大的困境就是天下無道,孔子曾自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
無論是對舜的贊美,還是倡導治理術,孔子的立場總是帶有一種鼓勵人們追隨作為典范的舜、去仿效舜的“無為而治”的根本目的。因此,后世的學者在對“無為而治”章的理解中,不約而同地轉向廣義的治理術范式,似乎并無不當。但其間存在的區別是,若“而”為并列義,“無為而治”并不能直接給出治理術的內容,需要在“無為而治”之外尋找何以為“治”的答案,“無為”只是檢驗是否實現這種“治”的標準之一;若“而”為因果義,何以為“治”的原因則已經被包含于“無為而治”之內,舜的“恭己正南面”足以促成“治”的實現。這種區分,恰好對應了長久以來闡釋“無為而治”的兩條經典進路。
二、在“無為而治”之外的“無為而治”
在“而”被定義為“且”的情形中,孔子只是通過用“恭己正南面”一語去反復重申舜的“無為”,強化著對舜的贊美,把舜提升到一個被高懸起來的典范地位上。但是,以“恭己正南面”為具體情狀的“無為”,與“治”的實現之間僅僅構成并列的關系而非因果的關系,所以不能為何以為“治”提供一種合理的解釋。這種情形迫使人們不得不走到“無為而治”之外,去尋找問題的答案。按照這條進路闡釋“無為而治”的學者,主要探討了兩類可能被舜所用的治理術。
一是舜因無改于堯之道而能“無為而治”。“舜上受堯禪于己,己又下禪于禹,受授得人,故孔子吁舜無為而能治也。”“既受授善得人,無勞于情慮,故云‘夫何為哉’也。既垂拱而民自治,政所以自恭敬而居天位,正南面而已也。”2盡管就一種不能被推廣的個人際遇而言,“無為而治”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舜擁有上繼于堯、下接于禹的特殊條件,但其中依然存在朝著普適性方向加以解釋的可能性,即把舜的“無為而治”歸因于舜對堯之道的繼承和光大。這里,舜的“無為”與孔子的“不作”意義相近,都有因循和弘揚之義。對此,可以衍生出兩類理解:其一,孔子旨在突出舜的因循和弘揚的精神。對于孔子而言,對于前人的因循和弘揚似乎本身就具有一種特別的價值,這既能見于“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的“孝”上(《論語·學而》),又體現在孔子對“古之道”的別樣關注中(《論語·八佾》)。其二,孔子旨在突出舜的“中庸”或“時中”的精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孔子極為贊許“中庸”之至德,“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孔子把舜視作能夠根據時機的變化,“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的典范(《禮記·中庸》),“無為而治”的實現,或許就在于舜能夠對堯之道“因時而利用之以集其成也”1。
二是舜因善于選賢任能而能“無為而治”。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為政》)孔子一貫重視選賢任能,這同樣成為后人解釋“無為而治”的一個方向,尤見于漢唐儒家的注疏之中,迄今依然為世人所采納和沿用。其實,早在經典時代,子夏就曾用舜來例證孔子的“枉直”之辨:“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大戴禮記》“主言”篇載有:“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在“無為而治”的實現上,舜“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為哉,但恭敬己身,正南面向明而已”2。這種解釋,把“無為而治”的實現置于君無為而臣有為的職責配置之中。因此,“無為”僅僅是獨屬于舜的私人狀態,政治的整體運行依然可能是“有為”的。需要特別區分的是,這種“無為而治”,更類似于對政治錄用保持開放的“賢能政治”,而非架空君權的“虛君政治”,并不涉及對“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這種等級化的權力結構的根本性變革。用選賢任能去解釋“無為而治”,似乎呼應了當時孔子對見用于君的渴望,但是,由此導致的問題是,難以據此彰顯出儒家與諸子之間的實質差別。法家同樣提倡“明君無為于上,群臣竦懼乎下”(《韓非子·主道》)。
必須承認,無論突出舜的因循舊貫,還是贊揚舜的選賢任能,這兩類解法的合理性似乎都能夠經由《論語》之中別處的“子曰”得到某種程度的佐證,因而不能被輕易否定。但是,這兩類解法面臨著兩個相同的問題:一是弱化了“恭己正南面”在“無為而治”章中的存在,甚至造成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之間一定程度的脫節;二是均把“無為”單純視作孔子對舜的一種寫實性的刻畫,突出了舜的優游自逸,卻忽略了孔子在言說“圣人”時所持有的特殊視角及其影響。孔子虛擬了一個旁觀的視角,通過從外部描述舜在“無為而治”中所展現出來的“恭己正南面”的樣子,去充實“無為”的內涵。這種外部化的視角,要求對“無為”做一種特殊的理解。
孔子曾用一個“畏”字,點明了“圣人”如同“天命”一樣的“深遠不可易知測”3。盡管這并不意味著人們不能接近“圣人”,但需要人們通過修身的途徑去感通于“圣人”,在未臻于“圣人”境界之前,人們在把“圣人”付諸言說時,就必須保持克制。孔子或許已經察覺到言說的限度,認識到依靠言說的力量不足以完全揭示出舜的“無為而治”,因此,孔子不得不著眼于可見的部分,將“恭己正南面”用作理解“無為而治”的資具。即便孔子能夠將修身做到極致,能夠克服言說的限度,直抵“無為而治”的全部奧秘,卻尚需顧及聽眾的狀況,“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人皆可見的“恭己正南面”,顯然有利于人們對“無為而治”的理解,易于在聽眾身上激起啟發。既然如此,可見的“恭己正南面”只是通往“無為而治”的入口,能夠連帶著引出“無為而治”中不可見的部分,因而不能僅僅以寫實的方式去解釋“無為”,舜的治理術及其效驗較之于字面上的“恭己正南面”遠為復雜。
那么,與其把“恭己正南面”當作對“無為”的真實寫照,不如將之看成孔子對舜的一種隱喻式的概括,其中涉及一個有待探索的深層區域。這時,作為可見部分的“恭己正南面”并非對“無為”的重申,而是連接著一個不可見的部分,這個不可見部分構成了“無為而治”的底層邏輯。
三、通往自發秩序的“無為而治”
當“而”在“無為”與“治”之間建立因果聯系時,“無為”就成為作為結果的“治”賴以實現的原因,作為“無為”的具體情狀,“恭己正南面”已經能夠給出何謂“無為”以及“無為”何以為“治”的根據,不需人們向“無為而治”之外去求索答案。
這種在“無為而治”之內去揭示“無為而治”的做法,首先經由朱熹的倡導而流行開來:“無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朱熹以為,“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1。朱熹對“無為而治”的解釋,能與多處的“子曰”相呼應。譬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
朱熹的特別之處,在于他把“無為”與“人之所見”聯系起來,因而能夠意識到在可見的“恭己正南面”背后尚且存在一個不可見的部分。這與之前對“無為”的一般看法不同。人們通常直接跨越到舜的立場上去解釋“無為”,以為“無為”是一種極簡主義的治理方式,是舜的真實狀態,卻未曾代入外部的觀察視角,未曾設想過把舜的“無為”與人們所看到的東西相等同的可能性,從而忽視了人們與“圣人”之間所存在的一個需要在修身之中努力克服的距離。但這并沒有暗示一種舜的在可見部分的“無為”和在不可見部分的“有為”的割裂狀態。在朱熹的解法中,舜的“恭己正南面”既是為所有人肉眼可見的,又溝通著“無為而治”中不可見的部分,不可見的部分與可見的部分不可分離地并存著,并沒有背離舜的“恭己正南面”。或可據此進一步推論,孔子是以一種飽含深意的方式,在提到“無為而治”時特別強調“恭己正南面”的:后世依然流傳有“舜勤眾事而野死”(《禮記·祭法》)的說法,即便就舜的對外展現而言,恐怕亦不只“恭己正南面”能被人看到,但在舜的所有行事中,孔子應該以為“恭己正南面”最能切中不可見的部分,能夠引導人們把目光從可見的部分轉移到“無為而治”的深處。這個不可見的部分,關系到“無為”何以為“治”的實現機制。
第一,“正南面”。朱熹對“無為而治”的解釋,側重于“恭己”而非“正南面”,但“正南面”同樣值得認真予以討論。“南面”在《論語》中共出現于兩處,除“無為而治”章外,孔子曾用“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一語評價仲弓。“南面”不僅能指代君主的位置,在朝聘、婚喪、賓客等諸種場合,均有對南面之位的設置,這種設置需要以“禮”為根據來確定。舜的“南面”,則是舜作為君主出現于眾人面前時所當在的位置,是一種合乎“禮”的規范狀態。寬泛地說,“南面”是任何上位者在面對下位者時所當在的位置。同時,“正”在《論語》中具有多重含義,譬如作為動詞的“端正”、作為名詞的“正派”、作為副詞的“恰好”等,當與“南面”連用時,“正”是動詞性的“正對”2,這種用法另見于“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論語·陽貨》)中。就表面的字義而言,“正南面”意為舜在君主的位置上正對著南面。對此可做兩層引申:一是“正南面”是舜作為君主的行事。“正南面”并非端坐于君位而已,似乎可以被擴展為舜作為君主,能夠恰如其分地履行君主的職責3,像“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之屬4,即能夠依禮行事,“‘正南面’者,正君位也”5。二是“正南面”是一種公開的行事。“正南面”撐開了一個容納著舜與諸人的公開場合,舜的行事不僅會作用于他人,而且讓舜在行事之中展現出己身,身處君位的舜,一邊打量著他人,一邊接受他人的注視,舜通過服飾、面容、外表以及一切言行舉止等可見的部分,自上而下地把己身公開出來,無所隱匿。
第二,“恭己”。這里的“恭”是一種使動用法,“恭己”即自覺地“使己恭”。“恭”在《論語》中被用于兩類情形上:一是“巧言令色足恭”(《論語·公冶長》)。這種“恭”僅僅涉及面對他人時的外表恭順,實際上表里不一,是孔子以為恥的虛偽狀態。二是一種內外一致、謙虛謹慎的“德”。“‘恭己’者,修德于己也”1,《論語》的歷代注家常有把“無為而治”與“為政以德”相貫通的取向,“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2。但是,不能僅僅把作為一種“德”的“恭”理解為靜態存在于人身上的特定屬性,而是必須見諸身體的行事之中。孔子就曾從行事的維度,以“其行己也恭”(《論語·公冶長》)一語來褒揚子產。因此,不妨將“恭”看作一種人在行事之中的身體姿態,這種身體姿態是對貫穿于人的全部行事之中的穩定結構的一種概括,既能夠表現為在可見的外在行事上的“恭”,又向內呼應著不可見的、作為心理活動的內在行事上的“恭”,最終構成一種包含整個身體、兼容內外行事的“恭”的整體狀態。在舜的“恭己正南面”中,“恭己”是為“正南面”奠基的前提條件,如果說“正南面”意味著舜作為君主的行事,那么,他就是以“恭己”的方式去行君主之事的,是以厚植己身之“德”的修身為前提,去自覺進行合乎“禮”的行事的。這不免令人想起與此相近的“富而好禮”(《論語·學而》),舜的尊貴地位與舜的謙虛姿態之間的對比,反而愈益顯示出“恭己”的真誠,顯示出舜對“恭己”的自覺。
在得到初步澄清之后,“恭己正南面”的效力便能夠穿透可見的部分,把“無為而治”背后的不可見部分,即把“無為而治”中的自發秩序連帶出來。
首先,“無為”不是“不為”。“圣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3。在肉眼可見的層面,舜作為“正南面”的君主,需要去履行的職責內容極為廣泛,甚至不能從中排除舜對“政”與“刑”的運用,“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4。“恭己正南面”是以概括的而非寫實的方式歸納了舜作為君主的所有行事,將可見的全部行事統攝于以“恭己”為奠基性前提的“正南面”之內。這種由“恭己正南面”來概括、以“德”貫穿于其中的行事模式,被孔子歸入“無為”的范疇。那么,本來令人專注于己身的“恭己”,如何在“正南面”的行事之中影響他人,從而達成“治”的狀態,就成為一個需要被解釋的問題。
其次,“無為”之所以能“治”,依賴于一種以不可見的方式維持運轉卻真實起效的自發秩序。在“恭己正南面”中,存在著一種雙向的交互:人們朝向舜的觀看,產生了可見的維度,孔子把人們從這種觀看中能看到的東西概括為“恭己正南面”,若僅僅停留于此,“無為”只適合被解釋為人們看不到舜的多余行事;但與此同時,舜在朝向人們的行事之中對于人們所產生的作用,則涉及到一個未必肉眼可見但能有所感受的不可見維度,“君主的‘無為’即在于只是通過其個人的修養與民眾產生相互的影響,而不需要以專制的方法統轄其臣民”5。舜的行事未曾對人們造成強行的壓抑,或者更為一般地說,人們并未從舜的行事中感到一種施加于己身的異己力量,“無為”因而有不會令人在己身之中產生被排斥感的含義,人們只是如同順應于己身一樣,以一種本來如此的狀態去自發服從于舜。因此,舜的“恭己”能夠通過“正南面”的行事,連接起己身與民眾,將之一并置于彼此交互的自發秩序之內。這是一種“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的自發秩序,“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6。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孔子對“正身”與“正人”的關系辨析,暗示著這種自發秩序的實現機制和擴展模式。通過這種自發秩序的運轉去實現“無為而治”的政治,就可被視為孔子Bnnnbf1keA9TKdaRildGzcEOMhm2E3lkh4VeX4KSIkM=風格的無為—政治。
四、在建構與演進之外:基于身體的自發秩序
其實,對自發秩序的肯定和追求,不能被看作是某一學者或某一學派的專利。自經典時代以迄高度復雜的現代社會,自發性幾乎一直是人類所能想象到的完美秩序的極限。在現代知識譜系中,不論由政治經濟學發現的“市場之手”,還是哈耶克所闡發的文明演化的“自發秩序”,抑或方興未艾的對人工智能技術與國家治理轉型的討論,當前理論成就的根底處總是滲透著人類對自發性的想象。然而,即便在現代科學語境中前所未有地融入了人們對秩序運轉的事實狀態的規律性把握,對自發性的想象卻依然難以擺脫一直以來的信念底色,任何有關自發性的論斷,或多或少反映了人們對秩序運轉的終極狀態的一種信念。這種信念如同自我實現的預言,引導人們按照其所提示的內容去理解和調適現實秩序。因此,在對“無為而治”的分析中,重要的不是去詳細論證何種自發性是正確的,或者說,并非在于去尋找一個真正的完美秩序,而是嘗試解開彼時如何建構人與自發性之間的關系,即厘清孔子以為的自發性的實現機理。在不同的語境中,對自發性的實現機理的理解,存在頗為懸殊的差異。
不過,當前任何對于自發秩序的討論,恐怕都不能繞過哈耶克,哈耶克在現代政治學的視野之內重新激活了人們對自發秩序的關注,將自發秩序置于政治運行的核心地帶,盡管政治學視野在哈耶克的整體研究中并未構成一個主要方向。哈耶克根據秩序產生的方式,劃分出基于理性建構的建構秩序和基于漸進演化的自發秩序兩種具有原型性質的秩序類型,建構秩序的典型形式是以統一的指令強制推行對社會秩序的政治工程學改造,將秩序的形成完全置于理性的籌劃之中;自發秩序則是一種內置自然選擇機制、多元互動機制、經驗積累機制等難以窮盡的多種非人格化機制的秩序運轉模式,是一種“經由自生自發且不可抗拒的發展而形成的結果”1,“產生于諸多并未明確意識到其所做所為會有如此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2。
哈耶克的二元秩序劃分,不僅出于針對現實狀態的實證主義立場,而且帶有規范性意蘊,哈耶克對建構秩序的反對和對自發秩序的捍衛,是為了“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通過維系這個“理性據以發展和據以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3,確保人對理性的正確運用。哈耶克所謂的自發秩序,是在微觀和宏觀兩類視野之內得到辯護的:對于個人而言,知識被個人分散掌握,個人能夠理性地運用知識于“置身于其間的情勢”之中4,沒有人可以掌握全部的知識,因而理性的使用存在一個不能超出的限度;對于社會而言,秩序的運轉根本上有賴于自由、競爭和有助于個人自由競爭的形式性規則5,是一種基于人之行動而非人之設計的非意圖性結果,社會秩序能夠隨著個人之間的競爭、合作、模仿等開放的互動過程而得到擴展。顯然,哈耶克對建構秩序和自發秩序的劃分,并不能被等同于古希臘式的“自然的”和“人為的”之別6,并未在秩序的運轉中排除人的參與,哈耶克只是把秩序生成的自發性放在人為控制之外的漸進演化的基礎上,這種自發秩序存在于一個不能被理性穿透卻能被人利用的無知之域中。
盡管與哈耶克式的自發秩序不同,但秩序生成的自發性同樣限制著中國經典時代先哲們的秩序想象。譬如,法家利用人對賞罰刺激的本能反應,致力于實現一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的自發秩序(《韓非子·揚權》),這是一種基于人的生物本能的自發性;道家則提倡一種“處無為之事”和“行不言之教”的自發秩序(《老子·二章》),其中的自發性隱含著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消極態度。孔子對自發秩序的看法最為生動地反映在孔子對“草上之風”的比喻中:“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于上也。”1對“草上之風”的譬喻,不能做一種物理學式的理解,不能從“力”的作用的角度去加以把握,“草上之風”應被放入如“四時行”和“百物生”一樣的自然情狀中去予以解釋(《論語·陽貨》),孔子為之設譬的是一種自發秩序的運轉:“君子之德”的外向顯現,自然會感化人們,引起人們自發的響應、順從和跟隨,達成一種“近者說”和“遠者來”的客觀效果(《論語·子路》),一切就像風吹草低一般自然而然地發生,并不是借助于強制的力量。孔子的教化機制就奠定于這種自發秩序的運轉之上,教化的實現以自發秩序的運轉為核心機制,舜的“無為而治”與舜的教化根本上是同一件事。
那么,這種自發秩序在何種層次上達成了這種自發性?或者說,自發性賴以實現的根據為何?事實上,對自發秩序的證明,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這種自發秩序是哈耶克式的還是孔子式的。因為任何把理性的論證加之于自發秩序之上的努力,似乎都暗示著自發秩序是能夠從外部被透視的,但自發秩序之所以對人表現出自發性,恰恰在于自發秩序是不透明的,不能讓人當作透明的東西去把握。自發性的證明近乎陷入了一種矛盾的狀況:當置身其中時,人與自發秩序之間并無扦格,自發秩序的效力沒有超出人的己身的限度因而難以找到一個在自發秩序之外令自發秩序生效的根據;假如能夠置身其外,人卻又不能確定自發秩序的存在與否,自發秩序因而是不可知的。這種不易克服的矛盾,曾是哈耶克的自發秩序論證中經常為人詬病的地方,哈耶克不得不強調他“只是表明理性并非萬能”2,而非旨在完成對自發秩序的完全證明。在經典時代,包括孔子在內的先秦諸子,則不約而同地把自發秩序的根據交給了形而上的“天”。孔子曾感嘆:“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3“天”的存在為自發秩序的運轉提供了最終的擔保,能夠“則天”的則是“圣人”,“古圣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而行之”4。這種以“天”為最高主宰的“天意政治”或“天治主義”5,將自發秩序置于一個不能亦不必論證,只需人們無條件遵循的范疇。
固然,孔子從未將自發秩序付諸理性的論證,但同樣沒有利用“天”來對自發秩序做一種決定論或宿命論式的簡單解讀,他把人的身體放在較之于“天”而更為接近人的位置,人能夠在己身上去體認“無為而治”中的自發秩序,能夠以“知天命”的形式在己身上去把握自發秩序背后的形而上根據。孔子用人的身體而非理性,去體驗性地而非知識論地認識自發秩序:自發秩序對于理性的“觀看”而言是不透明的,但卻能被人的身體所“感到”,作為未曾超出身體本身的東西而在身體層面被接受下來。這個身體不是靈肉二分法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儒家理解的身體主體只要一展現,它即含有意識的、形氣的、自然的與文化的向度。這四體互攝互入,形成一有機的共同體”6。當把這種身體從生理性的肉體或理性化的意識的遮蔽中重新喚回之后,便能打開一個新的對“子曰”的闡釋視界。人的身體能做的遠多于“視聽言動”。譬如,在《論語》之中,孔子所說的人皆有之的“仁”與“德”在人身上所存在的區域,就可被視為人的身體,而不必冒著僭越和分裂的風險非得將之劃入意識的范疇不可。身體的“有”的方式,不是以實體的方式去擁有特定的屬性,而是表現為一種身體之“能”,“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這種“能”是人本身先天固有的如同“視聽言動”一樣的身體能力,需要見諸身體的行事之中,而非停留于意識的活動之內。似可用“感通”來概括這種身體能力。
就此而言,自發秩序的作用層次直抵人的身體,“無為而治”在身體的層面實現了秩序運轉的自發性。“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1盡管“感”與“通”的朝向不同,但都統一于人身之中,都同時牽連著人己,人與己都同時出現于己身的感通之中,這就暗通于孔子對“仁”與“德”的討論。身體的感通能力,將人先天嵌入于“感”與“應”的生活世界之內。“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于感而言,則感又兼應意。”2感通與感應并無根本區分,若將感通視作歸屬于任一人的身體能力,感應則側重于突出身體之間在相互感通中的交互作用。從“人”之一側看,“感”與“應”是人作為身體性存在的生存模式;從“天”之一側看,“感”與“應”是連帶人在內的整個世界的運作模式。因此,只要人以身體的方式在世存在,就必然保持著開放的狀態,就不可避免地置身于人己之間的身體性關聯中,即孔子所謂的作為“仁”的“己欲立而立人”的關聯性之中。這種基于身體感通的“感”與“應”,澄清了“無為而治”何以實現如“草上之風”一般的自發秩序:舜以彰顯己身之“德”的“恭己”為依賴進行“正南面”的行事,人則被其所“感”而去“應”舜,這種“應”是直接出于身體層面而非意識層面的,是一種身體的選擇而非意識的反思,因而自發秩序的運轉不取決于人的自覺與否。是故孔子對季康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這同時解釋了儒家歷來強調的教化機制的運行方式。
當自發秩序落定于人的身體時,“無為而治”的自發性就完全不同于當前流行的哈耶克式自發秩序中的自發性。哈耶克對自發性的理解,側重于強調人對社會秩序的不可預料、不可設計且無法抗拒3,或者說,以消極的方式對待人的意識與秩序之間的關系。相較而言,孔子以更為積極的視角看待人的身體與秩序之間的關系:一是“無為而治”的自發性由身體予以確認。盡管同樣不依賴于對自發秩序的理性論證或意識明察,但人并非對“無為而治”的自發性無所作為,人能夠通過直接作用于身體本身的體驗,去確認這種自發性的真實有效,身體的確認較之于意識的推導更為徹底,更為貼近于人。二是“無為而治”的自發性由身體予以實現。對于舜的“恭己正南面”的自發性回應,是由人的身體直接做出的,身體以合乎其之所能的本己方式而非服從于外在力量的異己方式,產生這種并不以內在意識為先、人的意識反而寓于其中的身體反應,不過,身體本身經常會被遮蔽,每個人通過身體的感通,進而實現“仁”或“德”的能力存在程度和層級的不同,能否自覺把意識的目光返回來投向自己的身體,對于每個人而言是不同的。三是“無為而治”的自發性由身體予以擴展。可擴展性似乎是自發秩序中的一個普遍特性,與哈耶克把秩序的自發擴展歸入歷史的演化不同,“無為而治”中“治”的擴展依賴于人與人之間的身體性關聯,這種自發擴展同樣需要“世而后仁”的時間準備(《論語·子路》),但根本上起作用的是人的身體。
總體而言,“無為而治”中的自發秩序可被概括為一種基于身體的自發秩序,無為—政治的自發運轉同樣需要回歸到身體的層面。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不令而行”與“雖令不從”從正反兩個方面反映了孔子對于無為—政治的看法及其背后的權力觀念。
五、“不令而行”:無為—政治的自發運轉
孔子的“不令而行”一語已將“無為而治”中自發秩序的運轉推至極致。君主發布命令本是一項基本的政治活動,但“不令”否定了作為言說的“令”在無為—政治中的存在,甚至可被視作孔子排除了言說本身對于“無為而治”的必要性,無論言說的形式是宣之于口的還是布之方策的,無論言說的內容是政令還是教令。“先王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已形于外。”1當自發性的效力被發揮到極限時,君主不需專門付諸言說以說服、勸誡、恐嚇或蒙騙大眾,刻意的言說反而會損害自發秩序的自發性,只能顯示出這種自發性的實現尚不夠充分,顯示出君主的己身之“德”尚不完備。或許,孔子眼中的堯之“則天”,就有暗示堯因“德”的圓滿,故而能如“不言之天”一樣“不令而行”的意思。
若無為—政治的自發運轉并不借助于言說的力量,那么,“不令而行”何以實現秩序的自發擴展?孔子用令民眾“有恥且格”的“道之以德”和“齊之以禮”答之(《論語·子路》)。“道之”和“齊之”的對象是民眾,作為上位者的君主則是“去道”和“去齊”的人,君主“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2。“道”或“齊”的方式不是用“德”和“禮”去為政,更不是把“德”和“禮”轉化為強制性的規則。君主通過率先垂范,即讓對民眾生效的“德”與“禮”先在己身上生效,先使自己能“恭己”地“正南面”,引導民眾去自發響應君主。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孔子以為,作為“政”的政治與作為“正”的教化之間是互詮的,君主“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紐也。使天子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禮,以親親、尊尊、賢賢明男女之別于上,而民風化于下,此之謂治,反是謂之亂”3。不管政治,還是教化,君主都是自發秩序向外擴展的中心,隨著君主在從“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百姓”的修身進路中不斷取得進步(《論語·憲問》),君主的教化的影響逐漸擴展出去,“近悅遠來”的民眾逐漸增加。因此,君主為政的首要之義,就在于朝向己身的修身。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從“成人”的角度而言,修身是人人本應都去做的事情,是把孔子所注重的“仁”在身體上開顯出來的關鍵,這種“仁”不是“一個從外面得到的品質”4,而是身體本身先天就已具有的能力,規定著人之為人的本質,不過暫時被遮蔽起來,未能得到發揮而已;從“正人”的角度而言,孔子尤為強調修身對于君主的價值,強調君主的修身對于教化的價值。這里暗含著的一個問題是,純以修身論,除了“生而知之”這種特殊情形,人與人之間并無實質差別,與是否是君主無關,但緣何孔子特別看重君主的修身?若這是因為君主的有位,就相當于承認“位”優先于“德”;但若取消君主之于教化的特殊作用,那“子帥以正”與“孰敢不正”之間的關系就解釋不通。更進一步說,在無為—政治中,自發性的實現本應依賴于身體的作用而非權力的作用,突出君主是否表明孔子又暗中承認了權力的因素對“無為而治”及其自發秩序的強勢影響?其實不然。孔子在強調君主的修身能夠取得“子欲善而民善矣”之效的同時,堅持普通人的“克己復禮”,也能夠引起“天下歸仁”(《論語·顏淵》)的效果,“歸,猶與也”5,有贊許和傾慕之義。更有甚者,孔子直接把無位卻能推行教化的人,同樣看作“是亦為政”(《論語·為政》)。顯然,通過身體之間的相互感通這種身體性關聯,用己身之“德”喚醒他人之“德”的做法,始終是孔子眼中自發秩序賴以實現的根本機制。對于君主的特殊性的理解,需要回到修身的內部中去。
就一般的理解而言,修身當然包括一種“思”的維度,孔子有“學而不思則罔”(《論語·為政》)一語,孟子同樣告訴人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孟子·告子上》)。但是,這種自覺的反思不能被徑直等同于笛卡爾式的“我思”,更沒有使修身止步于以“自我”為主體展開的意識領域之內。修身之中的“思”,所針對的是身體的行事,而非對象化的肉體:“自我”不能讓人從自己的身體上抽離出來,站在身體之外去把這個身體作為孤立的實體放在“自我”的面前,使“自我”在反思之中以對象化的方式去透視身體本身,這里被反思的實則是人的肉體而非身體,這種反思實則是“自我”對身體的異化、吸納和僭越;身體只能在行事之中為人所完整體驗,作為能力的集合,身體的感通使人一經現世,就已置身于生活世界之內的相互交往之中,人們是在身體的行事之中去“仁”、去“德”、去“感應”1,即去實現感通的能力的,意識性的“自我”不僅不能脫離人的身體,而且是隨著身體的行事而一并構成的。但是,這個身體是能夠被遮蔽的,身體的感通能力經常被“意必固我”所阻塞,孔子曾用人們對“如之何、如之何”的感嘆來形容身體被遮蔽的不安狀態(《論語·衛靈公》),“如之何、如之何”的發出不是了解問題之后去求得辦法的追問,而是連問題所在都不清楚的抒發,是一個“含蓄的告誡”:“我們身上有什么東西出了問題”“它要求我們徹底檢視我們自己”2。修身就是去檢視身體的行事,無論內在的心理范疇還是外在的肢體范疇,只要牽涉到身體的行事,都需要得到檢視。
因此,修身不是離開生活的苦行,不是亦不能把人的身體從行事的情境中單獨剝離出來,而是讓人以合乎“禮”的恰當方式整體投身于具體的行事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禮記·中庸》)。在不同的情境中,每個人的位置不同,其所對應的行事方式不同。普遍地說,每個人都能夠隨著修身的深入,感受到人己之間的積極關聯以及自己對他人所承擔的某種責任,但對于君主而言,這種責任不僅是作為“成人”的方式,在修身之中逐漸被感到的,而且是直接被“位”所要求的,是一旦成為君主就必須立即承擔的:君主在代表“天”進行統治的同時,是面對“天”,在最為廣闊的范圍之內為民眾的所有不幸、錯誤或不完善承擔責任和付出代價的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論語·堯曰》)。因此,君主修身的特殊性,首先不是因為君主的權力,而是因為君主的責任,是因為君主必須在君主的位置中表現出對應的行事,以此承擔“正人”的責任;其次,君主修身的特殊性與孔子對“孰敢不正”中“不敢”的洞察有關,君主與民眾之間的地位落差,使君主的“正身”更易于引起民眾的響應,但這依然未曾超出基于身體的自發秩序的運轉,并沒有付諸或威脅付諸暴力,更接近于強大的感召。在無為—政治的自發運轉中,“恭己正南面”從不是讓君主把自己像雕塑一樣擺在那里,讓臣民去觀看一個所謂的“德”,而是需要君主自覺見諸行事之中,依賴生動的行事而公開展現出己身之“德”。這種展現是一種全方位的公開,并不局限于單一的某一方面。
其一,君主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在孔子看來,任何人的修身,都“始于在家之孝悌,終于博施濟眾,天下歸仁”3,這既非個人主義又非集體主義,其中的各個環節是由人的身體予以貫通和統一的,每個環節之間不可分割、連為一體。君主對此亦概莫能外。君主在所有的行事中都是同一個身體,不能在這個身體上劃分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兩個部分,即便君主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同樣具有教化的效用,同樣會引起民眾的自發仿效,并不是現代意義上被法律保護的隱私領域。“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4子曰:“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論語·泰伯》)“人君若自于親屬篤厚,則民下化之,皆競興起仁恩也。”5在日常生活中,君主以孝悌的方式行事對于教化的推行尤為重要,素來為孔子以及儒門學者所推崇。不過,日常生活的開放,不僅對于君主而言是如此的,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對于君主來說同樣是開放的。
其二,君主在禮儀場合中的行事。在日常生活與政治統治之間,君主的行事同時包含著諸種以“禮”為中心的儀式性內容。廣義而言,“禮”作為一種規范,幾乎囊括了人在一切場合中的一切行事,甚至規定著人在具體的行事之中的心理狀態;狹義而言,對“禮”的探討,可以聚焦于冠、婚、喪、祭等特定的儀式上,各類儀式因具有教化的作用而被納入政治的范疇之中。雖然既不涉及常規的治理活動,又不是維持日常生活的必要組成,但這種儀式性內容在君主的行事中占有相當比重,譬如,“每一個新受命的皇帝即位,其立政建制,莫先于改正朔,易服色”①。《論語》“八侑”篇載有孔子與人的問答:“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禘,王者之大祭也。”②“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禮記·祭義》)就君主的祭祀而言,無論被祭祀的是鬼神、祖先還是先王,“‘報’的觀念便貫徹了祭的全部分”③,君主在祭祀場合中合乎“禮”的行事,能夠向民眾傳遞“報本反始”的意義,引導民眾“興于仁”。
其三,君主在政治統治中的行事。孔子從來都不是道德空想主義者。對于政治統治,孔子既還有“足兵足食民信之矣”這種正面的建議(《論語·顏淵》),又有“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和“出納之吝”這種反面的訓誡(《論語·堯曰》),同時還有“先有司”“赦小過”和“舉賢才”這種簡拔賢能的提示(《論語·子路》)。表面上,孔子的主張看起來并無特別奇異之處,其中最為顯眼的地方莫過于反對君主的殘暴,支持統治的寬仁,主張與“庶矣”和“富之”相配合地推行禮樂之教(《論語·子路》);真正讓孔子的主張變得不同尋常的,可被概括為“絜矩之道”,即“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禮記·大學》)。“治國治要盡于此”“取于己而已”④。君主在政治統治中的行事,并不是以“德”用權,并非把權力的行使寄托給一個抽象的“德”,而是以“身”用權,把己身確立為權力行使中的尺度,這個己身絕不是作為一己之私的身體,而是時刻能夠感通于他人的身體,是能夠把“立己”與“立人”統一起來的身體。
六、結語
“無為而治”是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政治理念。“無為而治”對自發秩序的推崇,打開了一個溝通和比較中國政治與世界政治的切入口,迄今依然能從當代中國國家治理中窺見其痕跡和影響。當下,對“無為而治”的關注和激活,能夠在強行政與強自治之外,給出一種促進國家治理高質量發展的全新可能性,即一種基于自發秩序的低治理成本、高治理效益、上下一體貫通的治理模式。往更深處說,由“無為而治”筑造的政治秩序,已經超出了通常治理術的作用限度,包含著中華文明視野之內對于人本身的界定方式,人本身作為身體性的而非意識性的、關聯式的而非個體式的存在,是政治得以被奠基和完善的根源。
責任編輯 申 華
技術編輯 王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