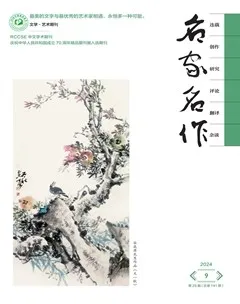辜鴻銘的中西文化比較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摘 要] 辜鴻銘作為學貫中西的思想家,以精神的器具為標準,結合自己的真實體驗和深入思考,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他認為這兩種文化都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雖然在具體層面存在差異,但最終還是會走向融合。而在辜鴻銘對中西文化的比較論述中體現出的文化自信、平等的文化交流心態以及對現代化進程的反思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思想精華。
[關 鍵 詞] 辜鴻銘;中西文化;文化自信
清末民初,有這樣一位思想家、哲學家可謂是矛盾的集合體:他自幼在西方長大卻留長辮、穿長袍;深諳西方物質文明卻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鐘;在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下,逆潮流行之,把以儒家文明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西方視為己任,并身體力行,力圖打破當時外國人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偏見。他就是有著“清末怪杰”之稱的辜鴻銘。時人嘲笑他的保守思想和怪誕行為,后人沉醉于研究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和在翻譯領域所做的貢獻,但關于其中西文化思想溝通者的形象以及與此相關的思想卻少有涉及。因此,本文立足于辜鴻銘學貫中西的文化溝通者的形象,從判斷標準、具體內容、歷史定位以及當代價值四個方面探究辜鴻銘的中西文化比較思想,對其進行梳理和闡述,并從中吸取適合時代發展的思想精華。
一、辜鴻銘中西文化比較的判斷標準:精神的器具
辜鴻銘學貫中西,對中西文化都有切實的學習與體驗。在此基礎上,辜鴻銘結合自己的思考,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而比較是基于一定標準的,辜鴻銘判斷中西文化的標準就是精神的器具。他指出:“文明的真正含義,也就是文明的基礎是一種精神的圣典。”[1]他反對以物質生活為標準判斷一種文化的優劣,認為物質生活的繁榮與否并不代表文化本身的高低,只有精神上的富足才能彰顯一種文化的真正價值。而在《中國人的精神》的序言中,辜鴻銘進一步明確了自己判斷中西文化的標準,即提出:“要估價一個文明,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它能產生什么樣子的人,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一種文明所產生的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正好顯示出該文明的本質和個性,也即顯示出該文明的靈魂。”[1]在此基礎上,辜鴻銘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
二、辜鴻銘中西文化比較的具體內容:大同小異
辜鴻銘對中西文化的異同比較既涉及宏觀層面,從文化的起源到最終走向,也涉及較為具體的層面,例如他在《東西文明異同論》中提到的東西方的五個差異。辜鴻銘通過比較中西文化得出的結論大致可以用“大同小異”四個字概括,即宏觀層面有共同之處,具體層面又各有不同。
(一)大同:從文化起源與文化發展走向來看
辜鴻銘因其獨特的人生經歷,有“東西南北人”之稱。他自幼接受的是西式教育,精通西學西政;年近三十歸國,進入張之洞幕府工作,受到張之洞及幕府一批儒者的影響,加上自己努力學習中國文化,歷時二十余年終成與泰戈爾齊名的東方文化的代表。因此相較于僅接受過單方面文化教育和熏陶的思想家,辜鴻銘對中西文化的比較更具有說服力,其中包含著他對中西方文化的獨到洞察與真實體會。
從宏觀層面,辜鴻銘指出中西文化在發展形式上是一樣的,都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辜鴻銘對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進行了梳理,并與西方文化相對照,更為清晰地展現了兩種文化的共通之處。在辜鴻銘看來,中國文化的真正起點是在夏代,隨后發展于商代,并在周代走向了第一階段的成熟。而與中國夏代文明對應的是古埃及文明,二者都是物質文明發展時期,夏代在水利上取得的成功以及埃及的金字塔和運河都是很好的證明。與商朝文明對應的是猶太文明,兩種文明都對道德以及心兩個方面尤為重視,在形而上學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發展。而與周代文明對應的是古希臘文明,二者重視智的發展。正是由于周代重視智而忽略了心,所以導致此時的中國文化逐漸走向凋落,出現了很多“亂道之儒”。秦始皇認識到這一危害,采取“焚書坑儒”的手段,并推崇法家,但歷史證明這種方法并不可取,所以秦朝僅僅過了兩世就覆滅了。而此時西方的馬其頓帝國與秦朝一樣先是將分裂的國家統一起來,但也只經歷了兩代人就滅亡了。
秦朝過后是漢朝,辜鴻銘認為漢代的中國相當于歐洲的羅馬帝國,二者都一分為二,羅馬帝國分為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漢朝分為西漢與東漢。中國文化在東漢又得以復興,但存在只注重心的弊端,好在有佛教傳入彌補了知的層面,但同樣也招來了混亂,產生了“五胡亂華”,與此同時,歐洲的古羅馬也經歷著被五個蠻族集團欺凌。接下來中國文化的發展來到了唐朝,辜鴻銘將其類比為西方的文藝復興時代,中國文化呈現繁榮態勢,但這種繁榮是脆弱的。為了挽留這種脆弱,中國文化迎來了新的形態,即宋代儒學,辜鴻銘將其類比為歐洲的新教派。由此可見,辜鴻銘認為中西文化的起源大致時間相同,并都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
除此之外,辜鴻銘指出中西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也是要走向融合的。他認為中西文化雖然存在很多明顯的差異,但未來這種差別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標上是會走向融合的。辜鴻銘認為,一方面,中國文化可以通過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來尋求走出儒學發展困境的方法;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可以從中國文化中尋找醫治物質功利主義的良方。所以,他曾為自己正名道:“其實,我既不是攘夷論者,也不是那種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東西方的長處結合在一起,從而消除東西界限,并以此作為今后最大的奮斗目標的人。”[1]
(二)小異:從中西文化的具體細節來看
雖然中西文化在宏觀層面具有相似性,但落實到具體層面上,還是會有所不同。辜鴻銘在《東西文明異同論》中主要從個人生活、教育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以及文明五個方面對中西文化的差異進行了論述。在辜鴻銘看來,能夠產生一個什么樣的人是評估一種文化的標準,因此作為文化的載體,辜鴻銘通過比較兩種文化下的人的不同從而折射出兩種文化的不同。
在個人生活方面,辜鴻銘認為西洋人沒有正當的人生目標,沒有思考過人是什么,而中國人對此早已全然領會,那就是孔子教導我們的,在家做孝子,在國為良民。西洋人是為賺錢而活著,中國人為享受人生,為幸福本身而活著;西洋人貪得無厭,中國人知足常樂。
在教育方面,辜鴻銘認為西洋人的教育在于教導人們怎樣做一個成功的人和適應社會的人,中國人的教育在于教導人們怎樣成為一個聰慧的人和為創造更好的社會做貢獻的人;西洋人的教育方法是不合理的,從孩提時期開始就給學生灌輸深奧的哲學知識,中國人的教育方法是循序漸進的,先鍛煉學生的記憶力,讓他們了解背誦祖先流傳下來的知識,然后再逐步增加難度;并且中國人記憶的方式與西方不同,西方用腦記憶,中國用心記憶。
在社會問題方面,辜鴻銘認為西洋的社會是建筑在金錢基礎上的利害關系,中國的社會是建筑在名分基礎上的道德關系。中國人先義后利,西方人先利后義,而這是中西文化的主要區別。
在政治問題方面,辜鴻銘指出西洋人因為畏懼強權而遵守秩序,中國人因為遵從綱常倫理而保持秩序。這一點在一戰后西方國家人們普遍陷入恐慌、混亂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辜鴻銘指出歐洲的社會結構建立在強權之上,維持秩序的工具是宗教和法律,人們因為害怕上帝和敬畏法律而保持秩序。但一戰過后,這兩種自然力量已經失去效果,擺在西方面前的出路是向中國文明學習,依靠正義與禮法的道德力量,這種力量使得人口眾多的中國保持著和平與秩序。
在文明這一問題上,辜鴻銘先給出了關于文明的定義,即美與聰慧。在這個定義之上,辜鴻銘認為由于西洋以制作出更好的機器作為自己的目的,是機械文明;中國以教育出更好的人作為自己的目的,是精神文明。辜鴻銘并不反對西洋注重物質的生產,但認為要用優秀的精神文明來制約物質文明,使其能夠按照造福人類的方向發展,否則就不能成為真正的文明,而西方正好違背了這個原則,所以辜鴻銘對西方文化持有批判態度。
三、辜鴻銘中西文化比較思想的歷史定位:撻西揚中與中西文化融合
關于辜鴻銘對中西文化比較思想的歷史定位,目前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辜鴻銘強烈批判西方文化,并主張用中國文化來醫治西方文化中存在的弊端,用中國文化彌補西方文化的空白;而面對中國文化本身,辜鴻銘主張尊孔復古,認為中國文化只需保持自身特色,無需向西方文化學習,因此認為辜鴻銘持有一種“撻西揚中”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二是認為辜鴻銘持有的是中西文化融合論的觀點:正如上文中辜鴻銘為自己正名時說的那樣,他是想把東西方的長處結合在一起,并以此為自己行動目標的人。辜鴻銘指出,西方在物質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超過中國的,并強調凡是西方文化中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中國也可以模仿。由此可見,辜鴻銘所批判的并不是西方文化本身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物質,而是這種文化被濫用了,他認為如果物質文明沒有得到精神文化的正確引導,就會有很大的隱患,即便它的外表再華麗,如果地基不牢固也隨時有坍塌的危險。而為了防止或彌補這種危險,西方或許可以借鑒中國文化中的“良民宗教”,這是辜鴻銘為西方文化開出的“藥方”。而對于中國文化中的不足,辜鴻銘認為自宋朝以來,由于佛教勢力的擴張,中國文化開始變得狹窄起來,而這一問題一直延續并未得到解決。所以為了擺脫中國文化所面臨的困境,可以借助與西方文化的交流這一方法。辜鴻銘認為自己并非時人所認為的保守主義者,而是將自己歸類為以張之洞為開山祖的“真中國黨”,而他對中西文化的比較也不是一邊倒偏向中國文化,而是主張中西文化之間相互借鑒。
四、辜鴻銘中西文化比較思想的當代價值:文化自信與對現代化的反思
現如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不斷加快,對外交流日益擴大和深入,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如何化解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變遷的過程中所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如何以平等的方式進行平等的對話,如何堅守并提升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或許辜鴻銘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那就是在堅守文化自信的基礎上進行文化的平等交流,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辜鴻銘厭惡那些秉持著“黃禍論”思想的西洋人,認為他們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國與中國人;同時他也厭惡崇洋媚外的人,曾在電車上痛罵用洋文戲耍他的青年,認為他們是用望遠鏡來看待中西文化的,即放大了西方文化,縮小了中國文化。面對種種現狀,辜鴻銘用自己的方式試圖改變,即向西方輸出真正的中國文化,改變外國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他將蘊含中國文化精髓的書籍,諸如《論語》《中庸》等書籍翻譯成英文,讓外國人能夠借此了解到真正的中國文化。與此同時,辜鴻銘的大多數著作是以外文撰寫的,尤以英文居多,可見他的思想的受眾群體是外國人而非中國人,他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傳播中國的思想,改變外國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正如辜鴻銘曾在講課的時候告誡學生說之所以要學英文詩,是因為要學生學好英文后,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及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可見辜鴻銘內心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但這種文化自信并沒有讓辜鴻銘故步自封,一味排斥文化交流。正如上文所說,辜鴻銘不但承認西方物質文明的繁榮,同時也鼓勵學習西方的長處,只是這種文化間的交流與學習是建立在雙方文化平等的基礎上的,而非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蔑視之上。
與此同時,辜鴻銘被譽為“率先認識到儒家文明的世界意義、認識到儒家文明對于現代化進程的意義的思想先驅,同時也是率先向西方讀者闡釋儒家文明之優越性的思想先驅”[3]。辜鴻銘之所以在轉型時期推崇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有出于維護傳統中國文化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對現代化的反思。辜鴻銘自幼生活在西方,看到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弊端與失序,諸如物質功利主義、技術理性的膨脹等,所以辜鴻銘認為如果先進的物質條件沒有正確的精神文化加以引導,就會造成混亂,這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得到了印證。為了不重蹈西方的覆轍,辜鴻銘指出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要發揚儒家對道德力的重視,以此作為一種約束力量來規范物質的發展,不至于陷入西方現代化所處的困境。
五、結束語
辜鴻銘本人是雙重文化的經歷者和學習者,他結合自己的所見所學、所思所想,以“精神的器具”為判斷標準對中西文化進行了比較研究。總結來說,辜鴻銘認為雖然中西文化都經歷漫長的發展過程,最終也會走向互相借鑒的融合狀態,但中國文化是一直綿延不絕,沒有中斷的;西方文化則因為種種原因出現了斷層。結合兩種文化在具體層面的差異,辜鴻銘認為中國文化是精神文化,像已經建筑好的屋子一樣,是一種基礎鞏固的文明;而西方文化則是比物質文化更低一級的機械文化,是正在建筑中的屋子。從辜鴻銘對中西文化比較的論述來看,辜鴻銘看到了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優劣,并提倡兩種文化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但其中還是難掩辜鴻銘對中國文化的贊揚和對西方文化的批判,這是因為辜鴻銘看到了西方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動蕩以及西方社會的失序,并看到了中國文化中蘊含的獨一無二的價值。同時作為華僑,面對當時外國人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蔑視,內心中強烈的愛國主義讓辜鴻銘選擇以一種看起來極端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文化,所以與其說辜鴻銘對中西文化持有保守主義的態度,不如說他是披著保守主義外衣的愛國主義者。而在辜鴻銘思想中體現出的愛國主義、文化自信、文化之間交流的態度以及對現代化進程的反思,都是我們今天值得借鑒的思想精華。
參考文獻:
[1]黃興濤.辜鴻銘文集:下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 高令印,高秀華.辜鴻銘與中西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3] 唐慧麗.“優雅的文明”:辜鴻銘的人文理想新論[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0.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
作者簡介:張爽(2000—),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