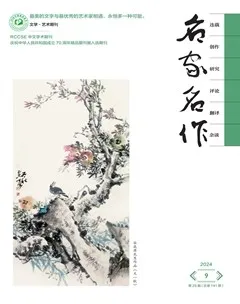雨果:用人道主義探尋“愛的藝術”
[摘 要] 維克多·雨果被譽為“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其人道主義已然成為雨果筆下的浪漫因子,他用“美丑對照”的詩學觀念,來描摹人道主義的理想藍圖,最終追尋那“愛的藝術”,反思愛的方式和人愛的本質。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可以說是其人道主義踐行失敗的代表,而《悲慘世界》則成功踐行,這兩部作品中的愛都受到宗教的影響。從這一敗一成的兩部文學作品出發,通過分析作品中人物的各種愛,來反思宗教對“愛”的影響,探究人性之愛和人道之愛,并進一步探討分析雨果所追尋的人道主義其實是“父性基督”之博愛。
[關 鍵 詞] 人道主義;父性博愛;美丑對照
雨果是法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領袖,在其生命盡頭他這樣總結自己的創作: “我在我的小說、劇本、散文和詩歌中向權貴和鐵石心腸的人呼吁,替小人物和不幸的人鳴不平,恢復了小丑、聽差、苦役犯和繼母的做人權利。”這“做人權利”就是雨果人道主義理想的踐行,而踐行的方式正是用愛。何為“愛”?如何 “愛”?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說道:“愛,不是一種無需花費精力的享受, 愛是一門藝術,它需要知識和努力。”雨果用《巴黎圣母院》和《悲慘世界》回答了這個問題,《巴黎圣母院》中通過“圣母院”將主要人物與“愛”聯結,寫出了愛斯梅拉達一見鐘情的癡愛,伽西莫多感恩式的錯愛,巴格特修女與克洛德偏激的私愛;《悲慘世界》用“冉阿讓”將人物與“愛”掛鉤,使這個悲慘世界沐浴到愛的溫暖,比如冉阿讓和珂賽特被給予的重生之愛。這兩部作品中的愛是為了制“惡”,《巴黎圣母院》失敗,人性之愛最終沒能戰勝以圣母院為代表的宗教力量,《悲慘世界》成功,人道之愛最終給他們帶來了一扇“門”。本文從這兩部作品出發,對人性之愛加以剖析,探討雨果的“愛的藝術”,通過“美丑對照”來思考宗教對人愛的本能的影響和人愛的本質,同時跳出人愛的人愛來窺探雨果內心強大的期待:用偉大的人道之愛去改善虛情假意、真情沉滅的社會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雨果的人道主義其實就是“父性基督”之愛,同時思考要如何愛,才能避免“被異化”這一人類無法超越的困境。
一、愛的失衡:“圣母院”與人性之愛的對抗
美丑對照原則最早出現在雨果被認為是浪漫主義宣言書的《克倫威爾》序言中,他認為美丑在大自然中客觀并存,文學作品中僅有“美”是單調枯燥的,崇高與崇高之間很難產生對照,而滑稽丑怪作為一種比較對象、一個出發點,卻能使人產生新的感受而朝著美上升,產生閱讀的震撼體驗。本文不從人物與人物的對照出發來看該原則運用的效果,而是將其聚焦到一個人的內心思想深處,窺其人物自我本身在愛問題上存在的“美丑”。同時,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序中寫到,在圣母院墻上“有這樣一個手刻的單詞:‘ANA1KH’ ”,這些字母蘊含著 “悲慘的宿命的意味”[1]1,從這里就可預判到書中人物的悲慘命運。但是,正如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言“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從《巴黎圣母院》悲慘的結局中,能看到“圣母院”所代表的宗教力量對人愛的撕扯毀滅以及各種愛的失衡,可以讓我們反思那最有價值的東西的本質——人性之愛。
愛斯梅拉達是美、善、愛極致存在的集合體。她敢于追求夢寐以求的愛人弗比斯,能大膽把握機會,抓住愛情之繩。然而,占據她生命全部的男子——弗比斯,卻是一個面俊心惡、追求肉欲和名利的不懂愛的世俗男子。“弗比斯”這個名字,本義是太陽神,象征著溫暖和美好,但是這個男子用他的人格灌注給這個名字完全另樣的生命代表,在愛斯梅拉達被捕之后,他回到了他的連隊,根本不想親自出庭,“發現在這段經歷里巫術的成分倒比戀愛的成分多些,她或許是一個女巫,或許是一個魔鬼吧?那歸根到底是一場滑稽戲,或者像當時的說法,一場很乏味的圣跡戲罷了,但他卻在其中扮演了一個相當愚蠢的角色,一個被打擊和被嘲笑的目標”, 甚至對此感到一種“拉封丹曾經描繪得絕妙的那種羞恥”[1]307,從這一點就能看出雨果對那“美好外衣”的懷疑,用名字解構了這類人的本質。他們的愛其實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文中總是用“孩子氣”來形容愛斯梅拉達,更用其來定義她的愛情,她這樣形容愛情:“那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合成一個天使。那是天堂。”[1]91這說明她是介于成人和兒童之間、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共存狀態,這是她愛的弱點,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指出愛有成熟和非成熟的形式之分,非成熟的愛是病態之愛,只有成熟的愛才是真正的愛。另外,弗比斯從一開始愛的就是她的美麗皮囊。這種“一見鐘情”式的愛情索取了愛斯梅拉達的生命,這就證明了此種愛的危險性,而弗比斯卻不被要求付出相關責任,這又反映了社會對男女在道德規范上不平等的事實,可以說這種不平等擊敗了她的“孩子氣”式的愛,從而造成一種失衡。
此外,為愛而付出生命的還有雨果“遺形取神”所塑造的伽西莫多,他因長相奇丑無比而只能依靠圣母院來生存,以敲鐘獲取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可以說伽西莫多表現出來的內心世界是陰暗的、漆黑的、沉悶的,當然這是長期缺愛的必然結果,所以愛斯梅拉達的一杯水就能使得伽西莫多流下生命史中的第一滴眼淚:“那一直干燥如焚的獨眼里,滾出了一大顆眼淚,沿著那長時間被失望弄皺了的難看的臉頰慢慢流下來”[1]210,那陰沉的生命世界被那善的陽光猛然照亮,但是由于長期昏暗,這出乎意料的善之光會被伽西莫多自身過濾,變成了相當強烈的愛之光,但自己最終被這光反噬而失去生命,這類似犯罪心理學中所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像極了《紅樓夢》中被薛蟠所強奪但一心一意地跟從著薛蟠、忠愛著薛蟠的甄英蓮(香菱),在這一點上看到了愛的失衡,警示我們給予愛的對象有時是要有必要的深思,否則會成為被愛者的桎梏。但我們在伽西莫多身上發現其實他的內心本質是光亮的、美好的、善良的,他將它封存是為了保護自己,和這個充斥著嘲笑、鄙夷、冷漠的世界對抗。
同樣由于愛上愛斯梅拉達卻無法沖破“圣母院”桎梏,而選擇死亡來結束痛苦的內心撕扯的還有克洛德。克洛德的一生成也因“圣母院”,敗也因“圣母院”。他愛她,但是他不懂得“愛的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克洛德的愛是自私極端的。收養“怪物”伽西莫多,撫育親生弟弟若望,然而伽西莫多從來沒有從外表所帶來的自卑心理走出,弟弟若望的人格也令人鄙棄,這種愛還不能達到真正意義的母愛,或許可以說是性別限制,但是我認為更多的是人格限制。克洛德的人格是不具有“屬我性”的,而是一種迎合當時“圣母院”的需求,按人們的觀念進行自我塑造,是為宗教活著,所以當他主動脫離世俗要求而追尋愛情時,他必然會造成人格失衡,從而異化他想得到的愛情。他披著一身代表圣神的宗教外衣,同時自己也被這一身外衣所轄制,其內心世界被其裹得透不過氣,使得他呈現出一個外表光鮮但內心缺愛的自由之氧。另外,愛斯梅拉達的母親巴格特不愛自己也不懂愛,在玩弄青春后墮落,在孩子被搶后受“圣母院”的影響而在老鼠洞中當修女,當其看到愛斯梅拉達即將被處以刑罰時是痛快的,而當她認出愛斯梅拉達是自己尋找多年的親生孩子而不是自己認為的埃及女巫時卻又極力保護愛斯梅拉達,這實質上是具有偏執的母愛與廣闊的人愛之間的失衡,這種母愛具有強烈的排他性,靠著血緣來維系,而這還不是雨果所追尋的人道之愛。
二、愛的救贖:人道之愛與救贖意識的躍遷
弗洛姆針對愛的異化,以人道主義為基點提出了“愛”的救贖方案,即創發性,就是自己去創造,首要因素是給予,這類似于雨果的人道之愛。《悲慘世界》中,雨果將一種救贖之愛灑向這片悲慘的土地。用冉阿讓的生命演澤人道之愛的救贖光澤,同時他的坎坷人生讓我們看到其救贖行為選擇下的救贖意識的躍遷:跳出狹隘的宗教要求,躍遷到一種人道之愛,同時向我們展示了在這種躍遷過程中救贖者和被救贖者的心理錯位。這種人道之愛其實也有影子,正如太陽光的投射一樣,這種“影子”的實質其實是人性的缺陷,這又說明雨果對于自己人道主義的理想的認知是清醒的,因為有種超越人性的現實。
冉阿讓的生命轉折是人道之愛所帶來的救贖,當他出獄時拿著黃護照,神情狼狽不堪,衣著粗鄙凌亂,把自己的臉深深地、深深地壓在帽檐底下,遭到所有人的排擠和拒絕,他似乎敲過了所有的門,甚至企圖在狗窩里尋求一點點溫暖和庇護,仍然沒有得到“許可”。在他對這個世界充滿怨懟、敵意、憤怒、仇恨時,卞福汝主教將善與愛的橄欖枝投向冉阿讓,給予他尊重、豐盛的美餐、舒適的床和他自己盜取的六副銀器和大湯勺,并說“您現在已不是惡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贖的是您的靈魂,我把它從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棄的精神里救出來,交還給上帝”[2]95,此后冉阿讓經歷了一番巨大的思想掙扎:他在田畝漫無目的地走著,在遇見小克倫威爾后,“他的膝彎忽然折下,仿佛他良心上的負擔已成了一種無形的威力突然把他壓倒了似的,他精疲力竭,倒在一塊大石頭上,兩手握著頭發,臉躲在膝頭中間,他喊道:‘我是一個無賴!’他的心碎了,他哭了出來,那是他第一次流淚”[2]111,這一刻,冉阿讓看到了自己和顯現在他良心上的光,甚至對那個自己有種強烈的反感,然后在比孩子更慌亂的猛哭后接過這一橄欖枝,獲得了靈魂的救贖,并用一生來播灑卞福汝傳給他的人道之愛,被這愛所拯救的有芳汀、商馬第、沙威、格呂斯、珂賽特等。值得思考的是,他不得不用一套名字來遮掩苦囚役的真實身份,這樣才能讓人道之愛被人所接受、銘記、尊敬,這在一定程度上又說明了書中那些渴求愛但不懂愛的人的自我欺騙性,所以當“馬蘭德”這一名字被冉阿讓自己揭開面紗之后,那個市的人們就不再認同他,甚至鄙夷他、忘記他,那愛在他們心中馬上就煙消云散了。這種愛的包裝構成了躍遷,這可能正是雨果所要向人們展示的人道之愛在這虛構的文學世界的缺失,這種缺失構成了雨果的人道主義理想,似乎雨果自身又明白這種理想在現實世界的不可能性,所以通過冉阿讓所展現。
另外,冉阿讓這種人道之愛存在著自身躍遷的一面。冉阿讓把救贖之愛給過著黑暗生活、缺失母愛的芳汀的孩子——珂賽特,讓她重新找回被愛的體驗,滿足被愛的需要。但是當珂賽特的少女心萌動之時,冉阿讓感受到了強烈的危機感,“這個人,能接受一切,原諒一切,饒恕一切,為一切祝福,愿一切都好,向天,向人,向法律,向社會,向大自然,向世界,但也只有一個要求:讓珂賽特愛他”“得到珂賽特的愛,他便覺得傷口愈合了,身心舒坦了,平靜了,圓滿了,得到酬報了,戴上王冕了”[2]890-891,這是人性自私的赤裸裸的展露。所以,真的存在著真正人道式的愛嗎?這正表明雨果對這種人道之愛的反思。此外,冉阿讓的救贖行為也值得思考,他總是因為給予他人無私的愛而被認出,一次又一次揭開刑犯身份,再次陷入危機,比如給裝成乞丐的沙威救助、給德納一家救助金等,這都說明了冉阿讓的愛是包含了某種混沌感的,他認不出他們,構成一種躍遷。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恰恰是雨果讓我們所要思考的:真正的人道主義之愛是會完全成為一種習慣,但是這種無防戒心理的愛又容易給自我帶來困難。
三、愛的“基督”:人道主義與本性之愛的復歸
雨果的人道主義是:要關懷人、愛護人、尊重人,以人為本,包含“平等”與“博愛”觀念,傳播正能量,從而感化他人、感化社會。所以,他的人道主義之愛,筆者認為乃出于為男性者的父愛本性,但這種愛是超越一般意義上的父愛,跳出人愛的人愛,包含著雨果內心強大的期待:用偉大的人道之愛去改善虛偽無情、真情沉滅的社會現實。這種人道主義之愛具體而言就是父性博愛,蘊含著人類普遍性的真摯情感。他在《巴黎圣母院》和《悲慘世界》里用美丑對照原則,用充滿巨大力量的感情表現出了一種高尚的愛,來嘗試讓人的本性之愛得到復歸,創造了一個屬于全人類的人道主義之愛的范式——父性博愛,同時,又把自愛作為其基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雨果浪漫主義之愛的具體投射。
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現心靈的美和崇高的是伽西莫多和愛斯梅拉達。在甘果瓦面臨生命危險的時候,愛斯梅拉達主動犧牲自己的婚姻來保住其生命,伽西莫多面對即將遭受制裁的愛斯梅拉達時,伸出援手救走愛斯梅拉達,這兩個崇高的靈魂,最終以結束生命來反抗“圣母院”所代表著的宗教及人性的黑惡勢力。此外還有克洛德,他在沒有被困于圣母院編織的網之前,他離雨果所提倡的人道主義之愛的距離是不遠的,他明白“人是需要感情的,他知道沒有溫情,沒有愛的生命,就像一個干燥的車輪轉動時格軋格軋的亂響” [1]132,當他肉體死去,而精神沖出“圣母院”的枷鎖后,那愛的本能就重新回到其身上;在《悲慘世界》中“父性”更是被冉阿讓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獲得了卞福汝的救贖,又用自己的一生去救贖他人,用一種超凡的力量,給予他人人道之愛。另外,還有因開朗的性格、頑強的生命力而演變成法國文化中擁有此類性格的人的代名詞,且象征著樂觀、可愛的粗鄙以及因為年少時一無所有而對人生的種種危險甚至死亡都顯得極不在意的性格特征的伽弗洛什,他在兒時就展現出與年齡極不相符的父性的一面,比如他收養照顧被迫在街上流浪的兩個馬儂的“孩子”。雖然這些人物都逃不了人性的某些弱點,但是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人道主義之愛的 “復歸”,并且通過不斷地播愛而拯救一個個靈魂,比如冉阿讓放走了一直追捕他的沙威,他本可以開槍結束沙威的生命,同時結束他被追捕的恐懼。沙威在冉阿讓的父性博愛的沖擊下,在自我的反省當中看到了冉阿讓善良的生命本質,看到了自己被法律、規訓所帶來的盲目,由此他展開了一場思想斗爭,最終選擇跳河自盡,他是希望通過河流來洗滌自己思想上的污垢,凈化靈魂,從而獲得一種超脫。
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指出:“最基本的愛是博愛,它是所有形式之愛的基礎。”[3]47博愛是雨果人道主義的關鍵,愛所包含的基本意義與使被愛者體現出人類本質特性直接相關。因此,愛一個人就意味著愛人類,但筆者認為雨果的博愛是建立在自愛的基礎上的。從《巴黎圣母院》到《悲慘世界》,我們可以看出雨果筆下的有些人物,他們的人格不斷健全,越來越有自愛的能力,在擁有自愛的能力之后更加把那種博愛給予這個世界,比如愛斯梅拉達,她愛弗比斯,但是自愛殘缺,也正是因為這種不健全、不成熟的愛而失去了自己的性命;而冉阿讓是首先完成了一場自我救贖,會愛自己之后,才去愛別人的。所以,雨果人道主義所追尋的父性博愛的基礎是自愛。
另外,雨果在其《靜觀集》中的《我要去》寫道:“人就應當以普羅米修斯,以亞當為榜樣。人應該從巍巍天宮偷取長明之火;應該去揭穿籠罩自身的玄虛,并把上帝偷來。”[4]面對充滿虛無、偽善的世界,雨果再次表明只有讓愛變成父性博愛,人才能為人,其所倡導的人道主義就是在表明自己對父性博愛的追求,我們可以從中看見雨果內心的強烈期待。值得思考的是,他把這種愛的希望寄予在《悲慘世界》中的伽弗洛什身上,一方面孩子是代表著希望的,是人類生命史的接續者,他可以接續日益衰老的冉阿讓,把這種父性之愛傳承下去,所以雨果塑造了這個小小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從“孩子”的眼觀看,與丑惡的政權革命不過是一場游戲,但是因為“父愛”的力量弱小,過于“孩子氣”,其實是不能獲得成功的,所以文中的伽弗洛什在撿子彈時被敵人打中,在革命途中嗚呼哀哉,這樣有著覺醒的人道主義之愛意識的孩子,最終未能從那異化的社會中被拯救出來,并且被伽弗洛什照顧的孩子,在獲得短暫的安全和溫暖之時,由于“革命”,又重返流浪的生活,逃到“革命”中那無人問津的花園,當然這又是雨果對自己理想的“父愛基督”不能實現的自我清晰的思考,正是不能夠實現,所以內心的期待更加強烈,也看出雨果想要自己做覺醒的父性人道主義者是相當困難的,但雨果也在積極踐行他的這種愛的“基督”。雨果不僅是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人道主義的代表人物,更是作為法蘭西民族的民族詩人和人民詩人,將文學與民族精神、人類發展聯系起來,就像魯迅所說的文藝作為“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便負有“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塑造“精神界之戰士”的職責[5],而且他對于這種愛的“基督”有著更廣的思考,把視野擴展到人類永恒存在之上:人類必然要經歷帶有周期性的磨難,如何在人道主義之上實現這種父性之博愛,是每一代人必須面臨的困難,只要人類存在,就要為此努力;他還在普法戰爭的硝煙中,揣著熾熱的情感,積極投身于斗爭之中。他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激勵人民的斗志,并毫不猶豫地報名加入了國民自衛軍的行列。
總之,愛是一門藝術,在雨果筆下的愛主要是受宗教影響,這構成兩個極端,一種為冉阿讓所代表的父性式的人道之愛,另一種是以克洛德為代表的沖破教條思想束縛的異化之愛。如何愛?怎樣去愛?怎樣才能避免愛被異化?這是人無論在什么時候都必須面對的困境。弗洛姆還指出愛在現代社會衰變就是因為 “現代人與他自己、與他的同類、與他的本質異化了。他被轉變成一種商品;在現存的市場條件下,他對自己生命力的體驗變成一種必須帶來最大回報的投資”[3]86。因此,雨果用他的人道主義追尋“愛的藝術”,筆下人物愛與被愛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刻的思考,這種父性式的人道主義之愛是我們當下需要去學習的。
參考文獻:
[1]雨果.巴黎圣母院[M].陳敬容,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2]雨果.悲慘世界:全 3 冊[M].李丹,方于,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3]弗洛姆.愛的藝術[M].李健鳴,譯.商務印書館,1987.
[4]雨果:雨果詩選[M].程曾厚,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226-227.
[5]魯迅.摩羅詩力說[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01-102.
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
作者簡介:褚梅娟(2002—),女,漢族,云南玉溪人,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本科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