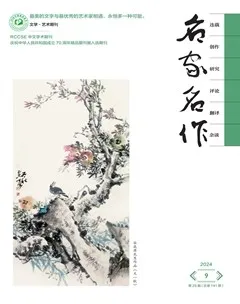高建群小說中的女性“出走”敘事
[摘 要] 當代陜西作家高建群的小說中有大量關于女性人物“出走”的敘事,其中,一類是為了追求內心自足而歸隱,或主動皈依佛門的“出走”;一類是為了追求自由或某種信念,超脫生死、瀟灑生活的“出走”。這種女性“出走”敘事是高建群在民族和國家視域下對女性命運的觀照與書寫,是文學史上有獨特意義的敘事方式。
[關 鍵 詞] 高建群;女性書寫;民族國家;“出走”敘事
女性“出走”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母題,西方經典文學作品中的簡·愛、娜拉、安娜·卡列尼娜等女性為了擺脫家庭或男性的束縛而出走,去尋求幸福和自由。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女性“出走”更是數不勝數,例如,胡適的《終身大事》里的田亞梅反抗包辦婚姻,毅然離家出走;魯迅《傷逝》里的子君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宣言,勇敢出走,與涓生戀愛同居;丁玲筆下的莎菲、貞貞等女性為了追求人生理想和價值而從舊日的生活圈子里出走;曹禺劇作中的女主人公為了追求幸福、自由和希望,或發瘋,或死亡,或逃亡,都顯示出決絕的“出走”姿態;巴金《寒夜》里的曾樹生以拋夫棄子的“殘忍”之心而離家出走,振翅高飛。“出走”成為現代文學中的一個顯著現象,作家以“出走”來啟蒙女性的覺醒,也展現了中國現代婦女解放的歷程。
當代作家高建群筆下的女性人物在民族紛爭、國家動蕩的時代背景下,往往擔負著政治使命和家族復仇的重任,這也是歷史長河中諸多女性的命運。但這些女性最后在完成使命和重任后決然出走,或者皈依佛門,或者超脫生死。這種不尋常的女性“出走”結局,是作者對民族、國家空間中的女性命運的思考,女性的“出走”敘事寄托了作者獨特的人文關懷和詩意想象。
一
高建群小說中的女性“出走”敘事實質上分為兩類:一是為了追求內心自足而歸隱,或主動皈依佛門的“出走”。例如,《統萬城》里敬諾利亞公主毒死入侵歐洲的阿提拉大帝,拯救了羅馬城,卻沒有選擇做英雄,而是選擇出走,隱居故鄉;羅什公主和鳩摩炎結婚生子,為龜茲國留下一位堪當重任的宰相后離家出走,成為一個到處修建佛洞的行者;莫愁毒死赫連勃勃,完成了家族復仇的大任后,主動為佛教獻身,成為肉身石像。
高建群長篇小說《最后一個匈奴》中用不少的篇幅講述了匈奴民族的歷史,其中游牧、遷徙到歐亞大平原的北匈奴在阿提拉大帝的帶領下進攻羅馬城時,羅馬大主教以不可辯駁的權威要求公主在危難時刻擔負重任,并用“不朽”的名頭引誘她獻身于阿提拉。其實,不管是否能“不朽”,敬諾利亞公主都沒有拒絕的權利和資格,因為作為公主,她只能為民族及國家利益著想。最后,公主服從政治使命,與阿提拉結婚,并以慢性毒酒毒死了阿提拉。但完成政治使命的敬諾利亞并沒有回到羅馬城做英雄,相反,敬諾利亞此生再未踏進羅馬城,她還乞求世界忘記她的名字,最后懷著阿提拉大帝的遺腹子回到了故鄉難產而死。這樣的結局是公主自己選擇的,她對阿提拉有沒有感情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她出走羅馬的結局似乎暗示了女性對政治權威的唾棄和抗爭。
在《統萬城》里,敬諾利亞公主的故事還有另一個版本的描述。據傳她16歲時就與近衛軍軍官私奔,羅馬帝國將她軟禁在監獄,她不斷地給阿提拉寫信表達她對英雄的愛慕之情,并且教唆阿提拉攻打羅馬城。這樣的公主無羈而放浪,注定有著不平凡的命運。敬諾利亞毒死了阿提拉后嘆息:“我殺死了一位英雄,我結束了一個時代!”[1]她給哥哥寫了一封信告知阿提拉已死,他可以高枕無憂地繼續做皇帝了。高建群塑造了這樣一個驚世駭俗的公主形象,她讓男性統治者膽戰心驚,她無視政治權威,隨心所欲地撰寫和改變歷史。也許她內心有過掙扎和猶豫,處在政治使命與個人意志的夾縫里,她感到生命的無聊與虛偽,所以她最后遵從了政治使命,但充滿了不屑與嘲諷,并拒絕國家賜予她的虛空的光環,堅定地走向屬于自己的道路。
《統萬城》里還有一位羅什公主,她是佛教高僧鳩摩羅什的母親。遵照父親的吩咐,她扮作牧羊女假裝“邂逅”鳩摩炎,然后生兒育女,目的是為龜茲國留下一位仁智的宰相。她起初為了國家利益來誘惑鳩摩炎,完成公主的使命,并接連生下三個兒子。但有一天她卻放棄了幸福的家庭和宮廷生活,游歷西域,留下風一樣赤著腳行走的倩影,帶著兒子鳩摩羅什出家修行,廣建佛洞石窟,成為半神半人的耆婆。當尊貴的公主成為手腳粗糙的勞作者,雖然生活清苦卻甘之若飴,這顯示出她生命意識的覺醒。“女性自我意識的生成和覺醒,必然上升到對自我價值與人生意義的探索與思考。”[2]這句話也許能解釋羅什公主離家出走的原因,也表明女性主體意識蘇醒后,能夠理性思考,決定自己的人生道路,開始對自己傳統的單一民族及國家的身份有了反思與質疑。
《統萬城》里最后一個匈奴王赫連勃勃的身邊有個鮮卑族的貴族女子莫愁,本與赫連勃勃情深意厚,勃勃卻因為政治野心和私欲謀害了岳父,身為女兒的莫愁必須為父報仇,她的內心痛苦萬分。但是家族使命和政治利益無視莫愁的愿望,將她當作復仇的工具,殺掉愛人,以此報仇雪恨。父親的至上地位正是父權社會的基石,因此,為父報仇是子女應盡的義務與責任,這是一種孝道,反之,就是大逆不道。這種孝道思想經常被父權社會的統治者利用,把它當作民族及國家的意志,實則卻包藏著政治利益。當莫愁每晚用鮮艷的鴆鳥羽毛拂過赫連勃勃的酒杯時,她成了復仇女神;當她撫琴吟唱古歌時,內心充滿了憂傷與悲哀,仿佛是天鵝最后的絕唱。最后,莫愁毒死了赫連勃勃,心中卻無復仇成功的快意,她只身離開了統萬城,成為一具盲目行走的軀體,走在與赫連勃勃曾經相遇的道路上。民族及國家的意志就是這樣讓一個弱女子內心掙扎而痛苦,奪去了她想要的一切,最后淪為一顆復仇的棋子。所幸莫愁最后在石碴河千佛洞里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成為一尊肉身女菩薩。高建群安排這樣的結局,揭示了民族及國家權威對女性主體欲望的強行扼殺,深切同情和理解女性的心靈空虛和痛苦,當歷史的車輪碾壓在女性的軀體上時,也許唯有宗教能填補她們殘破的心靈。
二
高建群小說中的另一類女性“出走”敘事是為了追求自由或某種信念,超脫生死、瀟灑生活的“出走”。例如,《遙遠的白房子》里的薩麗哈在經歷了馬鐮刀之死后,超脫生死,成為一個從紅塵中出走,超越時光的神秘女人;《最后一個匈奴》里的黑白氏從儒家正統文化里“出走”,無視禮教約束,大膽地追求情愛;丹華從中國傳統文化里“出走”,游歷于東西方,超越母國的種種束縛,瀟灑生活;《統萬城》里有個半人半神的女薩滿,借助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權力,從等級森嚴的政治框架中“出走”,實現和滿足了自己的世俗情感和欲望。
中國歷史上的北方民族——匈奴,是個桀驁不馴的“馬背上的民族”,他們的血液里流淌著自由的天性,他們崇拜生命,大膽追求性愛。高建群早期的小說《遙遠的白房子》里有個匈奴族女性,名叫薩麗哈,她多情而單純,愿意用她豐滿的胸膛給所有男人以溫存和愛撫。這是民族天性使然,她好像不諳人事,全然沒有儒家正統文化的羞恥和不潔感。她成為牧人的妻子卻和馬鐮刀私通,成為馬鐮刀的妻子卻處處撩撥士兵。馬鐮刀秉持儒家愛情倫理,要求女性從一而終、貞潔自持。以馬鐮刀為首的男性一味壓制女性的欲望,卻對自身行為不加節制和不作反思,是典型的父權社會里不平等的男尊女卑現象。馬鐮刀死后,薩麗哈最終遵從了儒家愛情倫理道德,滿足了男性的欲望,為其守身保貞。但是,她的遭遇恰恰說明她是男權文化的受害者,是一股對男性構成威脅與顛覆的力量,她不僅是情欲領域中的抗爭者,更是反對父權中心的吶喊者。
《最后一個匈奴》里的黑白氏,在受到丈夫冷落后,為滿足情欲,曾試圖勾引家里的長工;多年后,又為營救情人,準備沖擊牢獄,將兩人多年的地下情公之于世。高建群讓這樣一位敢愛敢恨的女性形象躍然紙上。
《最后一個匈奴》里還有一個匈奴后裔——現代女子丹華,其桀驁不馴,反叛世俗,個性鮮明。她是獨立干練的女記者,也是擁有30棟樓盤的女老板,瀟灑地行走在時代前沿。她像她的先祖一樣,酷愛游歷,有著不羈的靈魂。同時,她深受西方開放思想的影響,她的性愛觀更加大膽地挑戰了傳統道德倫理。她與楊岸鄉在異國邂逅重逢,熱烈地共度良宵,卻在結束后告訴對方:這只不過是逢場作戲的一夜風流,雙方以互相取悅為目的,不應有附帶條件。雖然這在西方世界是比較普遍的事情,但對傳統東方文明下的愛情倫理觀來說,不啻一記雷電,擊碎了那個年代陳舊的觀念。高建群寫黑白氏與丹華作為匈奴人的現代后裔,將先祖們追求情欲的天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寫她們忠實于自己的肉體和靈魂,注意到她們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反叛了把女性工具化、肉體化的傳統男權思想。
在匈奴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女薩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們是半人半神、可以通天的巫婆,額頭一只獨眼,能看到遙遠地方發生的事情。她們為民族的興盛祈禱,為統治者出謀劃策,并且預言未來。她們因此而進入男性統治秩序,干預國家政治。《最后一個匈奴》《統萬城》中匈奴國的阿提拉大帝和大夏王赫連勃勃父子身邊都有這樣一個獨眼的女薩滿,她們地位頗高,身為女性,卻借助神性身份介入權力系統。身體上的“獨眼”反倒造就了身份、地位的特殊,就連赫連勃勃都想把三個女兒培養成女薩滿,讓她們日后能在草原上呼風喚雨。相較于同時代的女性,女薩滿活得恣意而驕傲,似乎民族及國家意識形態與女性個體權力得到了契合。
同時,高建群小說中描述的女薩滿充滿了世俗的情感和欲望。女薩滿通常還會做些接生、治病救人的工作,當她們的神力為普通民眾服務時,她們才流露出自己真實的女性欲望和情感。《統萬城》里的赫連勃勃踏上征程之初,女薩滿從各個方面教導和指引他,甚至親身教他用男歡女愛的手段討女人歡心。“女薩滿說:‘人類之所以能活下去,一直活到今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這別樣的快樂。’說這話時,女薩滿的嘴角掛著一絲曖昧的、肉欲的微笑。”[1]這時的女薩滿從“獨眼”的神性束縛下解脫出來,流露出主體的欲望和情感。這種情欲的滋生與宣泄是打著民族政治的幌子實施的,充滿了諷刺與悖論。也就說,在高建群筆下,民族政治欲望與女性主體欲望的對弈,在女薩滿這里是表面契合、實質利用的關系。女薩滿利用她特殊的政治身份順利滿足了內心的情欲,這是對民族及國家至高權威的挑戰和戲弄,但只能以半神半人的薩滿身份實現,又表明女性在強大的父權體制中臣服于男性的現實和低賤、惡劣的生存處境。
A+porQ/cjO8mzG4V6vgoyg==以上可見,高建群小說里的女性“出走”,是女性求得自身獨立的一種生存方式,這些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精神和思想層面的覺醒與自主。當女性深受民族和國家、男性權威的控制與支配時,或為政治利益,或為家族復仇,或為滿足男性的一己之私,她們被迫屈從,犧牲自我;當女性主體意識蘇醒或者由于內心自我的呼喚,她們又掙扎和不甘,有迷惘和失落,民族及國家與女性主體常常背離和糾纏,最終,這些女性在完成了民族及國家的使命后,往往叛離民族及國家的身份指認,走向不尋常的結局。這種女性“出走”的書寫體現了高建群對人物真實的主體欲望和現實處境的重視與觀照,由此也反映出高建群關于女性敘事的獨特旨趣,真實展現了女性話語與民族國家話語的分裂與悖論。
在父權制社會里,男性群體依據天生的生物學性別價值體系對女性群體實行全面統治,這一權力的獲得如同封建社會依據血緣和出身決定階級和身份一樣“理所應當”和“必然”,并且這一統治權成為一種制度化的政治關系。這種男人按天生的權力統治女人的權力結構和組合被稱為“性政治”,并且“無論性支配在目前顯得多么沉寂,它也許仍是我們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識和最根本的權力概念”[3]。當女性被置于民族、國家、男性政治的權力結構中時,民族、國家和個人關系的演變、發展和交織,往往在歷史的長河里留下女性沉默的眼淚和斑斑的血跡。高建群小說中同樣有這種“性政治”的框架,他書寫了意識形態召喚下的女性命運。但這些女性不同尋常的“出走”敘事,說明高建群并不是單純地將女性納入民族、國家的敘述框架,而是通過女性“出走”的敘事,從“人”的角度關注和尊重女性的主體欲望與生存境遇,真實展現了女性話語與民族國家話語的分裂與悖論。由此反映了作者較為豁達寬容的女性觀,在女性敘事上也有獨到的文學價值和意義。
參考文獻:
[1]高建群.統萬城[M].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3:198,53.
[2]郭興.廬隱創作的女性敘事[J].柳州師專學報,2014,29(6):14-16,19.
[3][美]凱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33.
作者單位:西安思源學院文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3年度西安思源學院教學改革課題“課程思政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課程性別教育中的探索與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3SYYB08)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李娟(1977—),女,漢族,陜西漢中人,碩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女性主義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