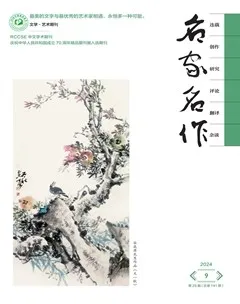補白:《故都的秋》中的悲涼美學與情感書寫
[摘 要] 當前,很多人對《故都的秋》中的悲涼美學缺乏認知體驗,同時易將以悲為美與悲秋相等同,錯失了對郁達夫獨特審美的探索。基于此,補白中國的悲秋傳統,爬梳以悲為美的歷史文化淵源;補白日本的物哀文化,探尋以悲為美的文化內涵;補白作者的文人情調,聚焦以悲為美的創作觀念,以期完整把握《故都的秋》的文學價值和美學價值。
[關 鍵 詞] 《故都的秋》;補白;悲涼美學
“時代、民族、社會形態、階級以及文化修養的差別不大能影響一個人對于‘花是紅的’的認識,卻很能影響一個人對于‘花是美的’的認識。”[1]朱光潛認為美是有社會性的,不同社會背景、不同時代的人對美的認知不同。對于《故都的秋》這篇彰顯郁達夫獨特審美趣味的散文而言,讀者囿于時代的隔閡與自身審美傾向的局限,如沿用以往慣常使用的從個人經驗出發來解讀作品,大抵難以品悟到其中以悲為美的審美內涵,導致作品解讀淺表化。尤其是青少年對郁達夫本人的文人格調較為陌生,難以理解作者以悲為美的審美品位,說不出這篇文章哪里美,甚至不覺得其是美的。由此看來,在鑒賞本篇文本時,可通過補白中國的悲秋傳統,爬梳以悲為美的歷史淵源;補白日本的物哀文化,探尋以悲為美的深刻文化內涵;補白作者的文人情調,聚焦以悲為美的創作觀念;以期完整把握《故都的秋》的文學價值和美學價值。
一、補白中國的悲秋傳統,爬梳以悲為美的歷史淵源
在這篇文章里,我們能讀到作者細膩詳盡地對北平之秋的工筆刻畫:庭院秋聲、破壁粗茶、花凋草謝、落花細蕊、掃帚細紋,還有時時哀鳴的秋蟬,秋雨中閑話家常、悠閑地聽雨賞雨的人們,甚至包括棗子、柿子、葡萄等清秋的佳果……沒有充分了解中國古代悲秋意蘊的人,是很難理解為何作者不寫北平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唱。
“各著名的大詩人的長篇田園詩或四季詩里,也總以關于秋的部分,寫得最出色而最有味。”的確,以唐詩的集本《全唐詩》為統計對象,量化分析的結果顯示,其中寫到最多的季節就是秋。對此文壇大宗韓愈有其獨特闡發:“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好之,則不暇以為。”就創作角度而言,抒愁苦之情、歌凄苦之聲更容易寫得動人心弦,令人傷感。由于地域的關系,中國文學同自7Fltua+s0+4btzgBCjEbWveXxns6BUU3sa3kje7m/Ac=然物候聯系甚密,秋作為四季當中最易惹人感傷的季節,悲秋情緒自此厚植在傳統士人的靈感土壤中,并在一代代的反復構建中凝聚著民族豐厚的文化內涵,逐漸沉淀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在中國古代文人文學的地層中沉積著悲秋文化激蕩、沖刷的痕跡。
才士悲秋的美感書寫及特定形式時常散見于歷代文人的詩詞歌賦中,《優古堂詩話》中說的“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其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便是此般意義。這些文人墨客將寒山、瘦水、殘荷、寒雨、冷風籠于形內又攝入筆端,而單寫秋中之物仿佛還不足以體現其沉郁、悲涼的內心一般,往往還特意將疏木枯葉、破月孤煙設為飄零肅殺的背景,使得凄寒愴遠的詩中寒氣越過千載,依舊蕩漾在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筆下。所有這些對悲涼異趣、與眾不同的審美追求,最終形成了秋士的名士氣派和異于常人的文人風度。由此觀之,郁達夫筆下“悲涼”的審美意趣,并非離經叛道,他沿襲了士人的悲秋傳統,并沉浸在其中。這是一種區別于庸常趣味的高雅情趣,非得在常人尋不到、品不出、嘗不透的地方才能咂摸出一二。
《長征殿·汪序》言:“曾聞秋士最易生悲,況說傾城由來多怨。”郁達夫與眾不同的是,他賞悲景,卻不怨,反而還覺得美。這與嵇康《琴賦》中“稱其才干,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陸機《文賦》中“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弦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鐘嶸《詩品》中“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體現出的“哀而不傷”更為契合。不僅于此,其中還隱約可見日本物哀文化的影響。
二、補白日本的物哀文化,探尋以悲為美的文化內涵
郁達夫寫故都的秋的頹廢、衰敗之美,雖繼承了傳統士人的書寫習慣,但卻向著西方美學的“向死而生”發展,秉承著日本文化里的“物哀”美學。不同于一般春女秋士的苦悶傷懷,郁達夫在賞玩殘隕;沉浸在凄苦哀颯的氛圍中,傳統秋士往往觸景生情,抑或被哀景所動以致情難自已,而郁達夫則是將自己浸潤在物哀的氛圍中,身臨其境地體驗、把玩秋給他帶來的與眾不同的感覺。這些細膩微妙之處,學生能隱隱約約感知到有些“不對勁”,但難點在于如何讓學生能夠準確認識并且了解到有這樣一種獨特的審美。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此時需要老師適當地補充,郁達夫在性情品格塑造的關鍵期,有長達十年的赴日留學經驗,這“既熏陶了他的感覺,使他精細敏銳,又局限了他的氣度,使他清瘦孱弱”[2],同時,他還深受日本文學中“物哀”的影響,其文字筆觸清晰可見“物哀美學”的統攝與發軔。本居宣長最先在《紫文要領》《石上私淑言》《源氏物語玉小櫛》中闡明與厘清“物哀”術語之內涵與價值,并首次將其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予以引證和闡述,即“物之心”“事之心”,“物”“事”主要指能夠引發“哀”感的事物,進言之是可以為人所感知、體察與理解的審美性的對象,在描寫的題材內容上,自然體現出鮮明的審美傾向和唯美訴求。一言以蔽之,用學者王向遠的話來說,就是“物心人情”,即“‘物哀’本身指的主要不是實在的‘物’, 而只是人所感受到的事物中所包含的一種情感精神”[3]。值得注意的是,物哀與頹廢并不等同,它的實質是倡導人感物興哀,可以對人情百態、天下大事和自然世界的各種情態有所觸發、引生,是一種善于感受優美、欣賞纖細、贊嘆哀愁的情感表現,敏感而多思的文人還往往于最絢爛之時可以窺見衰敗寂寥后的悲涼之美。悲與美不但不相抵牾,甚至就深層而言還相通相融。
郁達夫在《故都的秋》中對于意象營構出來的抒情層次,就是對物哀美學的借鑒,集中體現在他從無意識到有意識地品味“悲涼美”。從一開始對蘆花、柳影、蟲唱、月色等遠離城市熙攘與熱鬧事物的粗筆勾勒,到刻意避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熱門景點而是住“破屋”、靜讀“破壁腰”,再到對庭院里的“衰敗的牽牛花”“疏疏落落的尖細且長的秋草”等冷色調景物的刻意描摹,雖體現出其對日本“物哀美學”的沿襲與化用,但為何偏偏選擇此類景物入文的原因,還在于隨性而發的無意識狀態。
有意識是緣于秋槐落蕊的出現——不論是殘花落蕊,抑或是槐樹落葉,都讓他覺得“細膩”“清閑”“落寞”,這分明是將自己的主觀情感融入物中,與其說是郁達夫在賞景,毋寧說是作者在“孤芳自賞”,以至看到滿地憔悴的花蕊,聯想到古人所說的梧桐一葉而下天知秋,歲之將暮,葉落感懷,更是愈覺深沉,而作者本人就沉浸在其中,看見深沉,而不覺壓抑。下文更是覺得秋蟬是衰弱的蟬聲,都像是“特產”。這分明是將已經意識到的哀傷、蕭條、頹敗等復雜情感當作賞玩的對象。嘶叫哀鳴的蟬,其實早已成為古典詩詞中常見的意象,如“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猿啼三峽雨,蟬報兩京秋”(元稹《酬許五康佐》)。
郁達夫與眾不同之處在于,雖然沿襲并承認了蟬意象所蘊含的孤獨、哀傷,甚至恐懼等情感,但是將其當作賞玩品味的對象,他在欣賞衰敗、品味哀鳴,并稱贊其為“特產”與“家蟲”。可見其不但不覺得孤獨,而且還樂在其中,以至無不羨慕地說:“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聽得到的。”可見,他臻于極致地飽嘗了此般回味雋永的濃郁之秋。在這里郁達夫將物哀美學與悲秋傳統相結合,開拓了審美領域。生命的蓬勃值得欣賞,生命的頹敗隕落同樣值得品味,在享受優美帶來的愉悅的同時,亦可以浸潤在生命因有限性而造成的悲愴與蒼涼中,以濃情來眷顧“向死而生”的悲壯。在這樣的濃郁秋味之中,讀者如何會不隨著他一起,知“物哀”、明“物之心”,屏聲斂氣,滿懷“清”“靜”地靜觀萬物?怎么會不隨著他一起“賞玩”這“無限深沉”“悲涼”的秋味,貪戀著故都的秋呢?
補白這一概念,并不意味著對文本解讀本身的削弱,相反,這不但與學生的認知水平相契合,易于學生理解為何郁達夫有如此獨特的審美,即使我們不能也無須詳細地闡述與旁證為何郁達夫會有這般審美,但我們也不能對此置之不理,只停留在“以物觀物”,而無視“以我觀物”的主觀選擇性。
三、補白作者的文人情調,聚焦以悲為美的創作觀念
郁達夫作為中國新舊文學交鋒時期的文壇翹楚,既接觸了大量的西方美學原理,又積攢了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力,而其文學創作更是發軔于舊文學也止于舊體詩,這一脫胎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文人情調,浸潤《故都的秋》中,或許也正是這抹深沉的文人情調,使得郁達夫對于故都之秋產生了發乎濃情的眷戀,這眼光里分明閃爍著傳統士人的審美趣味,當其凝結成創作觀念時,則主要體現在郁達夫獨特的聲韻抒情與抒情夾議兩個方面。
其一,聲韻抒情。全文從頭至尾多為短句、散句,有意識地將情緒靜下來,聲調慢起來,語調拉長,讀起來不急不忙,雅態十足,并且還虛擬了北方人對話的場面,點評“北方人念陣字,總老像是層字,平平仄仄起來,這念錯的歧韻,倒來得正好”。平緩悠揚的語調,巧妙、精準地傳遞了作者悠閑平靜的心境。此類平仄、押韻、節奏等“外聲音”能不斷擊中讀者的心扉,文本蟬鳴、馴鴿的飛聲、閑話家常等“內聲音”更是可以引起讀者共振。這種頗具韻味的語言,讓整篇散文具有了詩的色彩。
不僅如此,在郁達夫看來,除了傳統的文字音韻外,自然本身就是最佳的韻律“四季的來復,陰陽的配合,晝夜的循環,甚至于走路時兩腳的一進一出”,合乎自然韻律方能物我交融。于是乎郁達夫憑借自己的審美想象,竭力將不同的生命形態配列,上攬天色、下俯落蕊、耳聽蟬鳴、眼觀秋草,不按順序、不從規律地將能體現秋所蘊含的生命意蘊的物體,競相納入文中。
由此看來,文中除了顯性的聲音韻律,還隱藏著南北韻味對比、自然萬物籠于筆下等隱性的獨特韻律。
其二,抒情夾議。結尾處運用了大量的篇幅與直接議論的話語來試圖為其以悲為美的審美進行合理闡發與謹慎辯護。“各著名的大詩人的長篇田園詩或四季詩里,也總以關于秋的部分,寫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見有感覺的動物,有情趣的人類,對于秋,總是一樣地特別能引起深沉,幽遠,嚴厲,蕭索的感觸來的。”這一片段的陡然出現,看似有些突兀,實則不然。其中正流露出作者深厚的文學修養,用倪文尖老師的話說是“這也是本篇文章區別于一般中學生作文的特殊所在”。
實際上,認真爬梳郁達夫的生平經歷會發現,這樣一位新文學的代表人物自幼與舊體詩交纏頗深。5年的私塾生活讓其受到傳統文學名著的熏陶,即使在新學堂讀書,也是“一味的讀書,一味的做詩”[4],積累了豐富的中國古典文化知識。一生更是創作了近600首舊體詩,且佳作篇篇,獲得了郭沫若、吳戰壘等人高度評價:“達夫的詩……確有李白的清新飄逸;但又不拘一格,而能出自唐宋元明清諸家,博采眾長,融李白……龔自珍眾作于一爐,視自己性之所近而取舍之,神明變化,存乎一心。”在此段中,郁達夫更是直接將歐陽子的《秋聲》與蘇東坡的《赤壁賦》點了出來,與文中引用的詩句一樣,無不是在向讀者展現其文人情調。
此外,這段議論更是彰顯其獨特的散文創作觀,即“現代散文”要“訴之于我們的智性”[5]旨在給予讀者智識,而這又需與情感價值聯系在一起,因而除了直接議論的段落外,智性因素還潛藏在其他抒情寫景文字中。“在北平即使不出門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住著,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
同樣有著古文基礎的文人會看到,這潛臺詞就是蘇軾的“萬人如海一身藏”與龔自珍的“城曲深藏此布衣”。通過引用古代典籍記載陶然亭、釣魚臺、西山、玉泉、潭柘寺等地名的由來,也讓文字之下的雅致浮現。
本文通過補白中國的悲秋傳統,爬梳以悲為美的歷史文化淵源;補白日本的物哀文化,探尋以悲為美的文化內涵;補白作者的文人情調,聚焦以悲為美的創作觀念;重新審視了《故都的秋》。讓讀者對本文的認識由零碎走向了整體,從分析審美表現到體認審美情趣,從淺表化解讀走向了深層次思辨,極大地豐富了文本的闡釋空間。
參考文獻:
[1]朱光潛.朱光潛美學文集:第1卷[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34-35.
[2]許子東.張愛玲·郁達夫·香港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166.
[3]王向遠.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審美概念的形成流變及語義分析[J].江淮論壇,2012(5):8-14.
[4]郁達夫.不驚人草[M]//郁達夫.郁達夫文集:第7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276.
[5]郁達夫.導言[M]//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5.
作者單位:長沙市周南中學
作者簡介:陳新春(1969—),男,湖南瀏陽人,本科,高級教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中學語文教學。
張晴悅(2001—),女,湖南婁底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學語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