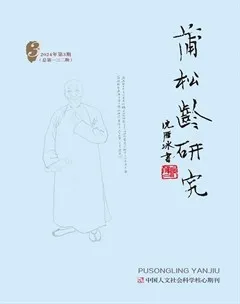聊齋影視改編的歷史衍化、敘事轉向及品牌塑造
摘要:《聊齋志異》改編為電影已有百年之久,回望聊齋影視改編的歷史衍化過程,了解社會文化的浸滲、鏡射和流變,洞悉名著改編的創作路徑、藝術旨歸和當代價值。聊齋影視改編起步于忠于原著、節選與挪用的搬演模式,久歷形神取意、嫁接與雜糅的拼貼模式,及至顛覆原義、重構與置換的整合模式。新時代語境下的聊齋影視創作,應在提升研究氛圍、開掘文化資源、創新敘事方式、拓展影視旅游、創生優質內容等方面深耕細耘,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塑造文化品牌,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
關鍵詞:聊齋;影視改編;歷史衍化;敘事轉向;品牌塑造
中圖分類號:I207.72文獻標志碼:A
《聊齋志異》是清初文學家蒲松齡創作的文言小說集,其文學藝術魅力恒久不衰,更被改編成戲曲、電影、電視劇、舞臺劇、廣播劇等多種藝術形式。百年以來,聊齋影視改編佳作頻現,以說狐談鬼道情,以闡幽喻世明理,將規勸、訓誡與勉勵等功能轉換為視聽語言并直抵人心。聊齋影視呈現體系龐雜、包羅萬象的整體特點,是視覺文化時代的精彩華章,并不斷推陳出新,建構出更具東方魔幻色彩的廣袤世界。
一、聊齋影視改編的歷史衍化
自1905年中國電影誕生以來,從歷史典籍、戲曲唱本、神話傳說、演義小說等文學題材中汲取素材和靈感,是影視創作中頗為常見、較為成熟的做法。這既與文學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原型、情節脈絡和主旨立意等構思設計有關,更契合了人們從抽象的文本閱讀跨越到直觀的視聽感受的文化心理。審視聊齋故事的影視改編歷程,也應注意歷史背景、時代精神和價值追求之間的耦合與互動。
(一)萌芽時期(1920—1949)
1922年,商務印書館取材《勞山道士》的無聲黑白電影《清虛夢》上映,使用了人走入墻壁、物體自己移動、水缸破而復原等特技攝影技術,開創了聊齋故事電影化的先河。早期電影又稱活動影片,配合簡單明白、婦孺皆曉的文字說明故事情節,涵蓋“教育、時事、風景、新劇、古劇”等五種題材。1923年,商務印書館推出《孝婦羹》,取材《珊瑚》篇的部分情節,沿用感悟家庭、維持風化的思想主題,但改“割臂作羹”為“做飯”之事,宣揚仁義節孝的傳統道德,以期裨益世道人心。姜欣榮認為,其“對原著作了啟蒙式的祛魅處理,為后續改編創作提供了重要范本與坐標參照” [1]I。
1925年,民新制造影畫片公司的電影《胭脂》上映。作為香港第一部長故事片,以時裝扮相,“寓意警世,橋段新奇,表情逼真,光線玲瓏,配景精致”,“警淫勵俗,最同近世社會情形,確能使人觸目驚心”,于劇情而言,影片幾乎照搬了原著設定。1926年,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馬介甫》上映。以說書人的口吻串起刁蠻惡婦遭報應的故事,并在片尾表明立場:本劇略加點綴,添出地獄之相,蓋亦冀觀者觸目驚心,有所警惕耳。宋碧洋指出,朱瘦菊“有意在這部電影中展現自己作為敘事者的在場,意圖在于更為直接的倫理教化” [2]89。此二作選材同源且主旨相近,可視作電影教育功能的現世表達。
1927年,明星影片公司的《田七郎》上映,以田七郎殺身成仁、舍命救友的故事為線索,描寫了人生甘苦之境及“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1931年,復旦影片公司的《巾幗須眉》上映。“‘聊齋兄弟分家’故事涉及到的眾多女性中,仇大娘是最為光彩奪目的一個” [3]47。影片刻意渲染了“苦守門庭,克勤克儉”的傳統女德和“敢于抗爭,知進識退”的人文精神,切中沉冤昭雪、闔家團聚的社會心理意識。同年,聯華影業公司的電影《恒娘》上映,“以最古雅的文章翻作最摩登的景物,以最公平的手腕解決社會妻媵問題”,夫妻關系和諧相處的立意,影射了民國社會的家庭倫理,強調教化人心的社會功能。
1935年,南華影片公司的電影《馬介甫》于香港上映,除保留原著人物的設定外,還增加了“潑婦逼夫賣國,志士手刃國賊”的情節,賦予主人公扶危救難的超然氣節,升華愛國警世的主題。1947年,歌唱片《莫負青春》大獲成功。吳祖光回憶說,影片中的V7R19Y+2tGonGc7zKfZVtg==三支插曲都由周璇主唱,當時唱遍中國以至東南亞很多年。[4]46影片突出青年戀愛主題,以自述口吻開篇收尾,以夢境消解神鬼氣氛,以溫婉音樂貫穿其中。“是男女的寶鑒,是戀愛的指南”,拌嘴打趣隨處可見,生活氣息濃郁,實屬難得的清新之作。
(二)探索期(1950—1979)
50年代的香港,南下影人分成“自由影人”和“進步影人”兩大文化陣營,“改編現代文學作品、古代經典文學以及西方經典文學作品蔚為風氣” [5]64。1954年,電影《人鬼戀》上映,因循民族古裝形式,諷刺封建社會疴陋,“刻畫人世間的丑和美,暴露幽靈中的惡與良”,將追求自由、為愛獻身的主題加以渲染。1955年,電影《阿繡》上映,劇中演員一人飾兩角,阿繡與狐仙同現熒幕,難辨真假的特技攝影,令觀眾眼界大開。
1957年,有五部聊齋電影上映,即《風月奇案》《半世老婆奴》《仙袖奇緣》《插錯美人頭》和《陰陽配》,大多為粵語歌唱片。吳月華提出,“電影的敘事風格繼承了仿真再現模式,而粵語歌唱片中的歌曲片段則將粵劇表現表演模式融入到電影的再現模式內” [6]133。《插錯美人頭》結合了丑角的詼諧表演,《仙袖奇緣》《陰陽配》則展示了神話、奇情類型片的獨特魅力,地方戲曲與聊齋故事的結合,以廈語片、潮劇、粵劇等為主。
1960年,大型歷史片廣受歡迎之際,善于迎合大眾的邵氏電影公司,看準聊齋題材的市場熱度,發揮李翰祥的導演功底,將古裝風格與恐怖類型相結合,制作出彩色電影《倩女幽魂》,片名借取自元代鄭光祖的同名雜劇。作為一部忠于原著之作,李翰祥注重運用典雅秀麗的場景布局,追求唯美真實的細節刻畫,斷壁殘垣、古琴雅韻、燈影婆娑等場景精心雕琢,確立了商業娛樂電影的民族審美特征。
1962年,李晨風導演了《富貴神仙》與《湖山盟》,前者為民國裝束的黑白電影,后者為實地取景的彩色電影。《湖山盟》反抗欺壓、善有善報的主流意識,蘊含著樸素的民本立場和生活氣息。這與新聯影業公司提倡的“嚴肅制作、講藝術良心、倡導向上向善”宗旨一脈相承,也為左翼電影創作開辟了新的題材類型。趙衛防認為,其一,“表現為創作者普遍擁有自覺的政治考量”;其二,“內地的政治肯定,在香港左派電影族群中營造出了相對寬松的創作氛圍,從而提升了影片質量”。[7]13
1963年,長春電影制片廠與香港繁華影業公司聯合攝制了評劇電影《花為媒》,取材《王桂庵》及所附《寄生》篇,成為評劇藝術的代表性作品。1964年,香港華文影片公司攝制的呂劇電影《姊妹易嫁》,大量使用了山東方言、俚語和民俗等戲劇元素。《花為媒》和《姊妹易嫁》均以有情人終成眷屬為主題,擷取生活化、日常化情節,打破了人們對聊齋故事的刻板印象。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邵氏、電懋、長城、鳳凰、玉聯、國泰等香港電影公司競爭激烈,推出了一大批聊齋電影,風格上大抵類似,同質化現象明顯。
1966年,從邵氏電影公司出走臺灣的李翰祥制作出《辛十四娘》,聊齋電影在臺灣打開局面。1969年的《人鬼狐》《雪娘》《王者神劍》,1970年的《小翠》《云翠仙》《鬼狐外傳》《俠女》和《喜怒哀樂》,1972年的《鬼新娘》《富貴花開》,一時佳作頻現。此后,“鬼才”導演姚鳳磐以《秋燈夜雨》(1974)、《寒夜青燈》(1975)、《藍橋月冷》(1975)等個性作品,開創了恐怖驚悚、哀情凄怨的“姚氏”風格。而胡金銓導演的《俠女》則將聊齋故事、新武俠風格和東方意境融為一體,斬獲第28屆戛納電影節最高技術獎。
70年代是“邵氏”電影由盛而衰的分水嶺,“由于過分強調商業利潤和生產規模,‘邵氏’已經不能滿足觀眾日益升級的欣賞口味” [8]83。1979年,重又回歸邵氏電影公司的李翰祥根據《畫皮》情節編導出恐怖片《鬼叫春》,秉承“重寫實氛圍、強故事情節、折子戲結構”等拍攝手法,開創了聊齋故事與風月片相結合的先河。
(三)創作繁榮期(1980—2000)
香港TVB創作聊齋劇集,始于1975年的《民間傳奇》。1987年,新加坡單元劇《奇緣》播出,其中的《辛十四娘》部分,情節忠于原著,敘事節奏流暢,特技運用嫻熟。1988年,香港亞洲電視拍攝的20集《聊齋志異》,選取了《畫皮》《花姑子》《三生》《姬生》及《伍秋月》等篇節,呈現出曲折離奇、凄美詭譎的獨特電視審美。1988年,臺灣電視公司啟動《中國民間故事》工程,采取邊拍邊播的運作模式,至1999年初共完成520個單元,與“聊齋”相關的就有《鸚哥報恩》等10余個,但由于時間跨度大,制作水準參差不齊。
1992年,香港TVB電視劇《人鬼狐》首次將魔道、武俠、神話等元素融入聊齋故事,以俠客、狐妖、殺手、女鬼等人物形象設定矛盾沖突,結合恩怨情仇的創作思潮,呈現出獵奇斗法、雜糅拼接的拼貼風格。1995年,臺灣電視公司推出《倩女幽魂前傳》,涵蓋《小謝》《小翠》《魯公女》《伍秋月》《珊瑚》《呂絲絲》等7個單元。聊齋劇集的持續火爆,致使香港TVB于1996年、1998年連續制作了兩部聊齋系列劇,更遠赴四川、云南取景,利用計算機特技制作,工于實拍場景的唯美,側重哲理悠長的抒情。“當時代潮水退去,眾多經典之作寫入香港電視劇歷史;當經典無法突破、超越時,‘再造經典’就成為TVB的新策略” [9]126。
1987年至1991年間,在福建電視臺的推動下,47部72集《聊齋》電視系列片陸續制作并播出,成為電視文化走向大眾市場的一道景觀。王林書認為,該劇具備相濡以沫的互助美;對于命運的抗爭美;女性的開放美三個淺層人情美,以及現實丑的激化趨向于美;對現實認識、描繪中的辯證美;滲透著勞動人民的樂天美三個深層人情美。[10]241-243由于創作思想、制作班底、觀眾需求等客觀原因,該劇在思想表達、情節取舍、藝術呈現等方面留下不少缺憾,這既關聯到原著題材的特殊性,也與創作主體的文化心理有關。
90年代后,中國內地的聊齋創作陷入低谷,僅有《毛大福》(1991,青島)、《聊齋傳奇》(1994,南昌)、《青鳳》(1995,上海)、《聊齋先生》(1998,浙江)、《人鬼情緣》(2000,山東)等少量作品。《聊齋傳奇》顛覆國產劇的正劇戲路,抓住聊齋題材的喜劇內核和娛樂元素,試圖消除原作中的恐怖怪戾元素,將之異構為鏡照現實的文化載體。《聊齋先生》則另辟蹊徑,以蒲松齡本人的歷史境遇帶入故事,以其人生經歷串聯起聊齋中的鬼狐精靈,于歷史時空中展現作者創作經歷,于想象世界中表達角色的情感糾葛。《人鬼情緣》(2000)以聶小倩、寧采臣之戀為敘事主線,串聯宦娘、秋容等悲情角色,將愛情、畸戀、陰謀、背叛、復仇等元素融于一體,建構起錯綜復雜的故事脈絡。
1984年,香港導演鮑方的《嶗山鬼戀》上映。影片以蒲松齡故居為引子,將青島嶗山、濟南趵突泉等地作為外景地,是香港電影走向內地的標志。1987年,電影《倩女幽魂》橫空出世,將鬼片、武俠、愛情、喜劇等類型元素融于一體,唯美浪漫的場景設計、凌厲激烈的武打動作、夸張幽默的港式調侃等令觀眾耳目一新。聊齋題材與現代手法的完美結合,引領香港電影走向類型化、風格化和模式化的創作道路,在文本借用、國族敘事和流程再造上不斷嬗變。此后,因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臺資港制的制片模式大行其道,比如《菩提幽魂》(1986)、《人鬼狐新傳》(1989)。與此同時,香港公司紛紛奔赴內地拍攝聊齋電影,如《狐仙》(1990,廣西)、《敦煌夜譚》(1991,甘肅)、《畫皮之陰陽法王》(1993,北京)等,風景地拍攝成為影視美學表達的關鍵性因素。
付瓊指出,“《聊齋志異·胭脂》從志怪小說《幽明錄·買粉兒》以及宋元戲劇、明代傳奇發展而來,是蒲松齡在現實推動下改造傳統的產物” [11]38。在戲曲舞臺上,60年代越劇《胭脂》曾大獲成功。改革開放后,貼合“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胭脂》(1980)熱映,成為時代大變革的文化印記。此后十年間,國內電影制片廠紛紛涉足聊齋題材,陸續推出《鬼妹》(1985,西安)、《碧水雙魂》(1986,上海)、《狐緣》(1986,西安)、《金鴛鴦》(1986,峨眉&安徽)、《古墓荒齋》(1991,北京),《幽魂奇戀》(1992,瀟湘),《癡男狂女兩世情》(1993,北京)、《古廟倩魂》(1994,北京)、《聊齋·席方平》(2000,北京)等大量作品。這一時期的國產電影,具有鮮明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整體上側重線性敘事和宣教色彩,映射出改革開放初期的文化意識和社會審美。
(四)成熟穩定期(2001—2015)
21世紀后,內地公司憑借雄厚的資金實力,不斷延攬各地影視人才,嘗試拓展聯合制片業務。2003年,瀟湘電影制片廠推出《陰陽判官》,由內地、香港、臺灣三地演職人員聯袂完成,邁出市場化轉型的關鍵步伐。2004年,廣東星際輝煌公司抓住《聶小倩》(2003)的收視熱度,簽約香港籍知名演員,制作出無厘頭風格電影《倩女失魂》。這種翻拍熱門電視劇的行為,盡管有蹭熱度、搶市場之嫌,卻成為后來網絡電影慣用的手法。
2005年,山西電影制片廠聯合上海、江蘇、香港的電影公司,連續推出《俠女復仇記》《兒女仙蹤》《鬼妹》三部聊齋影片,情節設計跌宕起伏,契合家國恩仇的宏大主題。此外,《家有狐妻》(2005)亦屬內地與香港合拍的聊齋影片,卻有意弱化深刻的思想寄托,強化詼諧幽默的喜劇精神。2006年,中央戲劇學院拍攝出《連瑣》《俠女》和《白秋練》等聊齋數字電影,為實驗性、程式化和技術流的“學院派”電影。
2008年,電影《畫皮》在全國院線上映。“影片將現代意識、自我意識和女性意識注入原有的故事框架中,探討和折射了現代人的情感、倫理困境” [12]49。根植于東方魔幻傳統,影片凸顯女性意識的覺醒,反思民族文化傳統的現代演繹,探索聯合制片模式的商業邏輯。受益于市場反饋,《畫壁》(2011)接續推出。《畫皮》以家庭倫理關系為中心,頌揚隱忍深沉、無私奉獻的愛情觀,帶有獨特的女性視角和現代精神;《畫壁》則表現世俗男女的婚戀態度,揭示“幻由心生”的禪學哲理。
2012年,《畫皮II》在電影寫實化風格上走得更遠,尤其注重特效鏡頭的精細打磨。從開篇的冰封狐妖、水下換皮,到靖公主揭下面具、與狐妖換臉,再到雀兒羽化升天、群鳥食巫WSf5c1+3Paxd+Rdj39V5Wh1IQlB8xoiGkBKYt8ZaAK8=師等關鍵段落,充分顯露出導演對細節控制的獨到之處。這種對純粹技術和藝術質感的協調把握,需要創作者熟悉中國文化的典型元素,深諳傳統審美的內在規律。《畫皮II》將特效技術巧妙地融入敘事,使之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力量,是觀眾沉浸式審美的主要對象。當然,在邏輯自洽、結局處理、命運走向等方面還有較大空間。
21世紀后,聊齋劇集創作逐漸從港臺轉移到內地。北京、上海等地的民營影視公司擔綱創作主體,以浙江橫店影視城為主要拍攝基地,拍攝出數量可觀的聊齋劇集。2004年,上海飛邁影視公司選取三個聊齋短篇,改編為《花姑子》《龍飛相公》和《粉蝶》等百余劇集,貫穿精靈變人、奇情絕戀的情節結構,探求愛與奉獻、人性向善的現代價值觀念。2005年—2007年,上海唐人電影公司先后制作了《聊齋志異》《聊齋奇女子》,采用跨界聯合的制作方式,展現出需求導向的商業意識。回顧中國與新加坡“合拍劇目中具體的題材內容,神話/古裝劇在海外華人區本身就有著堅實的營銷基礎和強大的跨越華語區之間文化區隔的能力” [13]105。2007年—2010年,上海東錦文化公司制作出《聊齋二》(36集)、《聊齋三》(36集)。2015年,上海星境影視公司制作出《聊齋新編》(36集)。至此,聊齋劇集仍以傳統單元劇形式為主。2016年,上海唐人電影制作公司編創的《青丘狐傳說》(40集)跨越到主題劇模式。此后,《畫皮》(2011,34集)、《畫皮之真愛無悔》(2013,41集)、《狐仙》(2013,43集)、《倩女喜相逢》》(2015,15集)等圍繞原著,大量擴增情節,以至節選、取意或雜糅其他作品的元素,極大地延伸了聊齋作品的思想內涵和精神意蘊。
(五)融合發展期(2016— )
2014年,愛奇藝影業公司首倡“網絡大電影”的概念和標準,“從類型范式看,網絡大電影高度集中于恐怖和喜劇兩種類型” [14]52。顯然,聊齋題材屬于前者。2016年10月,作為首部聊齋題材的網絡電影,《聶小倩之蘭若客棧》在愛奇藝平臺上線。經統計,在2016年至2023年的8年內,改編自《聶小倩》的網絡大電影高達十余部,題材扎堆現象嚴重。以北京東方飛云國際影視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的民營影視公司,主打“強卡司、高熱度”的網絡營銷策略,前后制作10部聊齋作品,取得了較好的市場回饋。
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網絡電影步入了高速發展期。在改編技巧方面,出于創作靈活度的考慮,多數作品僅僅保留了原著人物,故事情節臆造成分偏多,現代觀念植入痕跡顯著,甚至出現了一批偽聊齋作品。整體上,故事講述天馬行空,人物關系純屬虛構,獵妖除魔的氛圍之下,嗨爽吐槽消費快感,人文關懷逐漸式微,淪為文化資本的試驗工場。大多數網絡大電影故事的完整性、流暢性常被暴力、色情等碎片化元素和突兀、夸張的矛盾沖突所弱化,而影片的人物塑造多性格單一、臉譜化,其行為邏輯亦缺乏說服力。[15]200 2019年初,糅合聊齋人物的奇幻電影《神探蒲松齡》上映,“無論針對‘蒲松齡’角色之塑造抑或情節線索處理,這一新植入角色未能充分發揮其挈領、統籌效用” [16]112。盡管如此,該作呈現的故事思維及視覺奇觀,仍可為后來者提供一定的參照。
二、聊齋影視改編的敘事轉向
聊齋影視對《聊齋志異》文本的不同解讀,表面看是改編者二度創作的手法差異,內里則是時代變遷和文化審美的深層關照。究其敘事轉向來說,主要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忠于原著——節選與挪用的搬演模式
《聊齋志異》是一部包含近五百篇故事的小說集,篇目體量龐大,不但展現了蒲松齡高超的文學水平,還蘊含著古人的處世智慧和人生哲理。早期的聊齋電影改編,首選那些有教育意義的篇節,如《清虛夢》(1922)諷刺了那些學藝不精、妄圖不勞而獲的懶閑之人,提倡勤勞持家的生活態度;《孝婦羹》(1923)則致力于調解家庭糾紛,倡導以德報怨的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后來的《胭脂》(1925)、《馬介甫》(1926)、《田七郎》(1927)、《巾幗須眉》(1931)、《恒娘》(1931)、《馬介甫》(1935)、《莫負青春》(1946)等一批民國影片,大多關注婦女操守、夫妻相處、交友之道、家庭倫理、男女戀愛等社會問題,體現出思想性強、教化世道人心的功能訴求。
20世紀60年代,為后世稱道的聊齋電影莫過于李翰祥導演的《倩女幽魂》(1960)和鮑方導演的《畫皮》(1966)。兩部作品注重古風的場景表現,真實地還原了聊齋題材的鬼魅氣息和恐怖氛圍,受到當時觀眾的熱烈追捧。《倩女幽魂》中,聶小倩的“形象被刻畫為一個楚楚可憐的閨秀”,沒有過多去展現聶小倩的愛情故事。[17]66正因故事情節過于忠于原著,導致燕赤霞的地位不突出,缺少了戲劇沖突。《畫皮》延續了聊齋題材電影的驚悚恐怖屬性,在場景、道具、情節上盡力貼合原著,基本沿用原作的故事設定,怯懦軟弱、貪名好色的王生和賢惠平凡、迂腐善良的陳氏等都與原著相差不大。
(二)形神取意——嫁接與雜糅的拼貼模式
聊齋故事影視化過程中,導演不滿足于原汁原味地繼承,往往結合自身的創作需求,將聊齋中的人物、情節、線索等加以嫁接,實現不同故事元素的雜糅拼貼,保存了原著故事的精髓之處,達到形散神聚的藝術效果。所有聊齋篇目中,改編次數最多的當屬《聶小倩》。據統計,取材自《聶小倩》的電影、電視劇總數量超過50部。如此規模的影視改編,僅僅忠于原著是做不到的,大多數作品選擇“取意”這條捷徑,以蘭若寺為故事場景,以人鬼戀或人妖戀為故事架構,以色誘書生、道魔大戰為刻畫重點,引向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圓滿結局。改編次數居于次席的是《畫皮》,影視劇總數量為27部。類似于“換皮”“挖心”等驚悚情節被多次嫁接,勾連起觀眾的好奇之心,道出“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處世真理。改編次數緊隨其后是,《陸判》16部、《小翠》11部、《蓮香》11部、《連瑣》9部、《胭脂》7部、《長亭》7部、《阿繡》7部、《辛十四娘》6部。改編次數多,間接反映出原著故事的外部延展性,將“狐仙報恩”“借尸還魂”等母題加以藝術化處理,更加符合主題表達需要。
《辛十四娘》(1966)一改原作中狐婢赴燕都,跟蹤皇上到大同的妓院中,直面圣上拯救馮生的情節,而是將辛十四娘主仆置身于勾欄院中,巧遇圣上并直述冤情。救出馮生后,面對登門道賀的一眾故交好友,婢女喜兒義正詞嚴講出真相,“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傷我德,施之小人則殺我身”,辛十四娘主仆最終決絕離去。《狐緣》(1986)進一步演繹了辛十四娘為伸冤于京城妓院賣藝,為救馮生又不得已答應皇帝入宮,最終投井自盡,飛升成仙的過程。在處理楚公子陷害馮生起因時,前作設計為楚公子之妻阮氏失手掐死春娥,后者則換成楚公子對民女柳玉香始亂終棄,使之雨夜喪命的情節。顯然,柳玉香片段來自于《竇女》,“但影片刪去了《竇女》中竇女變鬼復仇南三復的怪誕情節,著重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描繪了柳玉香的稚嫩可憐和死后慘狀” [18]109。不同的是,前作安排了女鬼春娥在圣上面前顯身作證的情節,這更接近原作中狐鬼共存的角色設定,邏輯上合理合情,并無強行拼湊之嫌。
(三)顛覆原義——重構與置換的整合模式
《聊齋志異》是清初文言短篇小說的杰出代表,貫穿著蒲松齡的社會洞察和人文思考。用歷史考證的眼光加以衡量,原作中文學藝術、故事邏輯和思想意旨有其內在統一性,積聚了古人的思維意識和認知特點。由于文化時空的阻隔,對聊齋資源的挖掘利用,今人常常陷入“歷史主義的陷阱”,既要堅持忠于原著的歷史真實,又要強調還原再現的藝術真實。過于原封不動,就會走向保守和僵化;過于另類創新,則會喪失意旨和格調。以姚鳳磐聊齋電影為例,刻意強化驚嚇觀眾的視聽氛圍,著力增添夸張血腥的道具元素,探索出一條民族電影本土化的路徑。“其中土法煉鋼的鬼飄飄特技攝影異常艱辛,卻很成功,博得廣泛好評,尤其香港左派報紙的評價更高” [19]37。此外,《鬼叫春》(1979)不惜加入王生與女鬼的香艷情節,毫不避諱賺錢盈利之目的、愉悅觀眾之取向。到了《畫皮之陰陽法王》(1993)時,仍舊延續胡式電影之唯美古意畫風,但大量無厘頭語言的穿插使用消解了原作韻味,徹底淪為一部枝蔓雜亂、敘事失調的港式娛樂片。
在網絡播出平臺方面,年輕一代受眾逐漸形成了新的審美習慣和思維意識,他們不再滿足于傳統文學的內斂式敘事,轉而尋求文藝創作形式的求新求變,對傳統文化經典的顛覆、重構與置換的動能不斷增強。《搶救21克的愛情》(2016)實則是《聶小倩》故事的時尚版,將幾百年前的愛恨情仇放置于現代職場爭斗,探求的仍是真愛與永恒、復仇與博弈的價值觀。“新世紀聊齋題材電影中,蒲松齡形象以延異的方式不斷更新出場” [20]117。愛奇藝平臺播出的《聊齋變異》(2016),亦打破傳統敘事體例,借用蒲松齡轉世為現代人的橋段,串聯起探討職場規則的《偷桃》、展現二次元宅男真實生活狀態的《美人首》和顏值時代尋找真實自我的《陸判》三個段落。另一部網絡電影《伏狐記》(2018),則講述了假驅魔師蒲大師圖謀竊取金佛,混進美女鏢頭沈小魚、牛大膽、王不怕等人組成的鏢隊,途遇各種真假妖魔鬼怪的故事。在港式喜劇風格的包裝之下,在假定性、套路化的捉妖任務中,以營造視聽體驗為目標,以諧謔搞怪整蠱為賣點,終究淪為一部不折不扣的爆米花電影。
三、聊齋影視創作的品牌塑造策略
新時代以來,聊齋影視創作并未銷聲匿跡,而是呈現出一些新氣象。受眾群體年輕化、文化品牌產業化、影視資源本土化等市場趨勢,促使人們站在振興文化創意產業的新高度,審視傳統文化“兩創”的時代主題,擔當聊齋影視傳承創新的歷史使命。
(一)結合時代發展需求,提升聊齋研究氛圍
百余年來,聊齋題材影視作品不斷涌現,作品數量已達到規模化程度,但在技術水平和藝術表達上并未建立科學的質量體系和評價標準。這是因為,影視創作是時代的產物,承載了一代觀影群體的集體記憶,反映了時代發展的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時代的聊齋影視創作更要結合當前時代的情感需求,研究IP識別、IP認同、IP品牌的接受過程,促進用戶在認知、感受和體驗上的滿足感,實現從一般了解、深層記憶到完全內化的升華。在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進程中,聊齋影視創作也要揚棄舊思想,融入現代年輕群體的思維模式和認知特點,革新視聽語言表達方式,展示民族審美特征。
聊齋影視研究由來已久,1986年,王林書的《珠聯璧合,瑜瑕互見——談〈聊齋〉電影、電視劇改編中的得失》一文,最早談及了聊齋影視創作問題。1993年,王富聰的《聊齋影視評論》為第一部聊齋影視研究著作。2008年之前,聊齋影視研究處于極為邊緣的地位,全部學術文章僅有20篇左右。2008年《畫皮》的上映,不僅創造了票房奇跡,更引發了聊齋影視研究熱潮,尤其表現在改編現象研究、改編作品評點、接受與傳播研究三個方面,全部文獻總數量超過80篇,其中碩博士畢業論文12篇。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聊齋影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解決理論研究與行業實踐遲滯脫節的問題。
(二)厘清影視創作邏輯,開掘聊齋文化資源
影視作品是歷史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集中展示,是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形式。百年來,聊齋題材的影視創作經歷了從少到多、由探索到繁榮的發展歷程,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火熱局面。分析現有的聊齋影視作品,能夠發現聊齋題材的獨特性、人文性和價值觀,從而探尋古人的倫理觀念、文化傳統和處世之道,并深入挖掘提煉其當代價值,研究探索聊齋異界時空的愛恨情仇和奇譎想象的影視表達。山東淄博是聊齋文化的誕生地,合理利用地域文化資源,有利于振興地方文化產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強國建設。
當代影視劇創作具有高投入、高風險和高收益的行業特性,作為產業要素的知識、智力、科技、創意、營銷、資本等對于一部影片的成功至關重要。從影視劇策劃、構思、拍攝、制作、發行等流程運作來看,是一個產業價值增值的過程,也是一個知識產權構建的過程。在打造影視劇IP的時代,不能僅看一時之利,還要有長期的規劃和布局。為了應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需要及早樹立IP版權理念,構筑文化授權“護城河”,避免被山寨、復制和抄襲等行為的發生。為了激勵創作者的積極性,要采取商標注冊、授權開發、聯合經營等方式規避風險,切實保護原創性的創意設計、劇本方案以及相關文化要素。總之,聊齋影視創作要以地域文化為引領,以知識產權(IP)為根本,最大程度地構建IP生態鏈。
(三)突破聊齋文本局囿,創新聊齋敘事方式
截至2021年底,我國網絡文學用戶總規模達到5.02億,較前一年同期增加4145萬,占網民總數的48.6%,讀者數量達到史上最高水平。從這些數據看出,網絡文學的影響力不斷增強,這對傳統文化經典IP改編而言,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全民閱讀的氛圍加速形成,憂的是網民的閱讀習慣和題材偏好悄然發生變化,“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學效應似乎正在應驗。相較于古樸、典雅、凝練的古典敘事模式,網絡文學以時代性、互動性和圈層化引發共情,也因低俗、濫情、雷同等通病廣受質疑。《花千骨》(2015)、《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17)、《慶余年》(2019)等IP影視改編的成功足以證明,網絡文學的高質量發展是全社會的共同期待,原創文化IP轉化的典型范例也將為聊齋IP影視創作提供靈感和借鑒。
在中國電影電視銀幕上,武俠劇、言情劇、古裝劇、偶像劇、仙俠劇等類型化題材輪番上映,折射出新時代影視題材的巨大變化,體現了觀眾審美心理的轉換。與由武俠小說衍生的武俠劇不同,仙俠劇多是由游戲改編而成。自《仙劍奇俠傳》(2005)開創“仙俠劇”題材以來,將古裝、偶像、愛情、玄幻等元素融為一體,披著甜寵情愛的外衣,穿插權謀宮斗的伎倆,平添救贖蒼生的大義,難逃神仙眷侶的俗套。網絡文學有噱頭、有熱度,易博取點擊量,獲得市場青睞,但往往只是成就一時,很難成為傳之久遠的經典。已歷三百余年的聊齋文學本體,在后世不斷被注釋、品評和鑒閱,成為古典文言小說的集大成者。聊齋影視創作群體大可去糟粕而取精華,振正聲摒棄戾氣,葆意蘊祛除鬼魅,與仙俠敘事產生同頻共振,與社會主義文藝路線合流,實現“舊瓶裝新酒”的傳統文化復興。
(四)構建全產業鏈開發,拓展聊齋影視旅游
電影、電視劇都屬于文化創意產業的范疇,在知識產權(IP)方面具有獨占性和排他性。在影視行業內,IP更多指代網絡小說、游戲、漫畫等作品形式。影視劇IP大致分為三種形態:翻拍劇、上星劇和網絡劇。翻拍劇一般以金庸武俠劇為代表,上星劇以衛視臺購買的劇集為主,網絡劇則以各大網絡視頻平臺播出的劇集為主。網絡小說、網絡電影和網絡電視劇的內容生產已經形成產業鏈,涌現出以閱文集團、晉江文學城為代表的網絡文學平臺,以及慈文傳媒、正午陽光等影視IP制作公司。擁有龐大粉絲基礎的網絡平臺將作品授權給影視制作公司,借助高辨識度、自帶流量、變現能力強的IP符號特性,轉換為可觀的信息反饋、交流互動和社會傳播效果,形成支撐影視劇IP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
向勇指出,從文化形態的角度,IP可分為老經典、新經典與快時尚三種類型。[21]129古典文學名著屬于老經典IP的范疇,與當下廣受關注的網生代IP有一定差異,也存在著很多共性之處。聊齋文化歷久彌新,與當下影視翻拍直接關聯。兩百余部聊齋影視劇作品自成一統,為文學影視改編提供了素材與靈感,構筑起傳統文化、現代思潮與流行時尚的復合體。有人懷念《聊齋》電視系列片的年代氛圍,有人癡迷于《倩女幽魂》的繾綣深情,有人醉心于《畫壁》的酷炫神迷,足以說明審美的多元性。影視劇IP的傳播效果和變現能力有賴于口碑傳播、新媒體推廣等市場策略,也與影視公司的全產業鏈開發模式直接相關。劇集熱播往往還能帶動影視拍攝地旅游、植入廣告、衍生產品等附加產業。
(五)多方聯動協同合作,創生孵化優質內容
影視劇是包裹著文化藝術外殼的工業產品,是模式可循、技巧可鑒的團隊創作,是大量人力、物力凝結的成果。影視創作離不開導演、編劇、演員、剪輯、配樂、特效、宣發等人員的集體參與,也離不開政府政策支持和產業資本助力。褚宏祥提出,應“構建‘互聯網+聊齋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傳播及文化產業傳承與發展創新體系” [22]97。聊齋文化內容深邃,是影視創作的源泉活水。影視產業的根本任務是生產越來越多的優秀作品,優秀作品的前提是孵化原創劇本。因此,要積極引導資源配置向劇本環節傾斜,建立優秀劇本遴選機制,完善劇本評價反饋體系。政府部門或產業聯盟可以采取大獎賽、比稿會、懸賞令等多種形式,吸引優秀人才參與劇本創作,延伸產業鏈,提高附加值,拓展影響力。
2021年,國家電影局《“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指出,營造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充分發揮各類市場主體作用,有效激發企業進取精神和創新活力。民營電影企業是影視創作的新生力量,尋求特色化、差異化發展是當務之急。影視基地以服務影視創作生產為核心,實現與旅游、傳媒、信息等產業的融合發展是大勢所趨。智慧引領、創意驅動的影視業應以打造文化科技產學研聯盟為目標,實現內容生產、文化傳播到產業開發的全方位覆蓋,加大品牌營銷力度,推動產城融合發展。影視產業以優質內容創生為主鏈,還應積極籌建影視版權產業聯盟,構筑政府支持、市場主導、企業參與的影視劇本IP交易中心,定期開展影視節、首映禮、推介會等融商引智活動,拓展國內企業的創新思維、競爭意識和全局視野。
參考文獻:
[1]姜欣榮.中國古代文學的電影改編研究(1914-1930)[D].武漢大學,2019.
[2]宋碧洋.朱瘦菊——鴛鴦蝴蝶文人對我國早期電影的探索[J].西部學刊,2021,(9).
[3]馬寧寧.《聊齋志異》“兄弟分家”型故事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大學,2012.
[4]吳祖光.從上海到香港(1946—1949)[J].新文學史料,1996,(2).
[5]金進.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冷戰文化、南下影人與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化研究[J].當代電影,2019,(6).
[6]吳月華.粵劇與電影的匯流:粵語歌唱片[J].電影藝術,2012,(6).
[7]趙衛防.冷戰背景下香港左派影人的美學策略及影響[J].四川戲劇,2021,(4).
[8]傅葆石,王羽.香港國語電影的黃金時代:“電懋”“邵氏”與冷戰[J].當代電影,2019,(7).
[9]黃詩嫻.香港TVB電視劇題材類型、文化精神與發展路徑研究[J].藝術探索,2020,(3).
[10]王林書.“怪異·人情·哲理”的離合得失——《聊齋》電視系列片評論之一[J].明清小說研究,1993,(2).
[11]付瓊.略論古代小說、戲曲中“胭脂女”故事衍變[J].六盤水師范學院學報,2016,(2).
[12]趙芳婷.人皮易畫,人心難求——從《畫皮》看《聊齋志異》的影視改編[J].電影文學,2009,(20).
[13]張梓軒.中國大陸與新加坡電視劇合拍研究[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2,(2).
[14]曹開研.網絡大電影特征及發展趨向芻議[J].傳媒,2017,(4).
[15]楊藝.網絡劇大電影——網絡自制劇的延伸與發展[J].當代電影,2019,(11).
[16]王璟.求新有意 創新無果——試析Zug7JaX7ugAq8yYFXvoHzl2BCAH6sJ/JSz4P09yrQ+4=電影《神探蒲松齡》對《聊齋志異》的改編手法[J].蒲松齡Ey/iD2O+ycs5dy3sv2ZSUi6MUqFepF7a9QAnCR24jKk=研究,2019,(2).
[17]陳雙蓉.論聊齋鬼狐小說《聶小倩》的電影創新[J].電影文學,2012,(21).
[18]趙慶超,張冰潔.鬼狐的淡隱與現世的凸顯——從聊齋小說《辛十四娘》到《狐緣》電影改編的思考[J].蒲松齡研究,2015,(4).
[19]黃仁.臺港恐怖片的幾番風潮[J].電影藝術,2007,(2).
[20]趙慶超.新世紀聊齋題材電影改編新生征候考辨[J].蒲松齡研究,2019,(4).
[21]向勇,白曉晴.新常態下文化產業IP開發的受眾定位和價值演進[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
[22]褚宏祥,孫霜.“互聯網+”背景下聊齋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體系構建研究[J].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brand
building of Liaozhai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s
Abstract: The adaptation of Liaozhai zhiyi into films has spanned a century of vicissitudes.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adaptation of Liao-zhai in film and television,we can observe the permeation,reflection,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ulture,and gain insight into the creative path,artistic purpose,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adaptation of this classic work. The adaptation of Liaozhai in film and television began with a performance model that wa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ork,excerpted,and borrowed,and has gone through a collage model of form and spirit,grafting,and mixing,and finally to an integrated model that subverts the original meaning,reconstructs,and repla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the creation of Liaozhai in film and television should delve deeply into enhancing the research atmosphere,exploring cultural resources,innovating narrative methods,expanding film and television tourism,and creating high-quality content,in order to inherit traditional culture,shape cultural brands, and build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Liaozhai;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historical evolution;narrative shift;brand bui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