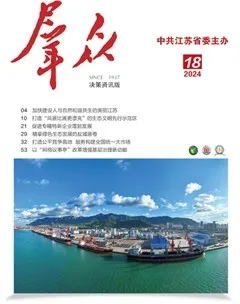筑牢公平競爭法治基石 持續建設一流營商環境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要求,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今年8月1日開始施行的《公平競爭審查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是這項頂層設計制度化、法治化的集中體現,也是對2022年我國《反壟斷法》首次修訂時新增的第五條“國家建立健全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具體闡述和細化落實,更是我國競爭法治建設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進一步完善的里程碑事件,為促進市場公平競爭、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公平競爭審查,指起草涉及經營者經濟活動的政策措施(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以及具體政策措施)的起草單位(包括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應當在起草階段對政策措施是否排除、限制競爭進行評估審查。其目的是從源頭上防止出臺不當排除、限制或扭曲競爭的法律法規和其他政策措施,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其核心任務是約束行政機關的經濟干預行為,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提供制度保障,也為政府更好發揮作用設定標準和界限。
公平競爭審查是理順企業、社會和政府關系的制度設計。在具體適用中,為了避免公平競爭審查異化為管制工具,需要以法律來規范和約束,《條例》正是目前開展公平競爭審查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據,確立了公平競爭審查基本規范體系。與以往規則相比,《條例》的突出進步在于,將審查范圍擴大到所有的法律法規和其他政策措施的起草階段;在起草單位自查基礎上強調反壟斷執法機構應參與公平競爭審查以更好發揮指導監督作用;加強對公平競爭審查工作的監督機制和追責機制的建設;特別重要的是,《條例》第十七條明確將對政策措施的競爭效果分析納入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從而把公平競爭審查與傳統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相貫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體系不斷完善背景下營商環境持續優化的前景值得期待。
完善競爭法治建設
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確立和進一步發展有助于完善我國競爭法治體系。作為對政府排除、限制競爭行為進行的事前預防性規制,我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建立在《憲法》第15條規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以公平競爭原則為基準,對影響市場主體經濟活動的政策措施進行合法性審查;與《反壟斷法》中禁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行政壟斷事后規制制度一起,構成約束行政機關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的法律制度體系;又和約束市場主體損害競爭行為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關規則一起共同形塑我國競爭法治體系。
市場的靈魂是競爭。維護和保障以公平競爭為核心的市場自發秩序,正是以競爭法為基本框架的競爭政策的價值目標和基本任務。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雖然只是競爭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因其核心功能在于正確定位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而成為建設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關鍵性制度。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以及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發展的要求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得到確認和重申。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2016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2017年發布的《“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和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是改稱“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且《反壟斷法》2022年修改時將其新增進第四條第二款,在法律層面上明確了競爭政策在經濟政策體系中的基礎地位,為《條例》的出臺及將來進一步細化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使競爭友好型產業政策、市場導向型經濟干預、市場經濟秩序框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新理念成為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有之義。
準確把握建設一流營商環境的著力點
優化營商環境,是應對當前國內外復雜經濟環境、實現統一大市場、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舉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重申“一流營商環境”的關鍵特征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蘊含著公平競爭的共同要求。
市場化是營商環境建設的關鍵,開放、統一、公平競爭的市場是吸引投資者的最好激勵。營商環境建設是包含一國經濟體制機制、國家治理能力、社會環境、思想觀念等多方面建設為內容的綜合工程,但其中最重要的基本面是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建設。這既涉及對規范私人市場經濟行為的《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及其實施情況的評估,也關涉政府是否能把建立和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作為基本經濟職能定位的問題。要求政府在制定和實施各項經濟政策時,不得阻礙和破壞市場公平競爭機制正常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杜絕以政府主觀干預之手代替或擠壓市場調節機制這個“看不見的手”。而這正是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核心要義。
法治化服務于市場化,表現為對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法律維護和對市場失靈情況的有效干預。市場競爭機制作為“發現的過程”是有效配置資源的“自發秩序”。這種經濟生活內在的、固有的客觀秩序,需要法律加以維護,抵制外在因素對市場自發秩序的任意干預。現實經濟生活中,政府既要做好守夜人,甘于“不作為”,也要適時積極作為,特別是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積極糾偏和重建市場自我調節機制。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市場經濟的永恒主題,通過法律制度理順二者關系是營商環境法治化的核心要求。“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政府依法干預,才能“更好干預”、有效干預,把“有形之手”的影響限定在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范圍內。
國際化要求主動對標國際標準,使經濟活動滿足經濟全球化發展需要。“營商環境評估本質上是對制度體系的檢驗。”近年來,我國積極參與在全球具有廣泛影響力和公信力的營商環境評估體系,如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評估。縱覽2021年之前的老版指標體系(DB)、2022年發布的新版營商環境評估體系(BEE)以及2023年開始推行的營商環境成熟度評估體系(B-READY),都是以法治原則為引領、以具體規則為約束,每一項評估指標及其評估實踐都建立在詳盡的規則基礎上,故有評價道“法治內嵌于世界銀行評估的每一項指標”。值得關注的是,B-READY評估體系將“市場競爭”作為新增的一級指標,表明其立場:競爭常常是不完美的,企業行為或政府干預都可能造成市場失靈;競爭政策是一國確保市場競爭不會因私人或者政府的反競爭行為而受到損害的法律與政策,對于營商環境至關重要。這一評估指標的納入,是國際社會對公平競爭之于優化營商環境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重要價值的肯定,充分體現了對市場經濟法治建設水平和促進市場公平競爭要求的重視和強調
(作者系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何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