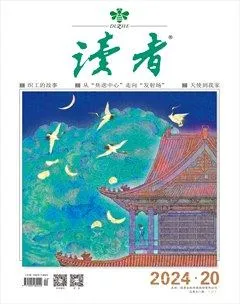那些年,射擊都教了我什么

你需要在30秒之內調整好呼吸,并扣動扳機,如果失敗,必須放下你的槍。
這是第一天訓練時,射擊教練對我們說的話。
那時候對我來說,最難面對的不是脫靶,而是在30秒之內沒有辦法調整好自己的呼吸。那種壓倒一切的寂靜伴隨著心跳聲,還有身邊的選手輕盈地扣動扳機后,將槍支前端架在海綿墊上的聲音,都令我感到泄氣。放下槍需要做好心理建設,因為它意味著剛剛做的——站好,舉槍,呼吸,將臉貼在槍上,看瞄準鏡,等等,這一套完備的動作的無效和失敗。沒有射出子彈就放下槍,約等于投降。
我也曾嘗試不要放下槍,什么時候調整好呼吸,就什么時候射擊。事實證明,持槍超過30秒,手腕就會出現難以覺察的抖動;靶紙上的落環甚至好幾次都不在環數內。那是一種從未感受過的挫敗和失望。
時至今日,回望這項運動,如果說它真的對我的人生產生了什么影響的話,我想就是,什么時候應該放下手里的槍,不管有多么地不舍,都必須放下,以便下一次更好地拿起。
在準備貴州省射擊錦標賽時,我不得不暫時停下一切其他運動,全身心地準備比賽。那時候我每周還有網球課,但后來在訓練中發現,揮拍這一動作在無形中影響了我手腕的穩定性,網球課不得不終止。
平時訓練時,我們需要在場館排隊領槍。門邊坐著一位男老師,負責登記姓名和取槍、還槍的時間,以及槍支的型號。倉庫里有幾把老式步槍,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應該是老式的峨眉EM45B型氣步槍。它的裝彈方式、重量和外形,都和比賽用槍不同。
我的訓練服是深藍色的。我們沒有多余的選擇,只能按照自己的身形選擇一套適合自己的服裝,在比賽服后面寫上自己的名字以免拿錯。我的訓練服上有一些褶皺,用白色和藍色的線條裝飾,穿上身后干凈利索,像個即將登月的宇航員。
衣服聞起來很像裝槍支的布袋,有著粗麻和尼龍布料浸進油里又晾曬干的味道。那或許是混合著汗味的一種既機械化又莊嚴的氣息。就像訓練館里寫著的“為榮譽而戰”,總讓看到的人為之熱血沸騰,好像穿上那身衣服你就不再代表自己了一樣。
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也是緣于人類基因中對競技的熱愛,對拼搏與自豪感的向往。
過去人們相信奧運會的傳承是因為人們將這種競技的形式,當作一種“虛擬的戰爭”,人們在此種廝殺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切不過是在“游戲”的范疇。然而,細讀《荷馬史詩》會發現,奧林匹克運動會這一盛事的延續,是因為它是葬禮上一種必不可少的儀式——人類以競技的方式向神展露人的力量,安撫逝者不安的靈魂,并通過比賽來重新凝聚人們因逝者離去而渙散的內心。
在所有運動中,我最喜歡射擊。射擊是一項孤獨的,和自己競技的運動。每一刻你都比上一刻更了解自己的身體。
調整好站姿,那套重達五公斤的射擊服讓人在其中難以晃動,就像負重前行時腿上綁的沙袋,你會感受到有一股力量拖著你下墜,仿佛要把你的雙腿釘在地上。我必須穿著單薄的襯衣,才能與這套沉重的衣服產生某種聯結。接著是肩膀,我要通過肩部的支撐和余熱去感受和溫暖那塊冰冷的金屬。
低下頭,閉眼調整呼吸和心跳。裝彈后,你要全身心地去感知這把槍的存在,甚至要盡力去想象它已經成為你身體的一個器官,你必須懂得如何運用它,讓它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對其他運動員來說,是不是也有相同的體悟:乒乓球拍、羽毛球拍,或者劍,他們是不是也將手里的物體想象成自己身上的某一器官,感受到它的溫度和跳動,才能更好地駕馭它?
槍彈射出的速度很快。但我在聽到那聲清脆的子彈穿過靶紙的聲音后,才能松弛地放下槍。
比賽那天,我在一開始就沒有調試好。我根據瞄準器或許有些朝左的偏差,微調了我的射擊范圍。結果,比賽正式開始的第一發子彈,我只打出了5環的成績。當看到這個數字時,我就知道,比賽已經到此結束。我只感受到在空曠的射擊場里,每個位置都站著一個正在瞄準的運動員,偌大的場館里幾乎沒有嘈雜的說話聲,只有不停地放入鉛彈、扣動扳機,以及靶紙被打穿的聲音。
我感受到比賽的殘酷。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被那些數字磨滅。最后那場比賽,20發子彈我只打出175環的成績。還沒有等成績完全公布,我就離開了比賽場所。因為我知道,這樣的成績在省里根本排不上名次。
那是我最后一次拿起氣步槍,成為職業運動員的夢想就此破滅。之后的日子,在每一次人生的抉擇關頭,每一次機會來臨的時候,我都記得教練給我說的那句話:調整好你的呼吸,30秒之內,發射出那枚鉛彈,如果沒有準備好,就必須放下你的槍。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自己能成就的事越來越少。我不知道早年的射擊經歷有沒有給我的人生帶來什么滋養,如果有的話,我想一定是學會在人生的長跑中,如何調整呼吸。
(彭慧慧摘自《文匯報》2024年8月5日)